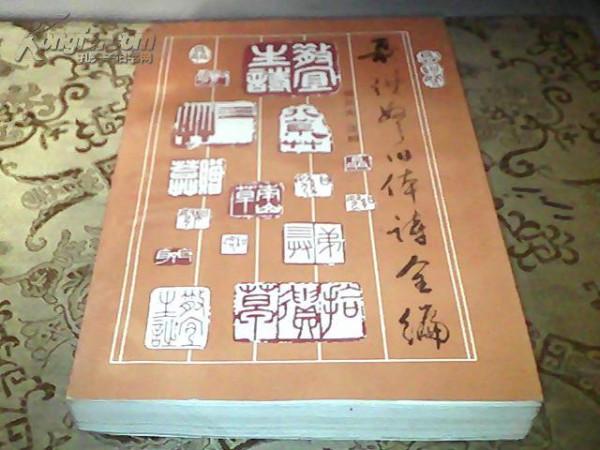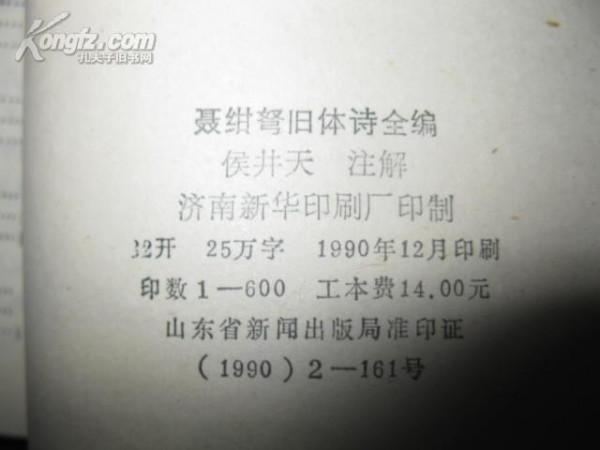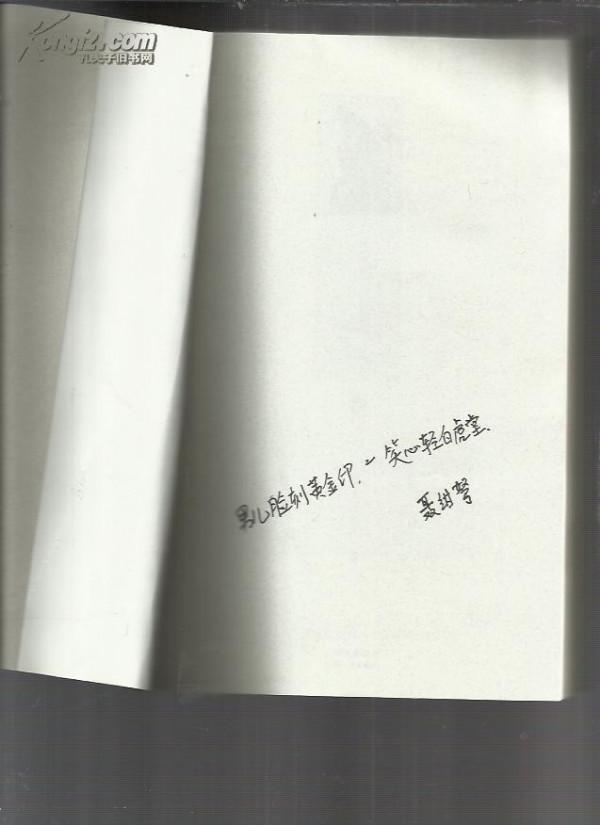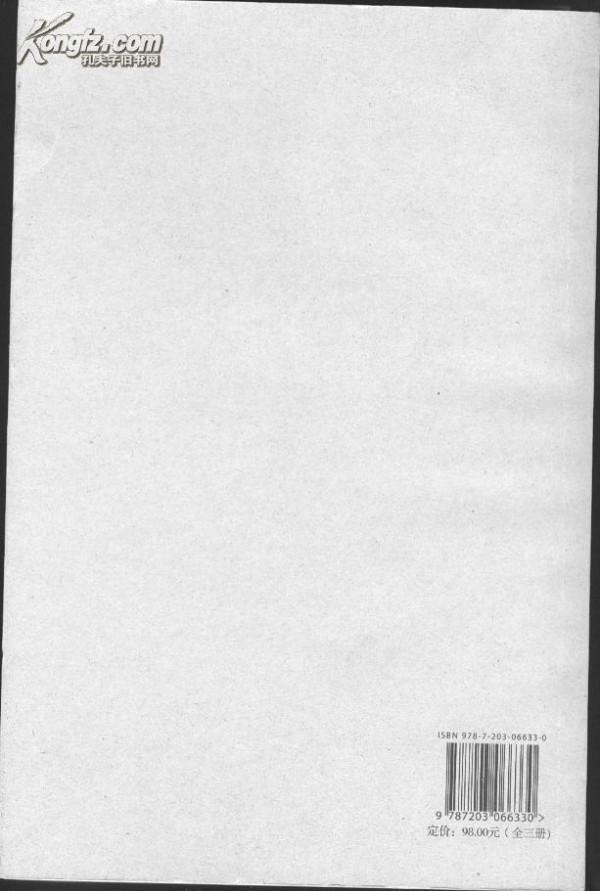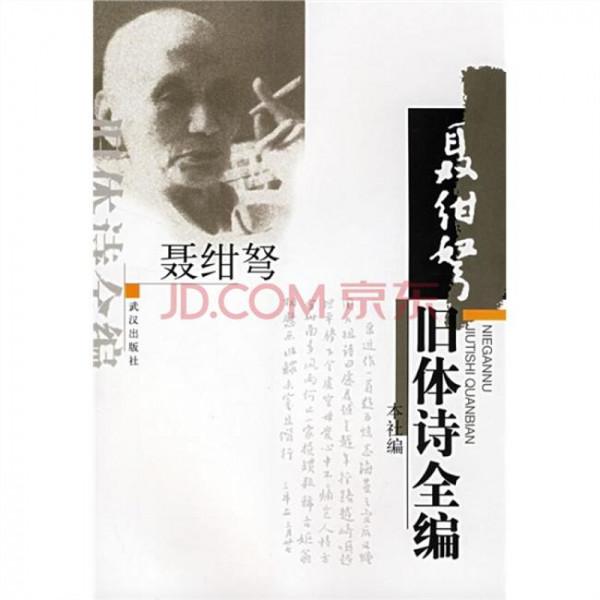聂绀弩旧体诗欣赏 漫谈聂绀弩旧体诗的艺术特色
这是聂绀弩于1986年逝世前写的纪念冯雪峰的诗。诗中说,雪峰下放干校时含辛茹苦,已经到了人生之秋,从干校回来病愁交加,郁郁而死。到了地下遇到章太炎夫子,该知道你是乾坤中第几颗头颅了!章太炎《狱中答邹容》有名句日:“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聂绀弩把冯雪峰与烈士邹容、前贤章太炎相捉并论,给予了很高的赞许。这首诗写于聂绀弩逝世前不久的时候,大概是他的绝笔之作,是不是也有暗作自许的意思呢?不仅是对雪峰,包括自己遇到章夫子的时候,也会是义一颗乾坤头颅吧!
聂绀弩确实立身很高,志向不凡。他对胡风、冯雪峰表现了那样深情的敬重和爱慕。而对另一些尚在台上掌权的人物,他的态度别有一种傲岸,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尤其是对那些他厌恶的人和事,往往破口大骂。
其日常言行,亦处处可见骨子里的气节,每令人肃然起做。 综上所谈,聂绀弩的经历、思想、气节,这些都是他的旧体诗的艺术特色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诗的灵魂与诗的语言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聂绀弩的丰富的阅历、自由的思想和不屈的气节,造就了他的诗的惊世骇俗的特色。
他的诗既有特色的内容,也有特色的形式。在诗的内容上,聂绀弩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他的情和志,他的阅历、思想、气节、人格,是他的诗的灵魂。
聂诗的灵魂,表现为强烈的思想性、现实性、战斗性。另一方面,在诗的形式上,他突破了传统的表达范式,创新了旧体诗的格律和语言。这是聂诗所表现出的显著的创新性。 一,聂诗的思想性。聂绀弩集中写诗是被打成“右派”之后。
致香港友人高旅的信中曾说到他当时心境:“五六年来,诸事颠倒,感情思想拘滞抑塞,彷徨不知所之”,“非此际遇,我亦无意为诗”。“这几年来感情上也不可能正常,不免要发抒发抒,不管如何发抒都好”。
又在诗集《自序》中说:“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由此而知,聂绀弩的诗都是“言志”的诗,都是表达思想、抒发感受的诗。诗中绝无轻描淡写之笔,没有一首诗是空泛写物、空洞议论的。
“言志”与“缘情”是相通的,“志”与“情”在古汉语中,很多情况下即为同义。“言志”是中国诗歌的根本传统。现代的某种西化的新诗概念,所谓“语言是诗的本体”,就完全背离了这个根本传统。
聂绀弩曾经认为,新旧体诗截然两道。因为聂诗恪守“言志”传统,他的感悟、襟怀、气节、忧患浸透在诗句中,使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思想性。 二,聂诗的现实性。聂绀弩有诗云:“谁知涉甚天下事,我但唱吾心里歌。
”这里好像说是不管它什么天下事,只管唱自己心里的歌,其实他心里的歌就是天下事。写诗不需要刻意去评说时事。但诗心不能不关怀时事,时事装在诗人的心里。如《北荒草》那些诗,写的是诗人在北大荒时的具体劳动。
但他写每一件具体事的时候,思想已远远飞跃于北大荒之外,心里想的是举国人民的事。看下面这些句子: 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 (《挑水》) 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 (《削土豆种伤手》) 曾闻买骨来多士,行见挥鞭上九霄。
(《马号》) 斧锯何关天下计?乾坤须有出群材。 (《伐木赠尊棋》) 天下人民无冻馁,吾侪手足任骈胝。 (《麦垛》)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清厕同枚子一》) 手散黄金成粪土,天将大任予刘曹。
(《清厕同枚子二》)可见聂绀弩善于寓大襟抱于小事体中。写北大荒的诗中,有一首《怀张惟》: 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 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 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
北大荒人谁最健?张惟豪气壮山河。作家张惟在北大荒时写了一篇小说叫《第一书记上马记》,内容为反浮夸风,被召开大会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聂绀弩为张惟鸣不平,写下了这首充满现实批判精神的诗。
聂绀弩说过,不经过忧患,不与社会有肉搏之处,旧体诗就写不好。他深切领悟了中国诗歌的“忧患”传统,继承了杜甫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可显示诗人本色的是他写在《除夜题所作》中的两句诗:“何能掷地金声响,只当忧天痛史观!
” 三,聂诗的战斗性。聂绀弩原来是以写杂文著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他的诗中有着杂文的影子,被称为“杂文入诗”。鲁迅的旧体诗就有杂文意味,如:“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自嘲》)“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义新春。”(《二十二年元旦》)聂绀弩的杂文受鲁迅影响,聂诗也受鲁迅影响。可以说他是“上追杜甫,下学鲁迅”。《挽王莹》一诗的第三联:“老归大泽菰蒲尽,露冷莲房坠粉红。
”上句出自鲁迅《亥年残秋偶作》,下句出自杜甫《秋兴八首》。杂文的战斗性,譬喻为“投枪与匕首”。聂绀弩在提到他的旧作《天亮了》这部杂文集时,有两句诗:“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
”可证杂文入诗,也把战斗性带进了诗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聂绀弩写了一首《没字碑》,以武则天影射江青:“东施效颦人尽嗤,岂汝称孤道寡时!”当时造反烈火方炽,江青气焰熏天的时候,写诗敢于如此锋芒逼人,的确是要有一种硬骨头精神的。
再举一些例句:“有字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题(鲁迅全集)》)“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八十》)“天下是非谁管得,彼皆人主咱其奴!
”(《雨中瞻屈原像》)“安得菜刀千百把,迎头砍向噬人帮!”(《挽贺帅》)这类诗句,即为词锋凌厉的杂文语式,体现了战斗性的杂文风格。 四,聂诗的创新性。聂诗的创新,既有内容的创新,也有形式的创新,两个相辅相成。
其内容上的创新,已包含在前面所说的诸多方面之中。聂诗形式上的创新,亦即语言创新,主要表现为: (1)口语入诗。“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归》)前一句是用杜诗,后一句是口语。
“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即事用雷父韵》)聂诗中这种口语、俗语、俚语很多,“无鸟事”都可入诗,还有什么词语不能用?当然要用得巧,搭配得好,入了对仗,合了格律。这种“诗化”的工夫并不简单。
如果简单地把口语往诗里塞,可能会弄得粗俗不堪,就不成其为诗了。 (2)袭用成句。“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八十》)“一谈龙虎风云会,顿觉乾坤日夜浮。”(《喜晤奚如》)“百年奇狱千夫指,一片孤城万仞山。
”(《有赠》)用前人诗中成句,诗家历来有之。聂绀弩颇善此道。但“四书”和古代散文中的成句搬到诗中极为罕见,这要算聂诗的一个突破。 (3)变化节奏。七律历来惯用的句式节奏是“二、二、三”结构,聂绀弩诗中对此有许多突破,常用“一、三、二”:“脱红绫袄心真碎,补雀金裘力早抛。”《晴雯》“三、一、三”:“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削土豆种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