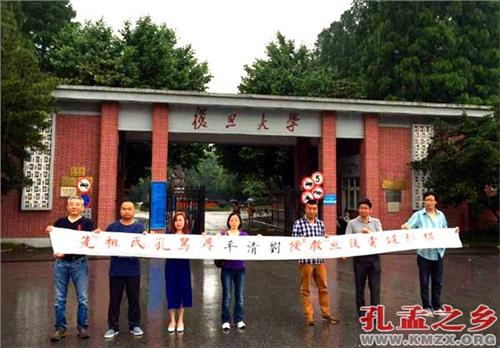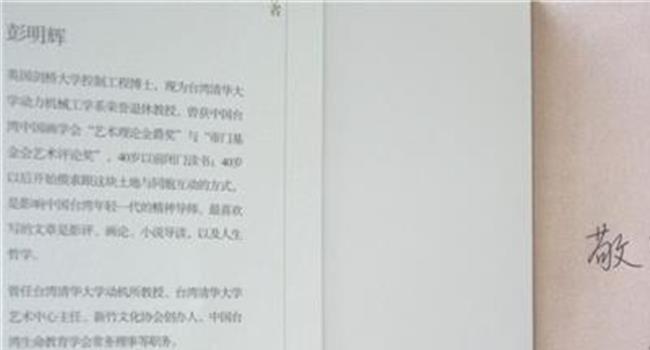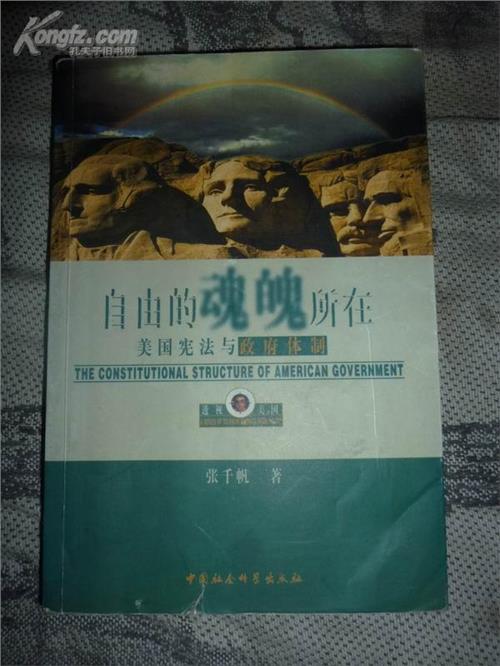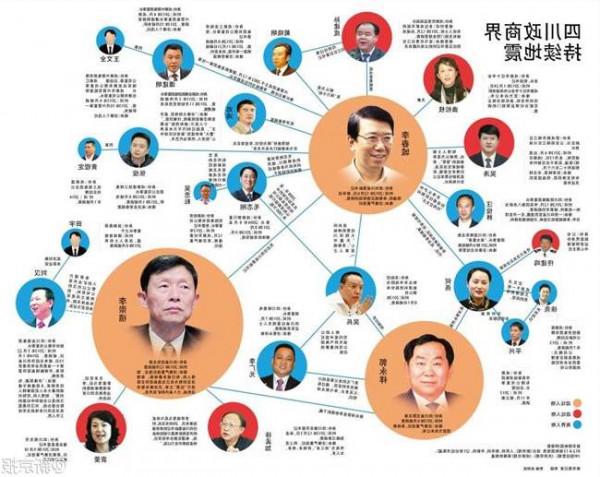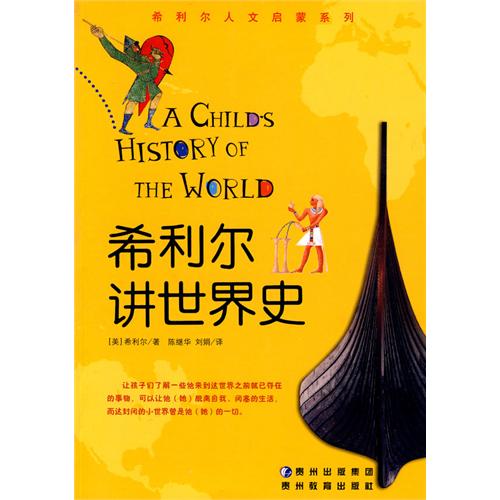刘清平孔子 刘清平:也谈孔夫子的“直”以及“作证豁免权”
秋阳先生在《从孔夫子的“直”说到“作证豁免权”》(见《儒家伦理争鸣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716页)一文中,将“人们最诟病孔子的一句话”——亦即《论语·子路》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与“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把血缘亲属纳入享有司法作证豁免权的群体”联系起来,强调指出:“孔子之所以要‘隐’,现代民法之所以要制定‘作证豁免权’,其目的乃是为了维护人们难以割舍的亲情”,并这样为孔子喊冤叫屈:“敏哉,孔夫子,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冤哉,孔夫子,为了这一发现,他老人家承受了多少年的委屈和非难!”
对于秋先生这种不想回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经典、却试图把孔子与现代民法(并且还是现代“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做法,我有一些不同见解,想在这里提出来讨论。
在我看来,秋先生不加辨析地从孔夫子那句话中的“直”说到现代民法中的“作证豁免权”,在法律上和逻辑上其实都是很不严谨的。众所周知,孔子是在“其父攘羊”的文本关联中,明确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与此相似,孟子也是在“其父杀人”的文本关联中,极力赞扬舜“窃负而逃”的举动的(见《孟子·尽心上》)。
然而,倘若我们要把这些话语与现代法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话,那么,按照后者的观念,攘羊、杀人这些违法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因此适用的应该是刑法,而不是民法即《民事证据法》。
但是,众所周知,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有意作伪证、隐匿罪证则是违法犯罪行为。从这里看,很明显,即便血缘亲属在民事案件中的确可以享有作证豁免权(假设《民事证据法》的上述规定已经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通过),但他们在攘羊、杀人这类刑事案件中,也根本不可能享有作证豁免权。
有鉴于此,秋先生依据“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的有关规定,来论证古代孔子主张“父子相隐”的正当合理,似乎有些驴头不对马嘴或是风马牛不相及。归根结底,尽管依据“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的有关规定,在民事案件中可以允许“父子相隐”,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攘羊、杀人这类刑事案件中也能够允许“父子相隐”,因为依据已经制定了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种“父子相隐”是违法犯罪行为。
我认为,在当前普法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一点特别有必要予以澄清,以免秋先生很不严谨的论述会在现实生活中引起某些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因为秋先生大概不会愿意承担这类严重后果的任何责任。
那么,对于血缘亲属的作证豁免权,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与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为什么会做出上述不同的规定呢?我认为,秋先生的下述看法,对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诸多价值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应该选择更重要的,而在比较次要的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从这个角度看,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血缘亲属在一切刑事案件中都不享有作证豁免权,其实是因为:维护公民的根本权益不受任何刑事犯罪行为的不法侵犯(一般而言,刑事犯罪行为所侵犯的主要就是公民的根本权益),要比维护某些特定父子(亦即从事这些刑事犯罪行为的人们)之间的血缘亲情更为重要;而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之所以又规定血缘亲属在某些民事案件中可以享有作证豁免权,则又是因为:维护普通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要比维护公民在民事纠纷中所涉及的次要权益更为重要。
换句话说,现行《刑事诉讼法》与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的这些不同规定,是按照公民的根本权益、父子的血缘亲情、公民的次要权益这一先后秩序来确定它们的重要性,并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做出特定选择的。因此,我国法律的这些规定虽然有所不同,但应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
相比之下,孔子和孟子有关“父子相隐”、“窃负而逃”的主张,却明显是认为:即便在攘羊、杀人这类刑事犯罪案件中,维护某些特定父子(亦即从事这些刑事犯罪行为的人们)之间的血缘亲情,也要比维护其他民众的正当财产权和生命权更为重要,甚至比维护他们自己大力提倡的仁爱理想更为重要。
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是把维护血缘亲情看成是人的存在中最为重要、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了,亦即孟子说的“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从而主张:“在诸多价值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应该选择最重要的血缘亲情,而不惜放弃和牺牲其他一切东西”。
在我看来,孔子和孟子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人们的非难和诟病,既不能说是冤枉,也不能说是委屈。
在人的整体存在中,血缘亲情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维护这种难以割舍的亲情,我们可以在涉及民众的次要权益方面做出一些让步。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把自己的父子亲情凌驾于广大民众的根本权益或是仁者爱人的普遍理想之上,以致为了偏向亲属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损害他人利益,或是为了偏袒亲情私利而不惜缺失社会公德、违反正义法律,否则就只能落入“私心太重”、“私情太重”的缺德境地,甚至是落入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腐败深渊。
接下来,秋先生又进一步举一反三,从古代孔子主张的“父子相隐”观念出发,讨论了“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对待我们队伍中一些同志的缺点错误”的现代问题,并明确得出结论说:“自觉地珍惜自己国家和组织的荣誉,珍惜自己同志的荣誉,维护其尊严,这也许是比坚持某些所谓‘真实’更重要的价值目标。”
我不知道秋先生在这里以嗤之以鼻的口气提到的“某些所谓‘真实’”究竟是指什么;但在我看来,秋先生的这一见解也是很不严谨、无法成立的,必然会导致一系列损害我们国家根本利益、损害全体公民根本权益的恶劣后果。其实,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同志的确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尤其是如果这些缺点错误有可能损害到广大公民的根本权益,那么,即便这些缺点和错误属于“在所难免”的范围,大胆揭露、勇于批评这些缺点和错误,也依然是完全正当、无可非议的,根本不会危及我们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同志的荣誉和尊严,相反倒会更有效地维护我们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同志的荣誉和尊严。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任何一个队伍里的一位成员或战士,只要他还爱护自己的国家和组织,爱惜自己的同志(借用秋先生的术语),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以“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态度挺身而出,大胆揭露、勇于批评这些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珍惜自己国家和组织的荣誉,珍惜自己同志的荣誉,维护其尊严”。
否则,倘若我们在这方面继续坚持“为长者隐,为尊者隐,为圣人隐”的悠久传统,文过饰非、隐瞒遮蔽、官官相护、亲亲尊尊、报喜不报忧,其后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不仅会助长讲假话、作伪证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行为,不仅会阻碍我们确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不仅会剥夺广大民众应该正当享有的知情权,而且还会在实质性的意义上严重损害我们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同志的荣誉和尊严——借用秋先生的术语说:“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事实上,十年“文革”中极为流行的种种假大空口号(诸如“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等等),近些年来依然时有发生的种种隐瞒矿难事故、隐瞒人为灾害、尤其是隐瞒各级官员“缺点错误”(借用秋先生的术语)的事件,不正是依据与秋先生类似的观念,打着“珍惜自己同志的荣誉,维护其尊严”的冠冕堂皇的旗号出现、并且得到了与秋先生的论证很是相近的热情辩护吗?甚至,目前某个国家的首脑以及极右分子出于同胞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极力隐瞒本国一些杀了人抢了羊的战争罪犯的残酷罪行,千方百计地“修改”历史上的“某些所谓‘真实’”,不也是在自觉地珍惜他们自己国家的“荣誉”,珍惜他们自己同胞的“荣誉”,维护其“尊严”吗?不也是把这些东西视为“比坚持某些所谓‘真实’更重要的价值目标”吗?因此,我想请教秋先生的是:在秋先生看来,这种“亲亲相隐”的举动究竟是应该谴责呢、还是应该赞美?如果秋先生认为应该谴责,秋先生又该怎样谴责呢?
我们很容易看出,“为长者隐,为尊者隐,为圣人隐”这个在过去以及在今天一直发挥着种种负面效应的悠久传统,与孔夫子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有着难以否认的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就是从他倡导的这种“直在其中矣”那里直接发展而来的。
不过,为公平起见,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孔夫子还曾经谈到另一种“直”,也就是秋先生颇为鄙视的那种“敢于尊重事实”、“能够坚持真理”之“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论语·公冶长》)微生高自己家里本来没有醋,但别人找他借醋的时候,他却隐瞒这一点,跑到邻居家借来,再交给那个来借醋的人。在这件事中,微生高几乎可以说是出于助人为乐的高尚目的而有意隐瞒真相。不过,很明显的是,孔子并没有为了珍惜他的“荣誉”、维护其“尊严”,就采取那种你好他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态度,而是从“敢于尊重事实”、“能够坚持真理”的立场出发,不留情面地严厉指出:这种做法不能说成是“直”。
在我看来,为了今天真正确立“诚实正直”的社会公德,为了今天发扬光大“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其实应该大力倡导孔夫子认同的这种“直”,而不应该维护他认同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直”。
不知秋先生以为然否?
末了,在《儒家伦理争鸣集》的一篇文章中,刘军平先生也谈到我国“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有关“作证豁免权”的规定,并且这样义正词严地发出质问:“笔者还想知道:刘清平……先生能否接受这种体现了儒家‘亲亲相隐’思想的进步法制观念?”(第750页)
首先,为满足刘军平先生的这种如饥好奇心和似渴求知欲,我想在这里简要地回答如下:第一,我不仅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这种法制观念,因为如上所述,这种观念在关涉民事纠纷的时候,给予了血缘亲情一个正当合理的相对地位;第二,我不仅不能、而且不愿接受传统儒家的“亲亲相隐”思想,因为如上所述,这种思想在关涉刑事犯罪的时候,无条件地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并且必然会导致上面提到的种种损害广大民众正当权益、不仅缺德、而且腐败的恶劣后果。
不知笔者的这些回答是否能使刘军平先生的如饥好奇心和似渴求知欲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其次,按照“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笔者还想知道:刘军平先生能否接受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与儒家“亲亲相隐”思想正相反对的进步法制观念?如果不能,他在“其父攘羊”或是“其父杀人”的假设情况下,又该怎样去做?
不知刘军平先生能否以简要的回答,使笔者的这点如饥好奇心和似渴求知欲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