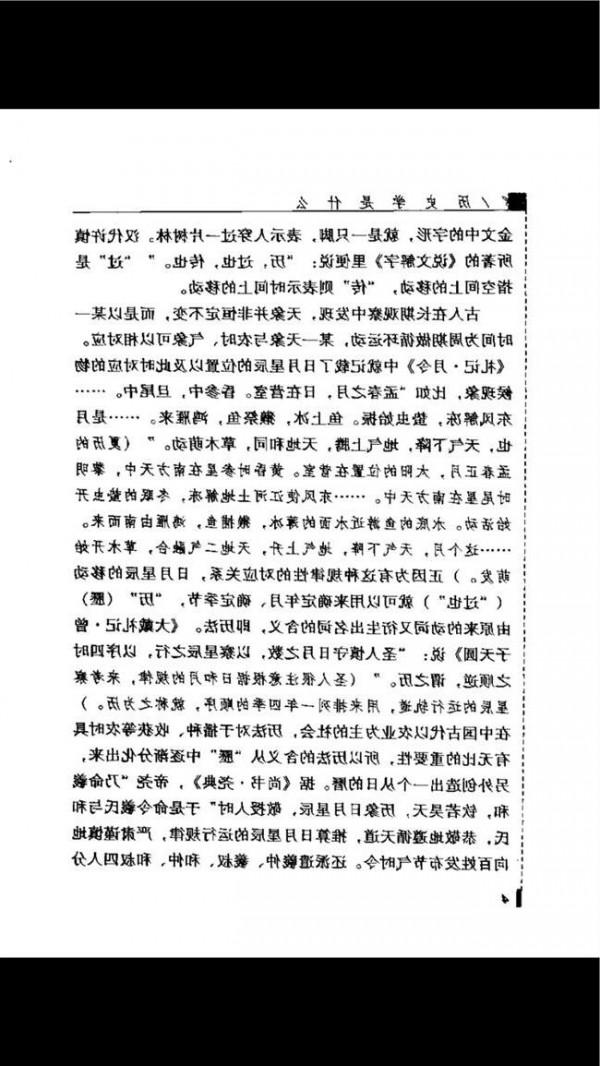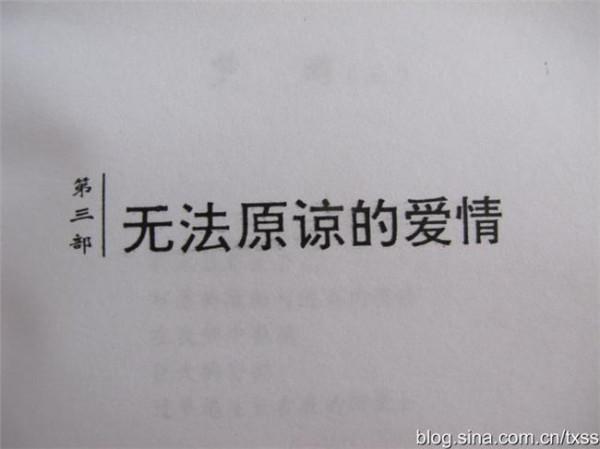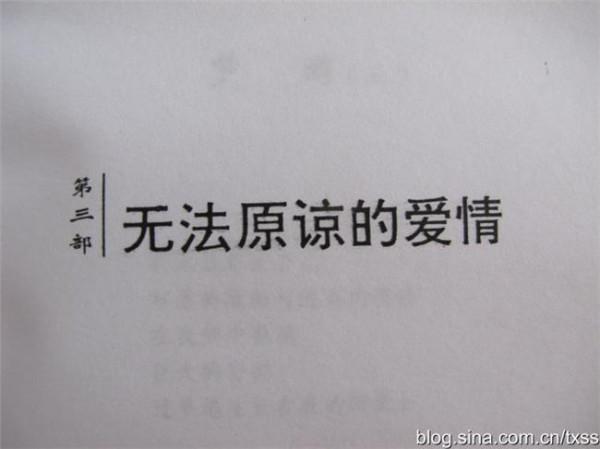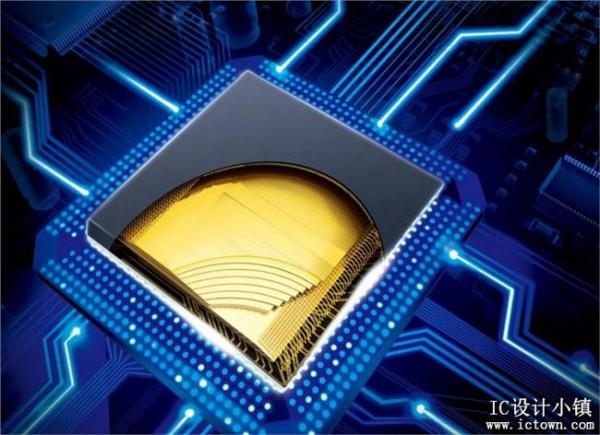阎连科受活 受活——比较莫言先生与阎连科先生的受奖演说
《受活》本是阎连科先生小说的题目,这里把它引来做我的题目,是由于看了两位先生(莫言、阎连科)的受奖演说词后的感慨,我认为用这个词再说里也暗指一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很有意思的是,“受”字,本有某种程度合适不过了。“受活”在小说里本指一隅贫穷而落后的受活庄,而在小上的被动之意,放在本指生活或活着的前面修饰“活”字更加令人深思。
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今阎连科又摘得卡夫卡文学奖,这不仅个人的荣誉,这更是两则中国文坛的美谈。生活对作家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在两位的演讲词当中,都提及了生活对他们写作生涯的影响,然而,相仿的年龄和相似的个人经历对生活的体会在他们笔下是嫣然不同的。
在我看来,阎连科先生在他的演说中似乎给生活化上了重重的烟熏妆——阎连科先生以黑暗的生活感受为演说的切入点,开头便说自己是上天和生活选出来感受黑暗的人,仿佛为世界盖上了一层轻纱。
与阎连科先生所不同的是,那个给我们讲故事的人,多次以“他”这个并不十分亲切的第三人称,从客观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用一种相对轻松的语调从他生活的细琐之事为我们讲他的生活。两位先生的演说,各有各的味道,一个是高尚得伟大,一个是平凡得伟大。
抛开作家的作品,就这两篇演讲,给了我们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个黑暗,一个光明;一个沉闷,一个诙谐;一个煎熬,一个享受。
首先从题目上看,我认为莫言先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他以《一个讲故事的人》为题,似乎暗暗将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住的身份,拉近了现场观众和读者与他的这两重关系;而阎连科先生便没有那么聪明,《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我看来,这首先加大了读者与他的横向距离,题目有意无意地提升了自己的身份。
撕裂了他与常人的关系。是的,生活中有黑暗,但也有光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黑暗的生活,甚至有些人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作家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是个能一眼洞悉这种黑暗并深加思考将它写在纸上的人。即便我认为阎连科先生在选题的时候用了个不很准确的题目,但我仍然喜欢那句“记忆与感受,使我们成了热爱写作的人”。
两位先生的演讲词当中,都提到了自己的母亲。莫言先生说:“很多人在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都分享了我的荣誉,唯独一个人,没有机会分享我的荣誉,那便是我的母亲”,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开头,接下来的故事,莫言先生有一半的故事是围绕他的母亲展开的,而那似乎与诺贝尔无关。
更多的像是在调侃自己小时候的调皮以及对母亲深深的怀念,然而,正是因为有了“母亲和高密东北乡”使得这位“文学流浪汉”有了一块写作的良田,这使我不禁想起我钟爱的作家三毛所作词的那首歌《梦田》,歌的第一句是“每个人心中有一亩田”,我想。
这或许就是莫言先生心中的那亩“梦田”吧。阎连科先生对母亲的记忆似乎很沉重,仿佛要推开一堵厚厚的墙才能看见母亲昔日的身影。这里就不多做说明,同样是生活,而两位作家对母亲的回忆却是大相径庭,阎连科先生在回忆母亲时说自己能想到的词是“煎熬”,这个词似乎贯穿于作家的整个生命历程;而莫言先生在感受生活上虽然也有一些苦痛,但我们更多感受的是一种调皮与可爱。
作家们最整齐统一的相似是都有一种“乡土情结”。阎连科先生在他的演讲词中给我们陈述的是一个煎熬的社会,煎熬着的故乡,多年前的母亲和父亲、伙伴和同村人、乃至今天的中国无一不是在黑暗的生活里煎熬着。更加确切地说,他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繁荣之下无比焦虑的中国,整片稿子,未涉及自己任何一篇作品,他以作家的使命这一线索为中心为我们深刻地阐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与他不同的是。
莫言先生在他的讲稿当中多次提及了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都遍及了让他又爱又恨的高密东北乡的每一寸土地,他的母亲和父亲、莫不相识的过路人,甚至是那里的一树一花都成了他笔下的素材。
阎连科先生的整篇文章布满了黑暗,然而在末尾,我们还是看到了微光,他的结尾再一次提到了那个在夜里持灯为别人寻找光明的盲人,而这样让人动情的光亮只有在极度黑暗的时候才会凸显——不仅是周围的环境,连眼睛里都布满了黑暗。
阎连科先生坦诚自己正承受着黑暗,而他又何尝不是在享受这种黑暗呢?因为享受这种黑暗,使他成为了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看到了别人无法看见了东西,挖掘了社会和文学的空白。莫言先生说自己在获得诺贝文学奖之后,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使他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他将在未来的生活里继续讲他的故事,在莫言先生的结尾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比阎连科先生更多的平淡。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谈及“美的本质”所用的比喻,我认为用在这两位文学巨匠身上十分合适,黑格尔以大教寺为例,分别例举了教堂的内部形态与外部形态的不同,教堂以哥特式建筑为主,内部的墙壁,柱子向上自由升腾,在上部形成了尖拱形的特殊形式,好像是植物的茎向上生长开出的花朵。
这样的形态体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感和宗教的意蕴。这就好比莫言的演讲词,平淡的陈述中不失一种血肉情怀。而教堂的外部形态,显出的性格是一种昂然高耸,在一切方面都显出一种尖角,也不失镇静和肃穆,依稀感发于人心灵深处。这和阎连科的演说,总是给人以肃然起敬的距离感,而这种距离又是离我们如此之近,近到我们甚至毫无察觉。
然而,当你品尽人世间的苦茶,看尽生活的黑暗面,你还是不能与生活告别,即使是“受活”,你还是不得不回归那平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