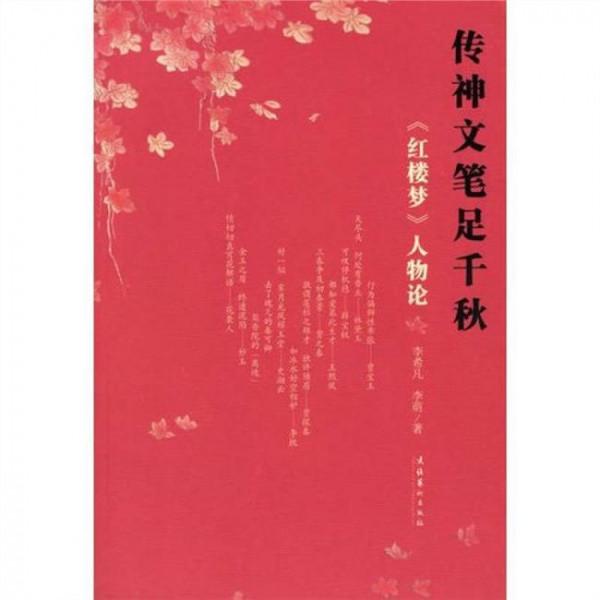李希凡红楼梦前言 关于《红楼梦》再版前言的一封信
我最近身体不好,寄来征求意见的三篇前言又是相当长的文章,所以我迟到现在才把它们读完,很抱歉!
就我匆匆读过一遍的印象来说,我觉得三篇前言共同的优点是:都介绍了不少和小说有关的知识,而且有一些分析和说明是颇有见地的,如关于孙猴子的反抗性及其限制的分析,关于宋江的两面性和关于忠义的分析,等等
李希凡同志的文章,不足之处是后面的文章好象不少部分仍未能超出过去的批评文章的写法,对《红楼梦》中的具体人物、具体情节讲得过多过细。
李希凡同志的文章的第一部分,有些地方批评到我,我在我写的文章和工作中,都是有错误的,我欢迎批评。不过我读时,感到有些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符合事实,我仍应该提一些意见,供李希凡同志参考。
一、我的《论<红楼梦>》一文,是有不妥之处的(《代序》是节录其中的一部分)。我在一九六三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发表的文章《曹雪芹的贡献》中,就曾经作过自我批评,我说对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肯定得太多保留得太少了,赞扬得过多批评得过少了”,“表明我们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还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还没有超越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水平。
”但是,对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看法呢?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和我这一类的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虽然主观上想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研究古典文学,而实际上确有很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
李希凡同志却是怎样叙述呢?他说:“正是由于批判‘新红学派’的斗争没有能沿着毛主Xi的指示的正确方向贯彻到底,盘踞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人性论的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又披着新的外衣又出现在所谓《红楼梦》的研究著作中间”。
我觉得这种提法应该斟酌,因为下面举的代表有一个就是我。我觉得这句话,第一,完全否定了我主观上想比较正确地解释《红楼梦》的努力,好象是有意伪装“披着新的外衣”出现;第二,否定改造世界观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凡是还学得不好的,改造得不好的,就是“披着新的外衣出现”的“反动观点”。
二、李希凡同志摘引了我《论<红楼梦>》一二句话,说是宣扬“恋爱至上”主义,其实如我在前面说过的,过去研究《红楼梦》的人过于着眼其中的恋爱故事是普遍的现象,就如李希凡同志写的文章中,不也是用大量的热情歌颂的话来赞美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吗?“美丽的生活理想”,“忠实于真正的爱情”,“充满着美好的灵魂”,“忠实于纯洁理想”,“忠实于纯洁爱情”,“他们真挚的相互热爱着,表现出高度的忠诚与纯洁”,“纯真的美的理想”,“人类优美的感情世界”,等等。
难道我们能够因为李希凡同志用了这些赞美的话,就否认他是在努力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吗?这些话和李希凡同志引的我的赞美的活,又有什么原则区别呢?看论文,它和看创作一样,是应从它们的主要倾向来判断的,不能因它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某些论点和说法的错误。就加以全部否定。 .
三、李希凡同志引了《论t红楼梦>》中的几句话,说我“公然宣传一整套永恒人性的‘典型共名说’”。这个问题我和李希凡同志已作过较详细的辩论,在关于阿Q问题上,按道理,李希凡是应该了解我的论点和看法的,不应再武断地说我“公然宣传”什么“永恒人性”,我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什么“永恒人性”,也没有说过有什么没有阶级的人性。李希凡同志摘引两三句的全文是这样的。
……人们叫那种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的人为贾宝玉。是不是我们可以笑这种理解为没有阶级观点和很错误呢?不,这种理解虽然是简单的,不完全的,或者说比较表面的,但并不是没有根据。这正是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点在发生作用。
后面我又说:
贾宝玉的性格的这种特点也是打上了他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的。然而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这却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因此,虽然他的时代和阶级都已经过去了,贾宝玉这个共名却仍然可能在生活中存在着。
这些说法当然是有错误的。第一,人们那种习惯的称呼贾宝玉的话,不仅是简单的,不完全的,比较表面的,应该说就是缺乏阶级观点;第二,说“贾宝玉这个共名却仍然可能在生活中存在着”,也是不妥当的,如果现在还有人戏称谁为贾宝玉,那应该认为是一种侮辱,那就是说他是贵族公子哥儿,而且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品行不好的公子哥儿。
但是,这怎么能说就是在“公然宣传一整套永恒人性”呢?就是说了“仍然可能(我用的是不肯定的“可能”)在生活中存在着”和“永恒”相距不是还有十万八千里吗?我首先是肯定贾宝玉的性格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不过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用得不彻底罢了,不是严格的罢了,怎么能说我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透顶的人性论”呢?毛主Xi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难道我主张过有“抽象的人性”,有“超阶级的人性”吗?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和说法,何况我讲的是典型的某些特点,还并不是人性,不等于人性。
关于林黛玉我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种理解虽然是简单的,不完全的,或者说比较表面的,但也并不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林黛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点在发生作用。
后面我又说:
林黛玉这个性格的特点,比较贾宝玉是更为具有强烈的时代和阶级的色彩的。随着妇女的解放,这个典型将要日益在生活中缩小它的流行的范围。然而,即使将来我们在生活中不再需要用这个共名,这个人物仍然会永远激起我们的同情,仍然会在一些深沉地而又温柔地爱着的少女身上看到和她相似的面影。
(同上,据1958年初版)
这些话也是有错误的,第一,今天如果有人称谁为林黛玉,也是一种侮辱;第二,“永远激起我们的同情”,不对,将来的读者将日益不能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觉得太畸形了,因而就会日益减少同情,以至不同情;第三,将来“深沉地而又温柔地爱着的少女”和林黛玉大不相同,根本不相同,人们不会从她们身上想到林黛玉。
但是,尽管有这些错误,也不能说我是在宣传“永恒人性”,宣传“资产阶级腐朽透顶的人性论”,因为我大讲了林黛玉性格的特点具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而且将来不再需要用这个共名。
我说过“永远激起我们的同情”,但这是指读者对林黛玉的同情,不是说林黛玉性格的特点或林黛玉这个共名“永远”存在。这也是属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用得不彻底的错误,而不是主张有什么“永恒人性”,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李希凡同志是一直反对和批评我对于某些文学上的典型的看法的,我应该感谢他,尽管他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对我的错误有些拔高和夸大,但作为一种忠告,一种警告,还是好的,提醒我不要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要滑到人性论的泥坑中去。但是,李希凡同志对典型的看法,虽然从未用过“共名”二字,是否也曾经有过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问题呢?过去他写的文章也是有过的,他这样论过典型:
在许多场合里,就不仅仅表现出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本质,而是更深广地表现出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征,使其形象成为全民的全社会的性格。
“全民的全社会的性格”,这不是比我的看法和说法更甚吗? 关于林黛玉,他又曾这样说过:
这一悲剧性格所进发出的光辉,却永远在人们的想象里闪耀着。
这不是和我的“永远激起我们的同情”的错误说法差不多吗?
然而我们能不能因为李希凡同志过去写的文章有这一类缺点和个别论点的错误,就批评他是在宣传“永恒人性”,宣传“人性论”呢?我看,恐怕不应该这样,因为他总的说来,还是在努力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我举出李希凡过去文章中的这些缺点,有三个意思:一是说正确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研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允许人家犯错误;二是有了错误当然应该批评,但是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根据文章的主要倾向来下判断;三是李希凡同志在批评别人的错误时,似应对自己也曾经有过的类似的错误有几句话交代一下,不写在正文中,也应加个小注声明一下。
我的《论<红楼梦>》错误是不少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主观上还是努力在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用得好不好是另一问题)。如果不仅仅就某些个别的论点(当然是比较重要的论点)来看,而就全书来看,这样的努力是应该看得出来的。
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某些典型,是有这样一种现象,它们在生活中的流行和运用不限于一个阶级中的人。这种现象到底应该怎样解释呢?是可以容许研究和讨论的,而且我认为是可以容许研究失败和犯错误的。记得李希凡同志有一种解释,说是借用或比喻(大意如此,记不准确了)。
还有一种解释,说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用马克思的话)。有不少典型是可以用这些理由来解释的,但也有极少数的典型不能用这些理由来解释。如堂·吉诃德,说一个主观主义严重的人是堂·吉诃德,怎么能说是比喻呢?又怎么能说主观主义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呢?我企图解释这种现象,就提出某些典型的特点不限一个阶级的人才有,但整个典型当然仍是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的人物,而且就是这种特点在不同阶级的人身上,也是既相同或相近,而又不相同的。
相同的仅仅是在主观主义的共性这一点上,不相同的是不同阶级的主观主义本身却有不同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色彩、阶级特点。对阿Q,我大致也是这样解释。
李希凡同志好象在有的文章中也承认阿Q精神不限于一个阶级的人才有,但认为时代很有限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却觉得好象还长久一点。说到这里,好象主要在时间的长短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而并不是在限于一个阶级的人物了。
我的这种研究可能是失败的,但李希凡同志仍然坚持说我是宣传什么“永恒人性”,“万古不变的人性”(记得他过去批评我的文章有这样的用语),我觉得不够实事求是,是不符合我的错误的实际情况的。
“共名”那种说法并非由我提出的,是过去文学理论中向来就有的一种说法,我现在已记不清最初是在什么书上读到,就接受了那种说法。对过去的文学理论,包括它的用语,是应该严格审查的,可能这种用语就不很科学。但不管这种用语妥不妥当,过去的文学典型有这种现象,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列宁就曾说过:
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老是躺在床上,制定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
这些话如果不是列宁说的,将受到什么样的批评!但列宁是看出有这样的典型的,有这样的现象的。当然,列宁没有说明为什么有这种现象,但似乎并不是用“比喻”说、“统治阶级思想”说所能解释吧。奥勃洛摩夫精神恐怕就不能说是一种思想(虽然它有思想基础),而是一种精神状态,象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那才明显地是一种统治阶级思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驳斥杜林的谬误的“永恒的真理”说的时候,以道德为例,说不存在“永恒的道德”,但是,恩格斯同时说:
……上述道德论,表现了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这就是说,它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就此而言,它们已不能不包含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的道德论,必然多多少少互相吻合。
(据1956年版本,不知新版中有什么修改没有?)可见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说不同的阶级的人有时在某些点上有相同之处,不一定就是“人性论”,不一定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观点”。恩格斯这里讲的就是封建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三种道德,可以包含许多共同之处,虽然总的说来它们是大不相同的,“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何况我在讲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时,紧接着就讲:这种相同或相似之处仍然有不同的阶级性。
既相同又不相同,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这正是许多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辩证法,许多事物的复杂性。
四、李希凡同志在批评了蒋和森和我之后,称他和我(当然也可能还包括别的人,但首先是我和蒋和森)为“一些口头上装饰着马克思主义词句的理论‘权威’们”,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斟酌的。蒋和森的文章有欠妥的观点.“永恒主题”说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当时发表文章时,还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完全不知名的青年,称他为什么“理论权威”,符合实际吗?至于我,我也有意见,口头上装饰着马克思主义词句的理论“权威”,就是资产阶级“权威”,修正主义“权威”,这样说是完全否定了我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企图运用来研究文学的努力的。
我原来并不写什么理论批评文章,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以后,由于工作需要,由于想宣传毛主Xi的文艺思想,才开始写一点理论批评文章(当然,宣传得并不好)。
解放以后,特别是来文学所,自己又乱七八糟多读了一点书,写文章时希图有自己的见解,甚至写解释毛主Xi的文艺思想的文章也希图有所发挥,结果就写出了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
对我这样一个犯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在今天党正在号召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时候,是把我划入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资产阶级那边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边去,还是把我留在无产阶级内部来教育好呢?我怀疑称我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理论“权威”,恐怕不大符合党的干部政策,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我完全不是否定我写的文章和我的思想中还有错误思想。但这并不等于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一个修正主义“权威”。
五、最后,李希凡同志在前言稿第六页最后,写了这样一小节结论式的话:“这是文艺黑线为复辟资本主义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一次演习”。不知道这是对从第五页到第六页全部文字的总结,还仅仅是这一小节文字以前的一段叙述的总结。
如果是前者,把蒋和森和我写的有错误的文章算成“文艺黑线为复辟资本主义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一次演习”,似有些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看样子可能是后者,但其中“关于曹雪芹卒年及其祖宗的繁琐考证”,并非来自“文艺黑线”而参加讨论的非党人士甚多,说他们都参加了“文艺黑线为复辟资本主义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演习”,也似乎上纲高了一些。
我写《论<红楼梦>》,是我自己研究的结果,其中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研究的过程中并未接受周扬等人的什么“指示”,写完后发表前也从未“送审”。因为我认为那是学术研究文章,用不着经过他们“批准”。《文学遗产》发起那次生卒年讨论,也不是来自周扬。 《文学遗产》由文学所办,那件事也主要由我自己负责,至于它的由来,说来词费,就不说了。
原谅我写得这样长,这样罗嗦,想把问题说得比较清楚,就写长了。另外,读时有些小意见,随手写在原件上,所有这些意见和批注的零碎意见,都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敬礼!
编者附记:这封信是何其芳同志于一九七二年、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写成的。本刊这次发表,未作任何修改,目的是怀念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有过一定贡献的何其芳同志。在此,我们对提供这封信,并在文字上作了校勘的何其芳同志家属牟决鸣同志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