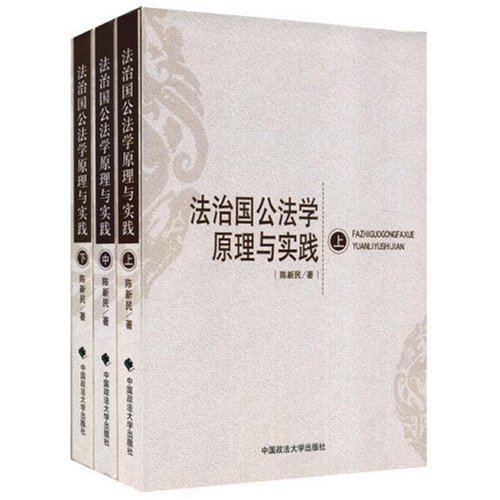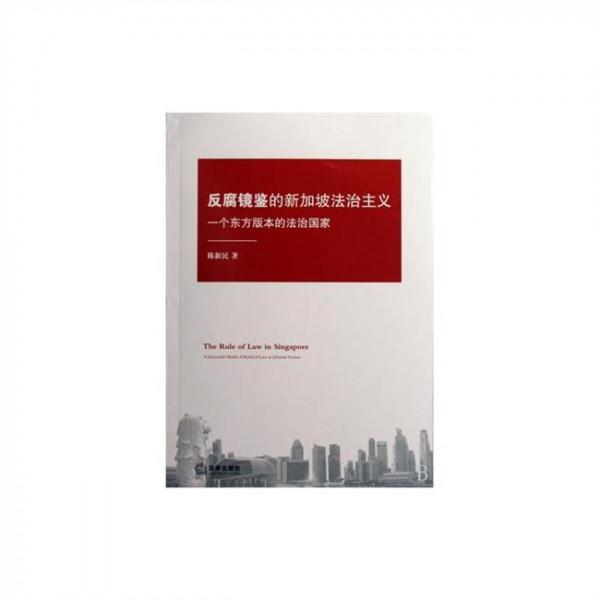刘军宁依法治国 刘军宁:从法治国到法治——对依法治国的再思考
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一切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的现实课题。在我国,人治与法治孰优孰劣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学术界的讨论焦点已从人治与法制之争转到(依)法治国与法治之争。
对法的认识,开始由“法制”向“法治”转变。随着讨论的展开,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类的概念也使用得越来越多。然而,法治(the rule of law)与法制(legality、legal system)、依法治国(the rule by law,亦称以法治国,依法而治)和法治国(rechtsstaat,legal state, law-based state,亦称法律国家)这三者貌似相同,实则有着重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常常被忽视或是被混淆。
显然,对这些字面含义相近的概念,尤其是对(依)法治国与法治作深入的剖析,无疑是深化对法治的认识所必需的。
一、源流
法治作为一种法律学说和法律实践,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逐渐形成的,它来自于特定的法律思想与社会实践的频繁的、积极的互动。从历史实践看,法治的形成得益于现实中存在的某种权力平衡,得益于统治者无力集中起绝对的权力,及因此出现的多元的权力结构。
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法治体现了反对专横的立场,包括反对统治者的专横行为和反对带来专横后果的立法。法治要求一切行动都必须服从于法律。为了确保法律是正义的,法治的鼓吹者主张一切法律都必须由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机关来制订,而且这些法律必须合乎自然法的普世原则,即尊重基本的(天赋)人权。
在中世纪之初的英格兰,法律的观念已显然强大到迫使国王只有在得到其最有权势的臣民(封建领主)的同意才有权进行统治。
由于王权的软弱和社会中存在多元的权力,尤其是领主的权力,1215年约翰王为取得发动战争所需的征税权,在领主们的逼迫下不得不在《大宪章》上签字画押。这一宪章成为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法律文件。
在《大宪章》出现之前,国王握有法律的权力,甚至可以说,国王就是法律。但有了《大宪章》之后,国王必须承认他也得服从于这一法律。《大宪章》本身并不是具有多少民主内容的文件,但它给王权的范围立下了界标,肯定了个人所应享受的人身权和民事权,从而表明这种为权力勘定范围的工作只能由法律来完成。
在西方世界中,另一个类似于《大宪章》的法律是1222年匈牙利的《金玺诏书》,但影响不及《大宪章》。尽管《大宪章》所带来的改革十分有限,但它却标志着法律对专制权力的胜利。1因而,它也为法治在近现代的西方社会,尤其后来在美国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从思想渊源上看,法治的形成与12、13世纪逐渐盛行于整个欧洲的高水平的法律意识及某种超验的法律价值观有关。在古代,这种超验的法律价值观存在于神和自然正义之中;在现代,这种超验的价值观则体现在对人权、正义、自由、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坚定信念之中。
法治的思想起源于自然法,得到了盛行的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持。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就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自然法,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由政府制订的法律不过是人类对这些自然法则的发现,因而是次要性的法律。所以,法治承认人类所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
法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来自于这样一个观念:在一切人订的法律之上还有时时处处适用于每个人的普世法律。这意味着一切人订的法律都必须服从于来自自然法的根本法律原则,而且不因时间和场合而转移。
在这一自然法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承认有绝对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因为他说,“谁让法律来统治,可以说是,只让上帝和理性来统治,但谁要让人来统治,那就要加上兽性的成分。
”后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这种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塞罗给自然法下的定义是:“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理解的规则,它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人,是稳定的、恒久的。
……要求修改或取消这样的法律是亵渎,限制它的某个方面发生作用是不允许的,完全取消它是不可能的;我们无论以元老院的决议或是人民的决议都不可能摆脱这样的法律。……一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律将适用于所有的民族,适用于各个时代。”2
同样,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议会派的胜利与其说是民主的胜利,不如说是法治的胜利。这场革命的结果重新确定了谁是英国的立法者。是洛克的理论使得在光荣革命中成为主权者的英国议会免蹈成为新的专制者的覆辙。
他担心,由主权者(不论是君主或议会)制定的实在法若不受理性、自然、上帝、正义等的约束会危害自由与财产权。所以,洛克把英国议会看作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受托者,而且坚持认为,议会无权通过立法来废除这些权利,哪怕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
这种新的政治哲学彻底改变了主权者与法律的传统关系。根据这一政治哲学,主权者为了行良政固然需要武器和法律这两样东西,但主权者的政权应来源于法律,而不是武力。一旦主权者只能用武力进行统治,他就不再是主权者了。
易言之,主权者必须以符合正义和人权的法律来作为使用武力的依据,而不是靠武力来作为使用武力的依据,靠武力来推行违背自然正义的法律(即恶法),使法成为纯粹服务于行使武力的工具。因此,统治和法律必须以人民的同意和保护人的权利为基础。
法治思想起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法律学说。这种观点不仅把法律看作是对自由的约束,而且更把法律看作是对自由的保障。对洛克这样的自然权利哲学家来说,这种更高的法律包括在自然秩序下属于一切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对于人的生存至为重要,不仅不能让渡,而且自动构成对统治者行为的限制。
这一学说为法国的《人权宣言》、英国的《权利法案》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因融入美国宪法而获得了法律效力。正是有了这种自然法理论的依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得以理直气壮地推翻由国会和州议会通过的,但被认为与自然法中的自然正义和天赋权利的某种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法律。
随着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法治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是专制与无政府的对应物。
与“法治”的起源不同,“法治国”至少在其起源之初,纯粹是个德国的概念。法治国的概念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3但这里的法律不是来自“法治”中的自然法,而是来自人民的联合意志(或者说公意)。
法律是作为主权者的立法者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正义的产物。推言之,法律服从于立法者的权力意志,而非自然正义。然而,在德国和欧洲其它地方,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很少象在英国那样对自由秩序的稳定起着积极的维护作用。
在许多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或者说以民族主义面貌出现的国家主义)搀和在一起。在德国,自由主义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尤为明显,其后果是把民族国家和主权者的地位抬得太高最终导致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National Socialism)在二十世纪的崛起与得势。
康德的自然法与卢梭的自然法一样都搀和进“公意”和“人民主权”这类极易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西。
4与自然法理论相对立,实证法把法律看成是国家的命令或者主权者的意志表现的概念。卢梭就认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是出自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命令。5
由于康德的国家与法律理论与卢梭是一致的,因而其政治法律学说也显现深度的“悖反”,即其政治哲学的立论表面上是自然法的,而其在国家与法律学说的神髓则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按照康德的看法,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只能由立法机关多数人的意志加以保护。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抗拒这种意志。在康德的理想政治体制下,忍受立法权的滥用是人民的义务,即使他们忍无可忍。主权者是一切法律的渊源,他本身不会作恶。由于康德认为只有实在法才具有强制力,所以,他为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6在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陆的君主专制或独裁统治之下,法治国的思想意味着把立法权交给(共和政体下的)议会或(君主制下的)君主。在德国各州的专制统治之下,情况更是如此。“法治国”的思想与实践对西方之外的世界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许多地方超过了起源于英美的“法治”的影响。
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和作为主权意志的法律为后来法律实证主义在德国的“昌盛”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养分”。其最正面的实际后果是魏玛宪法和魏玛共和国,最恶的后果则是第三帝国。新康德主义法学在本世纪初的重要人物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希特勒上台前,是海德尔堡大学法学教授,从1920年到1924年期间曾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出任魏玛政府的司法部长。
他根据康德的学说,提出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法律哲学,认为法律最终在于实现正义,但正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观念,最后必然依不同的政治信仰为转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超人格主义这三种价值观代表三种不同的政治信仰,无法科学地加以论证。
这种相对主义教导人们:没有一种政治观点是可以证明的,也没有一种政治观点是可以驳倒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大大地修改,甚至可以说放弃了原先的相对主义法律思想,从康德的相对主义、实证主义转向自然法学。认为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就是法律”的观念,有利于纳粹政权的暴行;法律应具有绝对的价值准则,在实在法和正义原则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应服从正义原则。7
法治国概念的理论化是由实证主义法学,尤其是由纯粹法学来完成的。这一法学流派认为,法律的最高渊源不是来自自然法的普世法则,而是来自立法者的意志,在国家的立法权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法律渊源。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法治国的概念已成为大陆法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证主义法学相信法律必能由国家制订,相信法律的效力来自国家惩罚违法行为的权力。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凯尔逊的纯粹法学也是以康德的不可知论为重要的思想渊源。
纯粹法学不关心法律中“应然”的价值问题,只关心实然的事实问题。这种“纯粹”法学是要从法律中摈弃一切“不是法”的东西,包括伦理、宗教以及形而上学,更包括自然法中作为普遍规律的高级法( higher law )的思想,以及自然正义和天赋权利等超越立法者意志之外的东西。
以意志界定的法律的极端后果,就是直接诉诸意志,绕过法律,直到废弃法律,关闭法律学校和法学专业,取缔法学家、律师乃至法官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