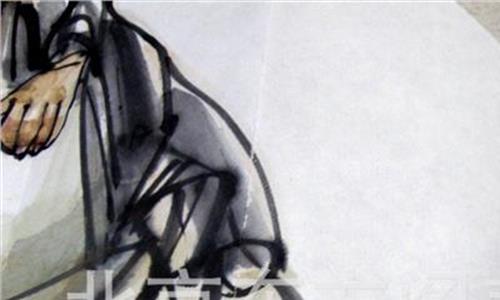画家史国良 【画家印象】史国良:走入佛门的国画家
出生于1956年的史国良,没过几年就赶上了那个全民饥荒的年代。父母每月70多元的收入,在那时是个令人艳羡的数字,可要用这些钱来养活7个孩子又谈何容易!小小的史国良已开始饱尝生活的艰辛:在臭烘烘的垃圾堆里乱扒,瞪圆了眼睛盯着那些能换几个小钱的破铜烂铁、废纸布头;到菜场和郊区捡菜帮和挖野菜;蹲在建筑工地的废木料堆上,顶着烈日一颗一颗地起钉子,再一颗一颗把它们砸直……
忍饥挨冻吃苦受累都没有什么,最让少年史国良受不了的是因贫穷而遭受的种种屈辱。妈妈把姐姐不能再穿的衣服染成黑色或兰色让史国良穿。他脚上那双露着脚趾的鞋已经够让同学们耻笑了,再穿上姐姐的衣服,他看到了更多的鄙视目光,听到了更加肆无忌惮的讥讽和嘲笑。他曾经反抗过,可换来的却是围攻、拳脚、唾沫和辱骂。
史国良自小就痴迷画画,可一直到上了师范学校,还是难得有钱买宣纸和颜料,只好在旧报纸上画画。母亲给他少得可怜的零花钱,他一分一分攒起来,当终于可以买回一点宣纸和颜料时,他便有了一个极佳的心境,感觉整个世界都明艳起来。在渗化多变的宣纸上用墨彩作画,真是奢侈的享受。
1977年,史国良的作品参加了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的巡回展并被文化部收藏。197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85年,他转业到北京画院,不久被评为国家一级画家。
那年正是中国画坛最为活跃动荡的一年。西方美术作品及理论大量介绍到国内,一些画家标新立异,以画出谁也看不懂的作品为能事。更有人大声疾呼:中国画可以休矣!中国画坛一时云遮雾罩、乱花迷目。这对于一直酷爱写实中国人物画的史国良来说,自然是一次强烈的冲击。但是,在沉思默想之后,他毅然坚定了走中国写实人物画之路的追求。当然,他也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艺术视角和感觉,为此他想到了西藏……
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史国良用他惯有的艺术眼光细细观察:各种祭香引燃的氤氲烟气,弥漫在大殿内外;一盏盏酥油长明灯闪闪烁烁,使布幔错落、神像林立的大殿笼罩在一片神秘而肃穆的昏暗之中;鱼贯而入的藏民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散开盘起的辫发,对着一个个神像下跪磕头;那喃喃的祈祷声和咚咚的磕头声,更衬出大殿的安谧……
史国良身不由己地也跪倒在佛的脚下,祈祷佛能点亮他的心智之灯,让他能用笔墨语言去揭示佛门内外文化的博大精深,揭示那无处不在的人性之光。也许就在那一刻,他已无可避免地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后的日子里,史国良画朝圣路上的藏民,画经幡飘动的佛堂,画神情凝然的喇嘛,画藏传佛教的祭祀大典,画一丝不苟勤勉刻经的信徒……最后画出了一个《空门系列》。
《刻经》获国际大奖后,史国良名声大噪。当年12月,他应温哥华大枫叶画廊之邀,赴加拿大举办画展。画展相当成功,可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卖画的钱差不多被画商完全侵吞了。为此,他拒绝了所谓的再次合作,独自在加拿大留了下来。
之后不久,由于伤病,他又把妻子接到了温哥华,二人白手起家,开始了全新的奋斗生涯。曾几何时,正是靠着妻子刘玉梅一双被泔水泡白浸肿的手,史国良才得以能够静下心来画他的画。画价日渐看涨,终于有了他们的豪宅和房车,这便是史国良称之谓他人生的第二个圆。如果就这样徜徉在这个圆里生活下去,那该是多么安逸啊!
史国良一愣,心想: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当和尚,只不过经常去西藏,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罢了。
“其实,你不妨作个画僧,让佛开启你的艺术心智之门,然后用艺术来弘扬佛法。”
一句话,使史国良的脑海闪过一长串名号:贯休、惠崇、巨然、怀素、石涛、八大、虚谷、弘一……他们的艺术之光,曾让他何等着迷!他心动了,认真地说:“让我想想吧。”
史国良认真地想了,想得很多很多,也想了很久很久。他有千万条理由不出家,却难以抵御画僧对他的诱惑。1995年10月,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无奈的刘玉梅带着儿子,怀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心情,亲自把挚爱的丈夫送到了美国的西来寺,开始了剃度前那磨人的集训。
1996年9月27日,是史国良又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经过几乎整整一年寺院生活的磨练,他终于在这一天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子们一起接受剃度。闭目合掌跪在地上的史国良,看上去十分虔诚、安静,然而他的内心却翻腾着狂涛巨浪。
将近一年的训诫生活,再苦再难他都毫不犹豫。然而到了此刻,一旦开始受戒的钟声响起,他就要真地抛开红尘中既得的一切时,他突然感到浑身发冷,心口堵得厉害。就在这时,他听到“咣”的一声,那悠长的钟声立刻把他的心给震碎了。他竟然不管不顾地大声嚎哭起来,哭得自在极了,放任极了,鼻涕、口水甩得四散,五官全都扭曲变形。世界仿佛在这酣畅淋漓的痛哭中消融并化解了。
也许是个性和学识修养使然,画僧史国良在任何场合都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多情的人。不错,他已经出了家,佛家诸多大戒他是必须操守的,但他作和尚不为别的,而是为了继承中国历代画僧的衣钵,为了将中国写实人物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可是一个不知情为何物 的人,又怎能成为艺术家?
就在他受戒之后走出戒场时,心中空落落的,却下意识地给刘玉梅拨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刘玉梅立时哭成了泪人儿,说要和儿子马上去看他。他急切地说:“不不,我已经正式出家,你不要来!”说完“啪”地把电话挂断。刘玉梅当然知道自己深爱的人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中,立即收拾行装,带着儿子起程了。
一见面,俩人忘情地相拥在一起,久别的思念使语言变得苍白。可是纠察师傅的一声断喝,犹如炸雷惊醒了他们,方知他们已是僧俗两隔,再不是从前了。
虽然已经离婚,虽然史国良多次由衷地劝刘玉梅寻找新的幸福,虽然刘玉梅身边也不乏追求者,但她的心里却始终满盛着史国良。这也难怪。史国良是在中央美院就读研究生时认识的刘玉梅。两情相悦,他们很快由相识、相恋到结婚。
婚后,二人携手并肩、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多少个令人难忘的日日月月啊!如今一切都那么美好,可是……1999 年春节,刘玉梅回国探亲,满怀期盼去看望史国良。在史国良那佛家气息浓郁的精舍中,她神情无忌地望着眼前这位和自己患难与共15年的男人,脱口而出:“国良,还俗吧。我们复婚,还象过去那样。”
“阿弥陀佛,我不能。”
“为什么?”刘玉梅期盼的眼光暗淡下来,泪眼迷蒙,“现代人作画僧,你不觉得离现实太远了吗?一盏孤灯,随时可能被风吹灭,他又能照亮多大的地方?”
“这些我早想过了,越是没人作的事就越有意义。再说,出家难还俗更难,你不想让我作一个俗不可耐的人吧?”
一向尊重自己爱人意愿的刘玉梅,只得用泪光盈盈的双眼盯着史国良说:“好吧,我在尘世间等你……”
在美国西来寺修行两年之后,已经谙熟佛法的史国良回到了国内。他的艺术之根和艺术灵感都在中国。对于半路出家的史国良来说,佛门内外的风景都已不再陌生。门内有佛家必须把持的清规戒律,而门外则有社会必须遵守的法纪纲常。
进出于佛门内外,他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感悟,这使他对生活有了比常人更深一层的理解。他要用他的艺术去深刻揭示人生,提示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毕竟已是僧人,弘扬佛法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而佛教的根本要义,不正是“仁爱”二字吗?从这一点来看,史国良真是把弘扬佛法和自己的艺术追求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作为中国当代唯一一位画僧,慧禅法师自然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加之史国良认为他是画僧的传人,有必要让世人了解当代画僧的真实面貌,也算是对佛门的一种贡献,因此而不放过任何一次宣传机会,近年来他可谓声名鹊起,画作的价位亦滚雪球般往上窜升。
于是, 因为走红,谤言四溢也就在所难免。有人说史国良善于炒作,也有人说史国良到处表演等等。就连《光明日报》在一篇肯定史国良的文章《从史国良作品走俏看艺术市场走向》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我丝毫不怀疑史国良出家的虔诚,但是其中是否也包含了某种运作策略?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这两种看起来似乎非常矛盾的东西,在史国良身上不可思议地融合为一体……”看来,炒作的嫌疑是无法避免的,那就让人们说去吧!
好在史国良有大量的作品摆在那里。他的画作贴近生活、题材宽泛、立意新颖、启人遐思、构图精当、笔墨洒脱而厚重,作品不止是充满禅意,更多的倒是一种人文关怀和爱心,堪称中国人物画坛写实画派的重镇。
如今,史国良在北京德胜门附近一片杂乱的居民区内,拥有了一座独特的小院。虽然院落并不阔大,房屋也并不宏丽,但的确别有洞天。可闻香火缭绕、佛乐轻唱,宗教色彩弥漫在这小小“寺庙”的各个角落。和他在潘家园的精舍相似,这里的陈设既古朴又现代,佛教文化与绘画艺术在闹中取静的空间和谐地融为一体。
画僧已经作了许多年,许多的苦楚已不觉其苦,或者说一切都已习惯。当代画僧的路该如何去走?最终又能走出个什么结果?史国良和我们一样都不得而知。兴许若干年后中国画坛又出了一个石涛或者八大,那岂不是中国画坛的一大幸事?当然也可能有八面来风,最终吹息了这盏踽踽独行的灯而再也无法点亮。还是让我们以平常心去耐心地等待和观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