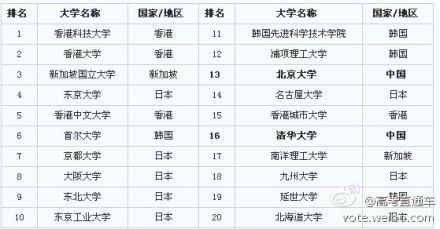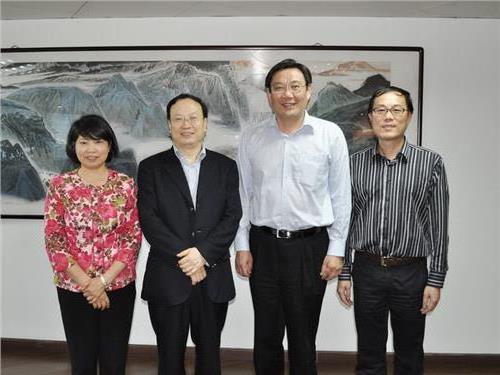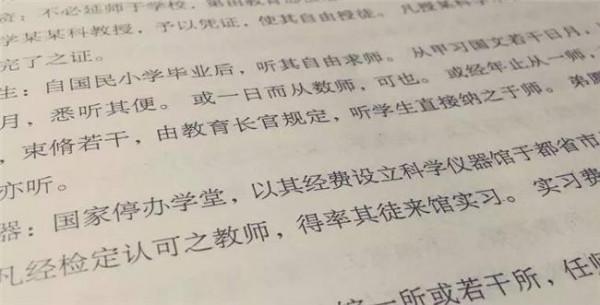周济贺信 邹恒甫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周济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2007年4月6日, 我, 邹恒甫, 突然收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任院长张维迎的一封英文信(请看附件).
维迎的信通知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4月4日院长会议决定, 我从2007年5月1日起, 将不再享受学院的任何待遇, 并开除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职务, 把我的人事档案移交北京大学人事部. 我对此感到既惊诧又好笑. 怎么在堂堂正正的中国第一大学竟然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
在此之前, 维迎并没有通知我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规定, 不许我在其它学校免费地,自愿地办教育事业. 事实上, 我从1990年开始就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先在武汉大学用自己和朋友的钱办学. 1997年, 由邹至庄教授推荐, 我同时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也帮忙办学(没有任何工资待遇).
这些事情您在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时早就知道了, 因为我也帮贵校的张培刚, 林少宫, 李楚霖等老师和徐长生同学办学. 1998年8月, 我在中山大学偶然遇到当时刚离开CCER的张维迎.
他告诉我他已就任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助理职务, 我有点惊讶. 但一想到他在CCER 好几年的内斗中连一个CCER的副主任也没有搞一个, 我也理解他的处境和痛苦. 他突然提出邀请我到光华管理学院办学. 我立马答应了. 这是我的本性, 您早就知道.
我于1998年12月12日到北京大学人事部陈文生那儿报到, 在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我在北京大学的折腾您是知道的. 我的办学理念对CCER, 北大经济学院, 清华, 人大的冲击您也听田国强讲过, 因为您当时也想让田国强回华中科大当经济学院的一员干将,而田国强也在武汉和美国来回奔波.
在北大干了两年之后, 我的主要任务已完成: 跟国际主流接轨的经济学课程都已开设,我的许多学生也都到北大任教.
2001年, 我又开始天马行空, 到浙江大学不要任何待遇地帮姚先国一点小忙. 这一切, 张维迎和光华管理学院的所有老师都是知道的, 他们也都是非常理解甚至支持我的``革命干劲”. 其实, 维迎也非常希望我多离开北大. 否则我在他和许多海龟的课堂里闹得他们够苦的了: 他们都知道我的一张大嘴的辛辣和刻薄, 动不动就在他们的课堂里讲他们没有讲对, 误人子弟!
2004年3月28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张维迎通过电子邮件突然要我给他家打电话或打他的手机:
我们好久没有通讯了.我3月29日看到他的邮件后, 作了如下回复:
我打电话到他家,他一听到是我的声音就说:他现在想要当光华的正院长, 北大的副校长也没有劲.然后,他说他一定能把厉以宁老院长搞下马, 现在非常需要我这一系主任的一票.我们还约好在5月18日见北大学校主要领导.
我放下电话不久, 芝加哥大学的刁锦寰老先生来了电话: 恒甫, 你一定要帮维迎当上正院长! 维迎和恒甫在北大光华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呀! 刁锦寰老先生后面的话就有点不雅致了:哎呀, 厉以宁怎么不象我这样犯一下心脏病啊!
他中点风就好了,轻轻地中风也好啊! 接下来几天, 我收到了许多拉我这一票的朋友的电话.我听了刁锦寰老先生的话后几天都不怎么高兴, 其实厉以宁老院长这边的人在2004年3月以前对我是不太好的: 毕竟维迎和恒甫在北大光华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呀!
但他们不知道我把维迎在全中国嘲笑讥讽得没完, 而维迎从不认为我是他的人. 我有天马行空的本性. 我绝不参加他们两边无聊的内斗. 惨啊, 知识分子在北大光华斗得如此残酷. 我逃得远远的. 2004年5月18日, 我跑到深圳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维迎也跟踪而来. 他打通了我的手机, 我说我在武汉.
他一定非常失望了. 我此后只见过维迎一次,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斗争. 但维迎是非常喜欢斗. 每到一处, 他 必然跟第一把手斗! 这也是他的一绝. 林毅夫和海闻一定是怕维迎在CCER的斗争精神的. 维迎那里有时间搞正经的学问, 他同时搅得别人也不能好好地搞学问!
中国大校里的悲哀啊.
2005年, 两边斗的结局是吴志攀兼光华的正院长,而维迎是常务副院长. 我约了吴志攀长谈了一次. 志攀一贯地礼贤下士, 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光华楼421房间). 因为维迎常务副院长在2005年6月份一定要我不当系主任了, 而改由新来的,刚报到的蔡洪滨当.
这也奇怪, 我1998年加入光华时, 我只想当一个数理经济学班的班长, 而维迎却专门要给我搞一个新的应用经济学系的系主任干. 现在, 他要我不干系主任, 搞些国际学术交流, 办好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这一学术刊物.
维迎常务副院长还不想同我彻底翻脸, 因为他离正院长还有一小步. 我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说给吴志攀听了. 志攀听了以后对我非常好: 武汉大学是你的母校, 你只管干; 北京大学是一个好平台, 你要发挥作用!
2006年, 维迎当上了正院长. 他很快给我来了如下的EMAIL
通知:
我只好最终哑口无言地服输: 我的系主任被他和蔡洪滨合谋拿掉了! 我每年在光华的地下室第五室上完课后, 就在我五道口的家里辅导我的研究生. 维迎从来找不到我; 而我也从来不找他: 我也就成了他的``Long-Time-No-See”的同事. 喜欢我的光华人总能找到我, 而我也每天请他们吃饭, 因为我在世界银行两个月的税后收入加上福利补助比他们在中国一年的税后收入要高多了.
您知道, 我对所有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了. 不跟我学的学生在美国申请博士奖学金, 我是最帮忙的: 如今年北大的沈吉(复旦本科)到耶鲁, 清华的杨明(南京大学本科) 到普林斯顿,复旦的张爽到康乃尔, 我都是从世界银行打电话给许多学校的教授, 高度地表扬他们的成绩. 我武汉大学的学生, 许多人不争气去投行, 我现在这几年都让他们去比较差的学校了.
最为重要的是: 我在北京大学呆的时间比许多光华流动教授如陈荣, 徐淑英, 刁锦寰…他们多多了!
而更为糟糕的是张维迎带头当许多独立董事, 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 我去年一次讲座也没有在社会上作过, 而我前年一年仅仅在北京给青岛的中层干部作了唯一一次报告.
他们给我两千人民币, 我都给他们买了阅读资料. 他们非常奇怪地问我, 为什么光华的其他老师收那么高的讲课费. 我说他们还没有脱贫. 由于许多人通过我打听他们的收费标准,我才知道张维迎一次讲座收费有时是税前六万元人民币.
我到苏州大学免费作报告,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 一定要给我上万的人民币, 我是坚决不要. 他们说, 光华的周春生给我们讲课,一小时一万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 我马上打手机给春生, 要他和张维迎讲良心.
我们都是农家子弟, 怎么能如此地剥削中国人民. 我在世界银行是扶贫的, 您知道我已干了十八,九年了. 我们世界银行给Nobel奖的大经济学的(三小时)讲课费也只有三千美元! 这维迎和春生的道德和良心在哪儿呀?
他们许多正教授在光华呆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助教授和副教授不可能到处跑, 因为他们没有tenure). 不信, 请您问光华的前副院长朱善利和现任副院长武常歧. 他们还开后门搞学位班, 拉政府官员当兼职教授打钱……这些我是不好意思说多了. 请您派一人去海淀税务局查一下便一目了然了.
不料, 维迎的飙还没发够! 两个多月前, 他EMAIL通知我: 从5月1日起, 恒甫再也不是光华的人了! EMAIL 还不够, 他还把他签名的同样的一封信用DHL快递到世界银行. 这实在有一点点欺人太甚了.
我庆幸, 我还有世界银行的每年九个月的饭碗, 尽管我在世界银行也被大家认为我不是全职员工:近七年来, 世界银行只给我发九到十个月的工资. 另外两到三个月,我必须到中国去摸钱. 我的好朋友和学生都知道, 我是不到社会上摸钱的, 而我北大的工资实际上不多: 我是1998年加入的北大, 老人老办法.
我希望维迎在网上公布我在北大的收入, 以正视听! 而我的董辅礽老师可怜我, 专门为我设了一个董辅礽讲座教授.
但此讲座教授的捐款单位是从不按时打钱的. 到现在为止, 2003年的工资还没有发给我. 因为董辅礽老师是我的恩师, 我不要一分钱也得要这一光荣称号. 现在维迎把我的这一光荣称号也剥夺了.
他还命令我把办公室马上空出来(现在早已空出来了!). 他又命令我必须在8月31日时把我在五道口的房子空出来.
周济部长, 我们都是老熟人了. 我不应该用我的这点小事来麻烦您. 我在中国从1987年到今天2007年教书所受得苦您是非常清楚的. 外人只看到了我风光的一面啊! 但是, 北京大学和中国的所有大学都不应该让维迎这样的领导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们手下的教授啊.
我本人好办, 在全世界都能找到饭碗. 我今年四十五岁, 我的年龄加工龄已六十三岁. 我可以拥有所有福利和保障地在世界银行退休. 但想想处于跟我不一样地位的全中国的大部分教授: 当他们受到维迎这样的领导打压时, 他们到哪儿去找公道啊? 所以, 我一定要出来发表此公开信.
我就不信中国教育界, 特别是以自由民主为旗帜的北京大学, 能容忍张维迎这类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颠狂分子肆无忌惮地折磨他们手下的,被领导的教授. 我的例子也不是单独的一例: 在中国的许多学校里, 领导对教授都是非常不客气的.
这实在让我们(包括您)这些所谓的海龟看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天壤之别: 在美国, 学院的院长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吗?! 美国的院长是服务员: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 Nobel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 对我, 梁小民, 何帆和全中国人民说过了:他当院长时,他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服务员.
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在哈佛念博士时(1983年开始),他先是我的年轻的系主任,然后是我的年轻的院长.有一天下雨,他把雨伞给了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而他自己淋雨.后来有一次,他当院长后,在路上他看见我穿的衣服太少,他在第一时刻
便把他的西服扔到我身上.这也是他的风格:每次上课时,他都把西服扔在(不是放在)地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