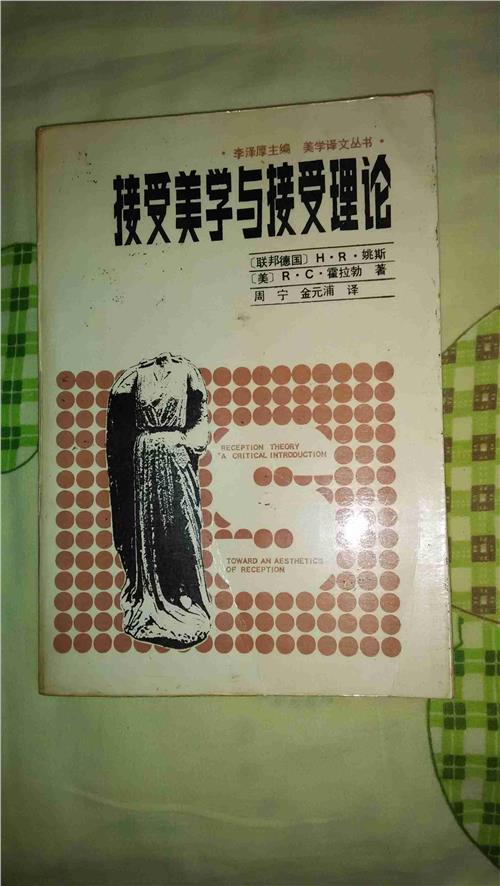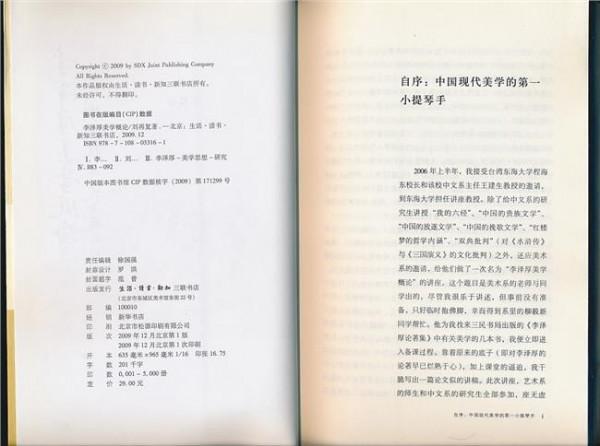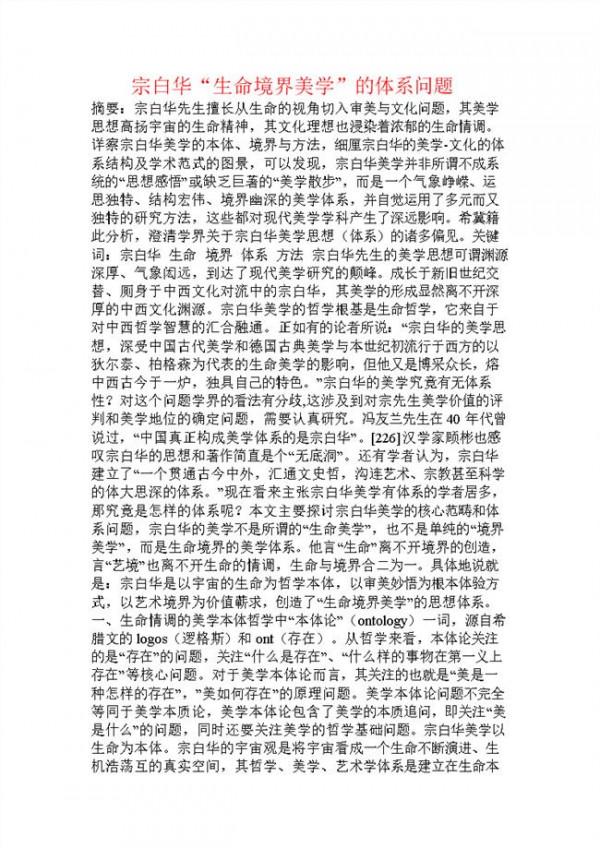朱良志的情人 为人生美学 访美学名师朱良志
摘要:朱老师关于中国美学及美学教育的论述,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提高自身美学修养,提升生命的境界很有参考意义。
我们自古以来就以所谓广义的艺术或审美来取代宗教的地位,通过人的修养和境界的提升,来使人的生命、生活更有意义。
人还是要有一点趣味的,没有趣味的人生过着干什么?过得匆匆忙忙的,当你一抬头的时候,年龄大了,老了,呵呵。
他所学到的哲学美学的智慧,帮助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安排。
来到大学最重要的是叩问知识,而这个知识是为了人生更圆满。不能放弃了这个本质的东西,要使对知识的探求服务于自己的人生追求。要学会欣赏别人,学会欣赏自己,学会欣赏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朱老师介绍美学传统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
我努力长期保持教学与课堂的新鲜感,要有新知识、新内容、新的方式,我不能把同样的内容讲两次。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身体要正,知识要丰富,方法要得当,同时还要把自己的角色淡化,这是比较重要的。不要老把别人当成教学的对象,实际上学生是朋友,是知识探讨的同路人。
–朱老师的美学课堂
一、认识美学,体验人生
记者:朱老师,您是搞美学的。我觉得美学素质是当今社会的国人非常缺乏的。一个人如果有足够高的美学素养,那么他的身心健康和思想境界可能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今天特别想请您谈谈美学对人类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还有您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启发学生产生对美的追求、美的体验。
朱老师:现在因为重商主义,经济浪潮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教育产业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中国教育的技术培训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从塑造人的大学变成了职业培训的场地。学生为了找好工作,自觉性主要在外语、技术方面。这个无可厚非,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对他们有什么指责。但是教育整体明显地失重了。
我做美学和中国艺术研究,这是一个人文学科,跟经济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学科的研究不可能直接赚到钱。本来美学就是非功利的、非目的的,如果抱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来学的话很难学下去。这些年来我在跟学生和教师一些接触中,发现他们不是不喜欢这个东西,而是形势所迫,根本就没有时间。
人生要有一定的趣味,要能用美的眼光欣赏一些东西,例如蓝天白云。这种悠闲的感觉在大学生中间很难找到。我经常跟我的研究生和朋友们讲:人还是要有一点趣味的,没有趣味的人生过着干什么?过得匆匆忙忙的,当你一抬头的时候,年龄大了,老了,呵呵。
人来到这个世界,去挣钱,挣钱干嘛?挣钱成家,成家生孩子,生孩子要抚养他长大。然后,噢!自己老了,退休,退休以后完了,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人的趣味何在?人生还是要有一些境界的,没有境界没有格调的人生,它站不高,也看不远。
清代有一个学者叫张潮的说,人生的境界有三种,他用了一个“看月亮”的比方。第一种,在窗子里面看月亮。大半的人都是如此,因为一般的人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限制,只能在窗子里面看月亮。第二种就是到庭中望月。从屋里面走出来,到了庭院里面。
庭中望月,哦,天地原来如此开阔,世界如此广大。这样一来他扩展了胸襟、气象。最高的境界是“台上玩月”。站在高台上、高山上和月亮嬉戏。这是一种快乐的大境界。他将这三种境界叫做“窗内观月”、“庭中望月”和“台上玩月”。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这种境界的提升。
境界的提升看起来对人没有多少用处,不会给你带来多少直接效用,但实际上对人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胸襟气象怎么树立的?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这有时候也决定他的创造力的大小。不同的心灵境界,不会给你带来直接的利益,但有可能提升你的创造力,让你不陷入一种蒙昧的挣扎和角逐中去。
记者:您如何考虑您的学生的就业问题?
朱老师:我的博士毕业也要面临就业,而且写的东西和就业不太一致。这是比较苦恼的事情。在西方,比如在德国,都是这个命运,在日本也是的。学哲学的,到社会上不一定就去搞哲学,大学聘的哲学教授是很少的。学美学的也不一定会做和美学有关系的工作。
这些我经常跟学生讲。从另外一方面说,这关系又不是很大。因为你学的是人生的东西,本来就不是直接有用的东西,是非功用性的。但是任何一种工作,无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偏重于技术的,做的怎么样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他所学到的哲学美学的智慧,帮助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安排。
我的学生在这方面还好,我不一定给他指导出一个就业的门径,但是我教的东西对他找工作和就业的观念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对他的人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记者:美学在现代社会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您能再深入谈谈吗?
朱老师:对于解决人生问题,美学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被塑造,生命注定被涂出很多种颜色,有时候是很混乱的颜色。禅宗讲,人要做一个“透网之鳞”。鳞就是鱼,人就像从网里头透出来的一条鱼,这样的人极少,大量的人都像是被网住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要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
人怎么摆脱外在的束缚,时间和空间、人内在的妄见、各种功利的驱动、社会习惯的力量、一些陈词滥调的理性知识,这些都给人束缚,使人得不了自由。人的一生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过程。席勒讲,美学是跟心灵做的游戏,它带来一种自由感,就是解脱束缚的。
孔子跟学生聊天,曾皙(点)讲:“暮春者,春服既成,童子五六人,冠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说“吾与点也”。孔子喜欢曾皙讲的境界,就是人去除整个的束缚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天人共生、人天同语的格调,这正是他讲的“仁”的最高的境界。
这种最高的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不是一种道德问题、善恶的问题,也不是知识、求真的问题,而是一个美的问题。这个境界是人和宇宙浑然一体,人在这种精神中能得到自己生命的超越,所以说美学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自由感。
二、提升生命的境界
记者: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中,美学的意义远远超出单纯审美的问题。
朱老师:北京大学从蔡元培校长就提出“美育代宗教”的问题。钱穆先生讲过,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艺术文化,强调人的内在修养。西方文化主要是求知的路径,而中国文化的路径主要是成就人生的。长期以来中国不是靠宗教来支撑的国度,不像美国、欧洲,他们可能信教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
西方一些比较激进的人觉得中国没有宗教,中国是没有灵魂的世界。宗教观念淡泊,人靠什么样的信仰来支撑呢?实际上中国人非常讲究人的内在修养、人的品行、人对世界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自古以来就以所谓广义的艺术或审美来取代宗教的地位,通过人的修养和境界的提升,来使人的生命、生活更有意义。我们传统的教育,主要的精力在这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一个识字教育、懂得科学的教育。
中国的传统,是重视审美和艺术的传统,是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境界的传统。国画的意思也不在于画本身很美,而在于它是人格的一种象征,精神的象征。又比如中国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一般的园林有两种功能,一是实用功能,住人的;另外一个是审美的功能,是给人看的,看起来要很漂亮。
但是中国人还将它上升到第三种功能,它是为了人修养心性的。人到了那个地方不是为了看一片好风景,而是体会一片好心情,体会一种人和世界融合的感觉。
中国一切的艺术,都是为人生的。中国的山水画,都是关系到人生的境界。老是有那么多人画山水。青山绿水很漂亮,但国画是水墨的、黑白的,把色彩全都淡去了,淡去那种色相、独存本真,表达的是人生命的愿望。
人生的教育,和艺术知识、审美知识的教育,我在讲课中把它们三个融到一起。美学是一个特殊的人文学科,我们把这个特殊人文学科所包含的人生的内涵更充分地剔发出来,这样能帮助大家理解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我们不一定成为一个画家、一个书法家,但是我通过欣赏这样的东西,可以提高艺术修养、人生境界。我从这个角度讲得比较多,我的一个主要理念就是“为人生的艺术”。
记者:我们的国画、音乐和诗词,都通过形式来表达一种思想。写实主义在中国好像一直是不受到推崇的。
朱老师:对。我曾经跟外国的一些学者聊天,聊到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对外国人来讲,叫写景诗嘛,他们看不上,因为华兹华斯、莎士比亚的诗,那种铺排,对自然山川的描绘非常详细。
这种小诗,我们读起来却非常有韵味。这不是一个审美趣味不同的问题,而是我们理解的角度与他们不同。因为我们从来不将它们当作写景诗,它描写的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在那种宁静中看人的活泼心情,在那种宁静中人和宇宙合一状态。
有的人画画,比如画梅花,就是画一个植物,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根本就不在于这个植物,在于“要留清气在人间”,要把那种内在的,那种清幽的、疏淡的、高逸的品性描绘出来。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曾问我,那么多人在画梅兰竹菊,画寒山,有什么意思?我跟他讲中国的艺术是重视品格的,这个题材只是他利用的方式,他主要是为了表达他自己心灵中那种感觉,那种对人格的、境界的追求。
中国美学跟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美学一般讲感性,美学是重视感性的学说,而中国的美学追求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它恰恰是要超越感性的。
记者: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学主要源于西方的美学理论,他们是成体系的,但这套体系套到中国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您的工作是建立了中国古代自己的一个美学系统。
朱老师:我写了《中国美学十五讲》,尝试用系统性的见解来把握中国美学的一种可能性。03年我出版了《曲院风荷》,尝试从中国艺术的系统性来把握知识。中国美学有自身的特点,要把它的特点讲出来。庄子讲“因其故然”,要依着它的内在逻辑。把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讲清楚,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我还在往前一点点地推进。
记者:西方的艺术、哲学,一个主流是写实和逻辑,基于理性;而中国的哲学和艺术不是基于严格的逻辑以及对现实的模拟,所以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一点也不奇怪。那么传统美学素养和对中国哲学的深入了解,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处理经济、法律等现实问题,会不会有不利影响?
朱老师:了解一些艺术,或者在艺术方面有一定的创造能力,不会对自己专业的、技术方面的研究。因为任何工作都需要灵感与直觉,科学与艺术、人文素养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中国的艺术在唐代之前走的也是重技术的路径。不仅是敦煌,整个汉唐时期,比如唐代的墓室壁画,章怀太子墓,西安、咸阳和它们周边大量的墓室壁画让人感觉到,中国在绘画上的造型能力,在唐代达到极致。
阴影的处理,光、块面的处理,色彩等等这些创作技术,绝不亚于西方的油画。但是中唐以后这种路径被舍弃了,人们认为这种形似的东西还不够。而西方19世纪后期,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尼采、叔本华等人的现代哲学也颠覆了写实主义的传统。中国这样的颠覆在中唐的时候就开始了。
中国哲学并非不重逻辑,比如惠子、僧肇,和天台宗的智顗大师,他们都有极其高超的逻辑水平。智顗大师对印度传来的逻辑学的改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后来这种逻辑渐渐地被放弃了。我们今天要追踪中国的重逻辑传统,要把这两者之间融合起来,尽量的减少宋代以来的这个千年传统中不足的地方,比如反技术、反知识、反逻辑。
我们一味地提倡庄禅境界,而忽视了技术这样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艺术和逻辑是不同的,但可以相互补充。我在北大中熟悉的一些人,他们对艺术、对庄禅哲学的了解,对美学的熟悉恰恰帮助了他的本职工作。如厉以宁先生是一位诗人,吴志攀先生则喜爱绘画。
记者:我知道原来物理系,数学系有好多国学大师。
朱老师:对啊,中国有很多科学家有很好的艺术人文素养,如杨振宁、苏步青、竺可桢等人。北京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有特色,但是还需要再加强,需要承继老北大的很多优良传统。
三、淡化教师角色,内容常新,知识与体验并重
记者:下面想请您谈一下美学教学问题。深入浅出,寓复杂的美学问题于平凡的事物是您的教学特色。
朱老师:当然不是给学生讲浅的东西,而是要把比较有意思的、深邃的东西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讲出来,这是一个教师应该做的。现在为什么让教师写教材?跟这个有关系,你必须要把它讲清楚了,讲通俗,使大多数人能够理解。讲课要有启发性。
记者:您能举个例子吗?
朱老师:在学科通俗性方面这几年我做了一些工作,尽量让课讲得通畅而有意味。比如我讲“含蓄”,中国艺术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中国的民族个性跟西方也不太一样,中国的艺术讲究言外之意啊,意外之象啊等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就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根本东西:含蓄。
我将我的论题定为“曲径”,中国园林为什么把好好的通天大道,弄得弯弯曲曲,快要看到了,却突然来一个遮挡。颐和园一进门的时候就有一个大东西把你挡住。扬州的各园个原,你沿着弯弯曲的小径走进去,转一个弯,然后豁然开朗,有一片大的世界。
这就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我从大家能感觉到的小问题入手,来讲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个理论排出三点四点。从具体事例,从可以把握的东西入手,力求讲得有意味一些。
记者:能谈谈您教学的经验和感受吗?
朱老师:教师的场合不仅仅在于课堂,课堂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大量的时候还在于言传身教。体态语言、著作、交谈等多种方式,来尽一个教师的责任。一个教师不是课堂上的一个教学者,不是一个教学精英,而是一个能够对别人有影响的人。我回到教师的本意,就是回到苏格拉底,回到孔子这样的教师的本意。这是作为人文学科学者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记者:孔子和苏格拉底他们的教学本意,本质上是什么?您能不能具体的描述一下?
朱老师:形式是自由的,是辩论性的、求知性的。知识探求是它最根本的内容,解决人生问题是他们最主要的驱动力。没有完整的答案,没有具体的形式。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都在传递他的教育,孔子弹琴都是在晓示学生。我们现在的教育完全是要承继一种比较死板的知识,知识是既定的,方式是固定的,教师与学生的角色也是确定的。
这不是教育的根本方式。“教学相长”,其实暗含着一种僵化的教学模式。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是教与学无处不在,相教相长,相学相长。
另外,知识本来就是灵动的、活泼的。保持探求知识的心态,你是永远的一个行路者,正在向高山上攀登。你不是把固定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而是要教给别人我怎么爬上山的经历、经验、体会。每次我上课我的内容都是新的。我思考的结论,至少目前的结论,也在变动中。
我教给他怎么思考,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以及我论证的几个方式。我的知识是活的,但我也会把一定体系性的观念传达给学生。这种系统性的意见对这个学科极为重要,对学生把握知识也很重要。
记者:朱老师,您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您的教学过程?
朱老师:我自己准备新教案,每次课都是。我一般把这一课的讲稿打给大家,课后去看,上课的时候主要听我讲,我讲的一般是超出教案的内容。我觉得按照教案一点一点往下讲,比较生涩,这个课堂的感觉也不是很好的。我努力长期保持教学与课堂的新鲜感,要有新知识、新内容、新的方式,我不能把同样的内容讲两次。
我也尝试用过几次比较“规范”、简单的教学方式,比如我这堂课讲几个问题,引文引哪几个东西、用哪些图片,制作了路线图。但做好以后,我上课的感觉不太好,因为限制了我的自由发挥。虽然让学生有所把握,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课堂气氛变得比较呆板,不太生动。讲课内容是很清楚,但是比较机械。
记者:如何保持每堂课都有新的东西,比如新的方式和新的知识?这方面您怎么作的呢?
朱老师:我上一次课,至少准备几天时间。这也成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一部份。我至少有三本是在我上课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中国美学十五讲》。每次课我准备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个完全新的问题、一个新颖的角度不断向前推进。学期开始我有总体上的考虑,每堂课讲什么问题,我尽量有一个综合性的设计。
记者:讨论在您的课程教学中是不是很重要?
朱老师:当然,我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互动比较多,有些典型问题我要经过准备,随时准备跟学生一起讨论。很多人提问题,我也一定会留问题给大家。有时候在上课中,有时候在讲完的时候。
记者:实际上您是身体力行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讨论、交流是最有效的教学方式。
朱老师:互动了就活了,水流动起来才活啊,不然教学就成了机械的了。讨论也可以对学生的理解力有一个了解。
记者:如果讨论比较热烈,涉及的方面是您以前没研究过的问题,您怎么样处理?
朱老师:这种情况很多。有时我回去查书、研究一下,下次再回答;另一方面,我尽量全面一点了解背景知识,尽量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能够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解决,或为学生提供一个恰当的思考方式。另外我不喜欢教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教学方式,好象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似的,那感觉非常不好。比较虚夸。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身体要正,知识要丰富,方法要得当,同时还要把自己的角色淡化,这是比较重要的。不要老把别人当成教学的对象,实际上学生是朋友,是知识探讨的同路人。这样,大家能够放下心来,能够走得更顺畅一些。知识也是这样子的,没有权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权威都是暂时的。教师自己要有这个能力去挑战它,也要求他的学生去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教书匠和一个启蒙者是完全不同的。
我上课中曾经有错误。教学知识的准确度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课要提供一个大致可靠的知识,但是不代表不能出错。如果说一个人错话连篇,基本常识不具备,那当然不具有做老师的资格,但要讲得句句箴言,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人文社会学科体系庞大,本身流派和争议很多,又涉及大量的历史文献解读,所以教师绝不能轻易把自己放在“真理”的立场上。
记者:您经过多年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美学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有没有学生对您的体系的一些观点表示不同意见的?您怎么对待?
朱老师:经常有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他在一起讨论。我的观点写出来,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东西我不会轻易放弃,我会跟他辩论。当然课堂上我不会用盛气凌人的语气,我是讨论式的。他要说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思路,我觉得他有道理的话我会接受他的意见的,而且我会明确地修改。我在书的后记里面都写道:有的内容是跟大家共同完成的。我没有出现过在课堂上比较独断地、声色俱厉地驳斥别人的现象,这不是我的性格。
记者:在您这个课上,考试是怎么样的?
朱老师:考试我有时候出两个题目给他们写论文,没有纯知识性的闭卷考试。
记者:人文学科的教学可能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与西方理论的比较,以及在教学中如何协调的问题。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朱老师:西方的教学方式确实跟我们有一定区别。在人文学科方面,他们的知识,表述的系统性、确定性跟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这里知识的体验性、非逻辑的特征非常明显。古人讲“圣人述而不作”,就是强调知识的体验性特征。
我们教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还是尽量地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方式,尽量地使它符合科学性,毕竟是学术,如果没有科学性,它就不具有大家互相理解的可能了。但是教学中又要注意到中国学术的特点,否则怎么能理解其精髓?中国的学科本来就是混成的,文史哲不分,强调了一种体验。
我觉得要从知识和体验这样两方面来启发学生。体验性的特征还是比较重要的。体验往往是和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跟自我的感觉是连到一起的。我不喜欢跟学生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一个确定的知识,而是要讲一个和我互动起来、我自己可以体会到的、有一定生命价值的知识体系。
记者:您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如说绘画书法和音乐,有过专业的训练吗?
朱老师:我没有上过艺术学校,但是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艺术有一些爱好,从小就写字,练书法;后来学过一段时间的画,篆刻做的时间很长。但都做得不好。就是说,我对艺术有一些感觉,对中国艺术有一点认知。对研究中国艺术理论的人来讲,有一些艺术感是很重要的。
但理论是超越技术的,而实践有很强的技术性。就是说,一方面,必须懂一点;另外一方面,还是要舍弃它,不能够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艺术的实践中去,否则会影响到自己观念上探讨的路径。
四、为人生的美学
记者:哲学系办有针对成人的培训班,招一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给他们讲哲学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对已有多年社会阅历的成年人,你对他们的美学修养有什么建议吗?
朱老师:比如说有人喜欢收藏,但是很多人只是关注收藏价值,比如说一千万买来的东西,想一千五百万卖出,赚五百万就是他的目的。至于这幅画是不是真的?这幅画表达什么意思?跟他无关。这个人追求的就完全是外在的东西,他不是艺术中的人。
有一次我专门讲一堂课叫“顽石的风流”,就是讲石头,讲中国的假山。你看西方的园林或别墅建筑都带有雕塑,有人的雕塑,也有神话和宗教的,但中国的园林没有。中国的园林普遍有假山。中国古往今来很多文人的案台上都有石头,这种清供。
他们欣赏石头比如太湖石、灵璧石、英石。这些石头比较珍贵,有来历,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石头能给他精神上带来什么。中国人欣赏石头叫“千秋如对”,“面对”的“对”。
石头是永恒的东西,它在中国人的意念中是不变的,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和对石头的欣赏是一种“千秋如对”的关系。欣赏石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跟永恒的东西的对话,这里面蕴含了无数的智慧。古人欣赏石头,都强调“瘦、漏、透、皱”,北宋以来一直如此。
“瘦”,为什么要欣赏瘦的石头,不欣赏那种胖胖的,或者说矮矮的那种?瘦的石头就像竹子,清高,不落色相,不受外在的干扰,独立。“漏”,为什么石头它要追求孔隙?太湖石有好多个洞隙。石头是在水的冲击下形成的空隙,这是与宇宙呼气的一个眼。人欣赏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欣赏通透的、玲珑的、人和自然密合的感觉。中国人欣赏石头,与其说是爱石头,倒不如说是爱人生。
通常说的美学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种是审美文化,知识方面的,扩展人生境界,人人都有爱美之心嘛;另一种美学是关于美、研究美的学术,是少数专业人员能够从事的。我们不能只讲纯粹的理论,也要在提高人的审美修养这一块做点工作,让更多人学会欣赏。
很多次我跟同学讲,怎样欣赏北方冬天的树,尤其在月光下面,树枝参差、错落,这叫“北树多姿态”。再比如说欣赏雪,欣赏冬天的苍茫,欣赏那种古拙的风味。还有北方的建筑,四合院,那种灰灰的颜色中加上大红大绿,毫不感觉土,而且感觉非常美。
我们刚才讲欣赏石头,你不仅仅要知道这个石头它能卖多少钱,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旱太湖石不如水太湖石?北太湖石不如南太湖石?洞庭东山不如洞庭西山的太湖石?
记者: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关键是放松自己的心情,去发现。
朱老师:是啊,放松自己的心情,就像苏东坡讲的,“何夜无月”,“何地无竹柏影”,只是我们没有心境而已。
我觉得要欣赏,而不是急匆匆的、急功近利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的、把人生当成丛林法则的那种态度。胜利和失败都是暂时的,人生也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来到大学最重要的是叩问知识,而这个知识是为了人生更圆满。不能放弃了这个本质的东西,要使对知识的探求服务于自己的人生追求。
要学会欣赏别人,学会欣赏自己,学会欣赏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方面,人生中美满的东西是暂时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好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失败者;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生处处都有美满,一朵小花都有它的意义。
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当我细细看/啊/一棵荠花/开在篱墙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学科对人的认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能够让人放松一点。老是想着,“我最强”,“我最棒”,不是成功的捷径,而只会带来巨大的挫败感。
记者:一味争强好胜的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容易走向毁灭。
朱老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这是苏东坡讲的。我们讲围棋,高手不是要杀得你死我活,而是形势与境界之争。比如说有一首词,北宋晏殊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他有一种怅惘,但是是那种美的怅惘,一种忧伤,也是美丽的忧伤,“小园香径独自徘徊”。所以说要知道欣赏生命中美好的东西。生命不可重来,人从小到老,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过程,所以人如果能够细细地欣赏、回忆,而不是成天计算得失的话,得到的东西会更多。踏踏实实地去干,也悠悠闲闲地欣赏。能够放下一片心来过日子,也能够凭着一股流利去干事情。
记者: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朱老师!
采访记者:郭九苓,史倩倩
采访时间:2009年1月7日,上午10:00-11:40
录音整理:安胺
文字编辑:余鹏,郭九苓
定稿时间:2009年3月19日,经朱良志老师审阅同意。
附:朱良志老师简介
朱良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著有《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扁舟一叶: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中国美学十五讲》、《生命清供:国画背后的世界》、《审美妙悟的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