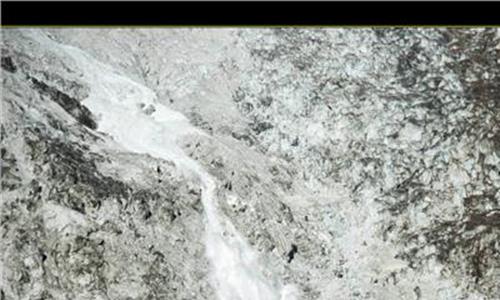【远行】寻觅三毛沙漠的家
看望三毛从前的家
当清晨再次赤足走到院子,仰头看飞鸟,看敏捷活动的云,深深吸气。后来我对老友小群说,这一口,是帮你呼吸的。本来这一趟,我是带着许多许多兄弟的心,一同来的。她们都说,去帮我看看她。
按之前做好的功课,大致知道三毛的家,在阿壅小镇的金河大街44号,这条街在当年,名叫加泰罗尼亚大街,多么西班牙的姓名啊。而金河大街,大致在国家旅馆向西的方向。所以走出旅馆大门,咱们先定好方向,便顺着一条大路走去,又疑问着,再回来走上别的一条,仍是边走边疑问,便拿着打印好的地址去问街边的战士,人家好像也不知道,就掏出手机问,问了一阵主张咱们,不如打车去。
我说,我想走曩昔。所以他用极不流通的英文,指了一个方向。咱们谢过他,在阳光下向前,又再问一位帅气的路过的军官,当来到一处小集市去问一位卖菜的大叔,不会说英文的他笑呵呵地,拉着咱们向前、左转,再指向右,说那即是了。
这是一条称得上宽广洁净的大街,不再是当年三毛文字里的杂乱与狭小,挨近正午的西撒哈拉的阳光明晃晃地直射在两边刷成五颜六色的墙壁上。一向走,一向向西,俄然,先就看到了左手边的一排房子,简直是飞奔而去,是的呢,那个白色粉笔写的44就在那里,就在淡黄色的墙体上,那样寂寥冷静地,被一只小小电表和杂乱的电线环绕着。
这儿,即是那个从前的沙漠里最美丽的家啊!那些捡回来的棺材板DIY的家私,那个旧轮胎改的沙发,那个从前将骆驼头骨当作成婚礼品的美丽的家,那个包过饺子做过甘旨的“雨”的爱意浓浓的家,那个从露台的天窗上掉下过一头山羊的家啊……居然,真的就在眼前了。
这排房子的街对面,是一道长长的围墙,正对面停着一辆火红的汽车,一向有人路过,还有一些人就站在街边,他们微笑着看我,眼里满是不解的友爱。看我坐在人家的门口,一向赖着不愿走。正坐在马路牙子上发愣,俄然来了一辆车,就停在咱们面前,车上下来一个英伟的男人,居然去按了44号的门铃。我竟是一向没有昂首也没有回身看,低着头,听到有人应门,他们简略对话,然后,男人开车离去。我在想:是不是,也应当去按一下门铃?
这么坐了五分钟,我站起来,对兄弟说,我要去按门铃了哦。门真的开了,隔着一道铁门的栅门,是一位穿戴家居服的撒哈拉威女性,用她美丽的大双眼看我。我说,我从我国来,从前有一位作家,许多年前在这间屋子住过,我可不能够进入看看?她慎重地没有笑意地看我,然后说,我的老公不在家,你能够,他不可。
所以我进入了。一入门即是一道窄窄的走廊,三毛首次来到这儿,是荷西抱她进入的。荷西说,你是我的新娘,我要抱着你回家。她说,荷西走了四大步,就走完了这条走廊。而走廊的止境,是一间空空的过厅,一昂首,便看到那个幻想过许多次的从露台上掉下过山羊的天窗,现在,现已用铁丝交织着围拦起。
我站在暗淡的过厅,短促地对女主人诉说着:大约40年前,有一位叫作Echo的我国女性,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写过许多撒哈拉的故事,我十分十分爱她……当提到“我来这儿的仅有的意图,即是为了来这间她从前住过的房子看一看”的时分,我居然有些哽咽了。
而她,站在我的对面,十分了解与痛惜地点着头,说她知道,一向都会有我国人来这儿,为Echo。
这是一个有着两个心爱女儿的四口之家,他们在此住了8年了,之前,她说,是别的一个家住在这儿。想起包包里有一些我国的糖块,便都掏出来给那一双美丽的女孩儿,又问,能够和你合影吗?她微笑起来,说,需求去换一件衣服。
她去近走廊的房间换衣服,我站在过厅,四下里张望,又去女儿们呆着的房间门口,打量着房间的姿态。全部当然现已不是当年的姿态了,这中心,究竟隔着40年的韶光啊。
她请她的大女儿为咱们摄影,然后,她总算说,能够请你的兄弟进来,假如仅仅看一看的话。我欢喜地跑出去,将老实地在门口坐着的兄弟唤进来,可是一时刻,又不知道该说啥好,由于有兄弟在,我反而有些欠好意思再像方才那样急切切地表达。那就离别吧,最终再看一眼那个天窗,我想,是真的能够掉一头山羊下来的呢。
咱们又在门口坐了好久,风很大,阳光依然很绚烂。幻想着当年,对面应当是能够直接望见沙漠的,当今的阿壅,已可称得上富贵。当年摩洛哥老迈哈桑占据了这片土地后,给予了极大的优惠政策,因而招引了许多商客,富贵是必定的。仅仅,三毛的家,三毛的撒哈拉,三毛的梦,从前是一向是咱们的,现在依然仍是。
她的文字留给咱们无限的力气
后来,咱们在这片沙漠边的住宅区走了好久,再后来,咱们坐上六人的老奔跑出租车,去了海滨,我不知道这片海岸,是不是即是当年三毛与荷西打鱼和捡石头的当地,可是,我一厢情愿地当作它是。风十分大,海水很蓝,咱们坐在海滨的石头上,不说话,不说三毛,仅仅,那样持久地缄默沉静,啥都没有想。
三毛还写过,由于家住在坟场区没有门牌号,所以她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天天走路一小时去邮局收信取邮件包裹。第二天早晨,问过国家旅馆那位风姿潇洒的前台先生,他具体地说了一通,说,走路,五分钟。又跑出旅馆门口,将一条准确的路指给咱们。
事实上,即是步行五分钟的间隔。在一条微斜的大街,摩洛哥蓝黄相间的邮局象征,显眼地贴在一幢修建的一楼,而就在邮局的楼上,是当年的法院,三毛与荷西即是在这儿,签下了阿壅小镇法院发布的第一份婚书。仅仅现在,旧法院现已抛弃,楼梯口一片狼藉,而邮局的大门紧闭着。
咱们去看门口的牌子,清楚写着营业时刻,却又有一部分被涂掉了,再去近邻开着门的一个啥组织问,人家说,关了。连邮局都抛弃了,假如再晚一些时分来,是不是连这幢修建也会不见呢?
我在阳光下有些苍茫,只觉得年月无敌。想起早上看到兄弟头天发的兄弟圈,说是去了三毛家期望有人买下这个房子复原当年的容貌,再搞个三毛纪念馆,我就很生气,硬是逼着他删掉。我说,咱们爱三毛,就这么平静地爱着就好了,是怎样就怎样了,不要故意更不要有这种僵硬俗套的想法。我来,仅仅为了来看一看,隔着这40年,仅仅为了一个梦。
当咱们后来脱离阿壅,回到卡萨布兰卡,再动身去马拉咯什,然后,从马拉咯什动身,预备深化撒哈拉沙漠的第一晚,居然在酒店的餐厅偶遇了几个我国人,而其间四个美少女团,是我在穷游网上约过伴由于行程不合适而没有约上的,别的一对夫妻dodo和yyy则从广东中山来,他们一路叹气为何没有去网上约伴,否则咱们或许早即是一伙的了。
而美少女四人团的其间三个,都是在英国念书的90后,别的一个则是她们在网上约到的伴,北京来的一兮。咱们传闻咱们去了阿壅,都叫了起来,一兮乃至还问:那个天井在吗?山羊吃过叶子的植物还在吗?而后来,我在邻桌听到90后张大爽跟兄弟们说,刚去英国读书的时分,她即是带着三毛的书去的……
Echo,听到了吗?隔了这么多年,你的文字和故事,依然给予咱们这么多的力气啊。后来,一兮真的一自个去了,我看到了她在沙漠上写下“Echo”的相片,咱们的火伴狐狸也一自个去了,她在44号的门口,挂了一个艳红的我国结,她还带去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她最终决议,把书留在国家旅馆,让今后再去的人,能够在三毛的小镇看到这本书。
那个撒哈拉沙漠露营的夜晚,我一自个,躺在沙地上,看着漫天的繁星,一向在听一首歌,那首名叫《七点钟》的歌。“此生即是那么地开端的……”那个深埋着不安分的漂泊狂念的此生,应当即是这么开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