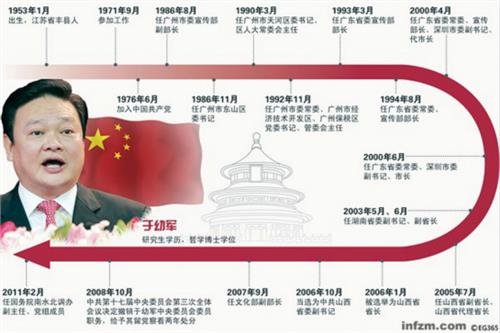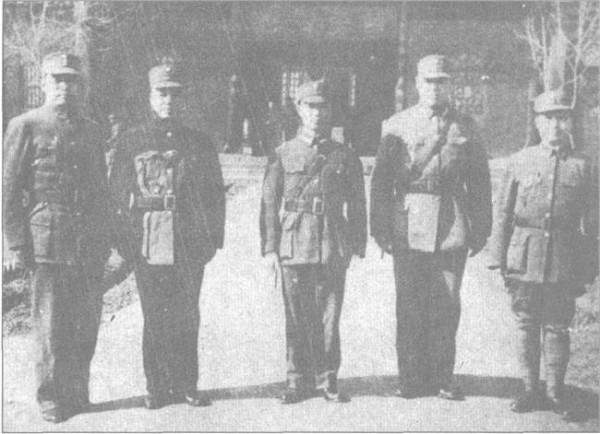孙幼军的成就 孙幼军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写够童话
[摘要]著名童话作家孙幼军于8月6日离世,孙幼军的夫人朱景彦表示,“他临终之际很平静、很清醒,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写够童话,还想写。”
近20天在重症监护室的治疗最终还是未能挽救孙幼军已然脆弱的生命,这位当代著名童话作家、中国首位安徒生奖提名者于8月6日离世,享年82岁。昨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孙幼军的夫人朱景彦表示,这些天来家人的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他临终之际很平静、很清醒,此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写够童话,还想写。”
孙幼军(图源网络)
孙幼军1933年出生于哈尔滨,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获国际安徒生文学提名奖和IBBY荣誉作品证书及国内多种奖项。
196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此书出版累计册数达百万以上。其创作的长篇童话还包括《没有风的扇子》、《铁头飞侠传》、《仙篮奇剑传》、《跟怪老头儿漫游奇境》,系列童话集《玩具店的夜》、《怪老头儿》、《亭亭的童话》、《唏哩呼噜历险记》等,并翻译出版了巴西、日本、斯洛伐克、捷克、苏联等国家的童话故事。
盼回家 年轻时心脏就不好
孙幼军年轻时心脏就不好,他的父亲就是因心脏病而早逝。朱景彦介绍说,孙幼军20多岁时心脏就有传导阻滞的问题,心脏跳动过缓,有时一分钟才跳38下,“医生都说,他这个心脏能为他服务82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不过,他平时就是太大大咧咧了,不在意身体,否则,肯定能多活几年。”
从2004年开始,孙幼军的身体开始不“合作”了,“他基础病特别多,2004年和2011年还患了两次脑血栓。好在两次脑血栓的结果,除了让他记忆力下降,人开始变得丢三落四外,庆幸的是,没有落下其他的后遗症。但是他76岁时又因胃出血住院,后来又得了舌咽神经疼,之后又是肾功能衰退。”
而今年1月22日的一场肺炎,给了孙幼军严重的一击,孙幼军因为这次的肺炎终于下决心戒烟。到了7月,家人刚觉得他脸色恢复得不错,7月22日他就因心梗住进了医院,在急诊室被抢救了两天。朱景彦说:“医生告诉我们,虽然他60%康复了,但随时都有变化,因为他的心脏有堵塞,心脏不好又影响肺部的正常工作,造成肺水肿。那些日子我们经常在半夜被叫去医院,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最终,在重症监护室熬了十多天后,孙幼军还是没有挺过去,于8月6日发生第二次心梗而病逝。朱景彦当时很心疼孙幼军的身体被插满管子的样子,“他挣扎着不愿意上管子,看着让人难受。”
孙幼军在医院治疗时,医院有严格的探视规定,每天下午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有三个人去探视,那就每人只能十分钟,加上穿隔离衣等程序,其实探视时间也就八九分钟。朱景彦说她去探视时,经常装扮得让孙幼军不知道是谁,否则,孙幼军会要求回家,“我现在也想,要是那时带他回家多好,可是这也不过是他的孩子气,我如果真这么做了,也许他回来的路上就不行了。
在医院,医生都很尽心,肯定比在家里照顾得更好,所以就算是我后悔,照他的想法带他回来,也不一定就是对的。”
孙幼军去世后,家人没有举行追悼会,就是在医院按照普通的程序,家人加上亲朋好友,不到20人参加了最后的告别仪式。朱景彦表示,这是孙幼军自己要求的,“因为他这个年龄,经历了不少同事、朋友的离世,每次他去参加追悼会后,回来都沉默着不愿说话。之后,他说举办追悼会是给活人增加痛苦,活着时大家都有说有笑,可是参加追悼会时,却是天各一方,他自己死后一定不要这样。”
一方面是尊重孙幼军本人的意愿,另一方面,朱景彦也考虑,周围的朋友年龄确实都很大了,不要为了参加孙幼军的追悼会再把别人折腾病了。尽管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不多,但朱景彦很满足,“隆重又简朴”。
爱读书
谈恋爱也去图书馆
孙幼军离世了,可是他满满的书架仍在,每本书上仿佛都有孙幼军的影子,不时在朱景彦眼前晃来晃去。相濡以沫多年,孙幼军在家是“甩手掌柜”,朱景彦则是家里的“大内总管”。朱景彦回忆说,早年间两人聊天,孙幼军用手给她比划着,说人生只有短短的那么一截,他想给社会留下点东西,而他的特长就是写东西、写童话,所以他要多写,给孩子增加快乐,“我那时就对他说:我是笨鸭子,没有你的这些本事,你写吧,我来分担家务。
”在朱景彦尽心尽力的照顾下,孙幼军一生创作力旺盛,写出了大量深受欢迎的儿童作品。
书,是孙幼军的宝贝,朱景彦说他们去五七干校收拾东西时,朱景彦要锯木头钉箱子装被子,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孙幼军什么都不管,他就想着怎么处理自己五个书架的书,“这些根本就带不走。最后没办法,8分钱一公斤卖了,他是流着眼泪卖的。”
提起孙幼军对书的“痴”,朱景彦脑海里的故事简直说不完,“我们刚认识时,他就带我去书店、去图书馆,我那时想,这也叫谈恋爱?他还带我去外文书店,我又不懂外文。”
因为书,朱景彦也跟孙幼军怄过气。那时朱景彦的工资是一个月46元,孙幼军是56元,两人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一天,朱景彦给孙幼军20元让他去买衣服,结果就看孙幼军夹着本《辞海》回来了,“我跟他说:孩子的奶费都交不起了,你怎么又去买书?花了我半个月工资,想看书的话,为什么不去图书馆借呢?他说跟图书馆借只能用20天,可要是自己的,就随时都能看。他跟我说‘我还自己加了一元钱呢’,让我听了哭笑不得。”
朱景彦说,那时家里全是书,连床底下都是孙幼军的书,“我说家里都快没放床板的地儿了。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书。我曾经问他是把这个家放第一位,还是把那些书放第一位,他回答我说:‘平行’。”
忆及这些,朱景彦嗔怪之余却流露着爱与欣赏,也正是这份感情,让朱景彦这么多年无微不至,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孙幼军。
老小孩
怕去医院怕吃药
在朱景彦眼中,孙幼军就是个孩子,一辈子也长不大,活在他自己的童话世界中。“他老了就成了老小孩,我跟他说,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你怎么还是个孩子。”
年轻时生活苦,朱景彦常为吃了上顿没下顿发愁,可是孙幼军从来不愁,“他就和孩子笑啊闹啊耍贫嘴。”朱景彦回忆困难时期,有一天她买了一瓶菠萝罐头,孩子们看了都高兴坏了,“我就和他们说,你们都等着,我分给你们吃。
我去厨房拿了四个碗四个勺,一出来我就笑坏了,原来他们三人按大小个,排队等着我呢。孙幼军排第一,女儿是姐姐排第二,儿子排在最后,三人都是立正姿势,双手直直地垂在裤线上。我们家每次吃东西,我自己都是分最少的那份,他们三人一样多,所以孙幼军从来不看我的碗,可是他瞟两个孩子的碗,那副表情生怕我给他少了,给孩子多了,特别孩子气。当然他那样也是故意在逗我们开心,他会从自己的碗里再拨一些分给两个孩子。”
孙幼军的女儿曾说他们的父亲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而孙幼军“护犊子”的名声在邻居那儿更是知名。孙幼军一家一直生活在外交学院,孩子们在一起难免会打打闹闹,朱景彦说,有一次院里的孩子把她儿子打了,姐姐一看不干了,又去打那个小孩给弟弟报仇,结果人家的妈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了,“我们两人使劲给对方赔不是,赔礼道歉说一定教训我家这俩孩子。
人家妈妈刚一离开,就听孙幼军一边敲一边说:‘你们以后还打不打人了?’我一看,他拿根棍子抽木箱子呢,人家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在打孩子。”
孙幼军怕去医院、怕吃药,所以每次朱景彦都要“哄”着这个老小孩,“一听说要去医院,简直是要了他的命,害怕。”女儿从美国给他带回保健品,朱景彦每次都哄他说:“这是治脑血栓的药,吃了你就能继续写作了”,他就听话乖乖地吃掉了。要是跟他说保健品,他不相信保健品有功效,就不会吃。在这样的“哄骗”下,孙幼军吃着吃着觉得身上有劲了,朱景彦才敢向他透露吃的是保健品。
孙幼军的代表作除了《小布头奇遇记》,还有《怪老头儿》等,问生活中孙幼军是“怪老头儿”吗?朱景彦毫不犹豫:“他怪啊,说高兴就高兴,说不高兴就不高兴。”朱景彦觉得孙幼军跟外人说话不留情面,“我对他说‘你说话要委婉些,给对方留面子,学学说话的艺术。’可是他不,他就像个孩子,心思特别简单,想什么就说什么,发脾气也是。过一会儿他自己好了,忘了他发过脾气这事了。”
不服老
写不出东西生自己的气
在朱景彦眼中,孙幼军是个闲不住的人,尤其不服老,“他70岁还学开车呢,71岁时还开,我劝他别开了,万一撞了人怎么办。他还骑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我们家光他丢的自行车,就有7辆,他还有照相机、摄像机,还学电脑,他的文章都是自己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没他不感兴趣的。”
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对生活充满兴趣的人,在不得不服老时,心气随之也垮了。朱景彦回忆说,孙幼军得了两次脑血栓后,创作力仍然旺盛,他2011年至2013年还写了七篇中短篇童话,可是从今年1月得肺炎后,朱景彦有了不好的感觉,“他从今年开始,记忆力严重下降,忘这忘那,写东西也想不起来,坐在电脑旁干着急。
得肺炎那天,他坐那写不出东西,就特别生气地把键盘一推,说‘我是怎么了?’他不住唠叨自己没用了没用了,晚上就发烧得了肺炎。”
讲故事、写童话,是孙幼军这一生最为在意的事情,小时候给弟弟妹妹讲,到以后给夫人、朋友、孩子讲。当发现再也写不出驰骋在脑中的情节时,孙幼军难免会生气和绝望。
朱景彦说,孙幼军以前写完故事会讲给她听,虚心接受批评建议,“他跟我开玩笑说,老婆说的话一定是真心实意的;妾说的有拍马屁之嫌;而朋友说的,又常常是在捧你。”而朱景彦听完后有时会说,“这个好听,这个好玩,这个有些生硬”,对于批评,孙幼军从来不会生气,他会很认真地考虑。
院里的小孩都喜欢听孙幼军讲故事,孙幼军写《小布头奇遇记》时会把写好的给孩子们念,写一段念一段,孩子们都听上瘾了,见着他就问“孙叔叔,小布头后来怎么了”?
问及孙幼军是否有没完成的遗愿,朱景彦说:“有啊,就是他还没写够,他还想写。”写不出东西的孙幼军不让自己休息,又开始整理从小就开始写的日记,还每天坚持写日记,写的字都大小不一。脑子开始糊涂的孙幼军也会活在幻想中,对着电脑发呆,让朱景彦看着心疼,“以前他爱吃肉,什么红烧肉啊、肘子啊,无肉不欢。
家人为了他身体考虑不给他吃的话,他还不高兴。后来我想他也80岁了,想吃点就吃点吧,又能吃多少呢?可是两个月前,我问他想吃米粉肉吗?他没有往常的高兴劲,没精打采地说:你做什么,我吃什么。我听了觉得心里一沉。”
让朱景彦稍感安慰的是,孙幼军临终之际很安静很清醒,“他的朋友来看他,握着他的手,他有意识,知道朋友来探望他。女儿从美国赶回来,跟他说‘爸,我回来了’,他答:‘嗯’,心里都很清楚。”
同普通读者一样,朱景彦喜欢孙幼军写的《小猪唏哩呼噜》、《小布头奇遇记》、《怪老头儿》等作品,“有的作品他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书都跟政治有关,很生硬。现在,希望这个怪老头儿可以在天上自由地幻想他的童话。”(文 /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