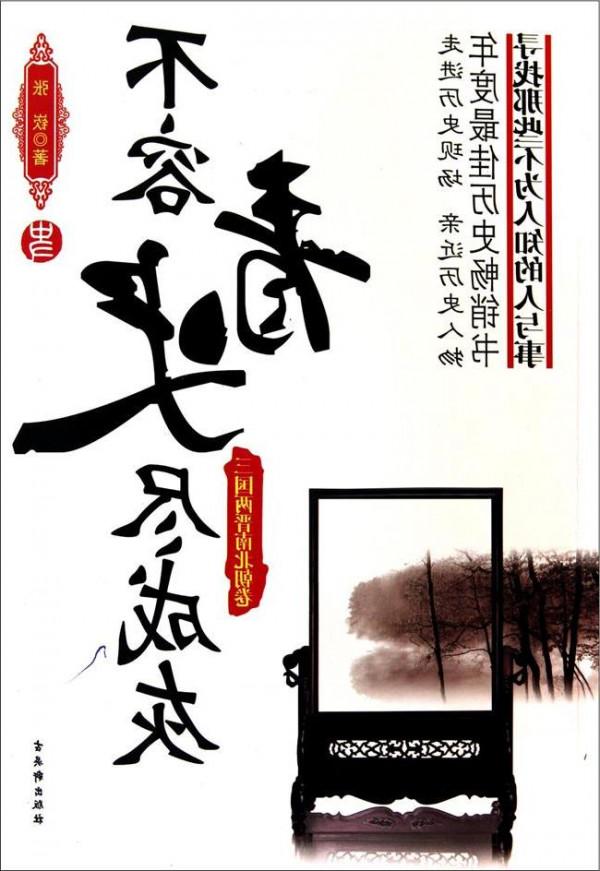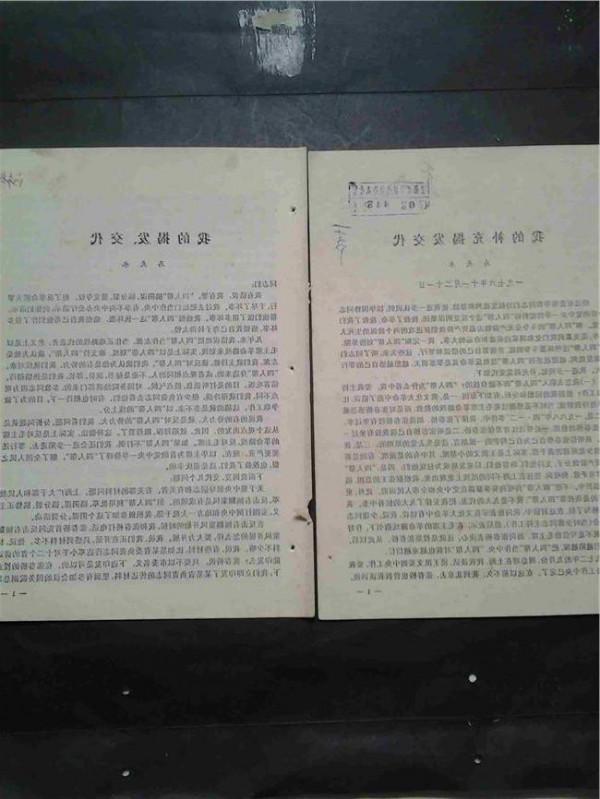马天水的儿子 晒晒马天水的疯癫人生
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50年代以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50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穿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向干部、工人了解情况,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到了张春桥接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要用他。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在1966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林彪的批评。事后,张春桥找马天水做工作,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967年初,林彪、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勾结在一起,乘天下大乱之际,首先在上海进行篡权活动,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事前,王洪文等集会煽动群众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接着他们制造了沪宁路全线停车的“安亭事件”,又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使上海市委及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
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与亲信密谋。同日,他们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把由他们一手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财经大乱的罪责,栽赃在上海市委和主要负责人身上,从而逐步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各造反团体发了贺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竭力予以支持。夺权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热潮,要把张春桥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张春桥说话。当天晚上,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当选以后,马天水被连夜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喜从天降,令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里。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对邓小平复出心怀不满;邓小平却对其认识不足,惹下麻烦。
1973年3月,毛泽东作出了让邓小平复出工作的指示,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邓小平向中央写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中央文件,决定向中央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
在讨论中央文件时,马天水说:“邓小平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不满归不满,拥护中央决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定,他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原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遇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对马天水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张春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娑着光滑的头皮,向张春桥老实交代:“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张春桥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中央要印发政治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张春桥没有发火。马天水心里明白,张春桥的想法其实和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邓小平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到上海访问,马天水接受了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邓小平十分尊重。
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估计不足。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在“文革”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把其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要陪同菲律宾贵宾到上海访问。6月11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响了。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打来的。王洪文说:“马老吗?明天邓小平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天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邓小平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中央政治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王洪文那摸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一下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谈。”王洪文避开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王洪文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
6月12日,邓小平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
邓小平问马天水最近在抓什么,马天水将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内容是说重点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纲上来,树了几个典型等等。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打断马天水的话:“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邓小平问。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说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去北京开会时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只好故意装傻说不知道。
“有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邓小平进一步交底,“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意识到这是讲江青。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接点张、姚,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得住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上海批了林彪、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说。
邓小平转了一个话题,问马天水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邓小平又问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熟不熟。马天水说与他们很熟。
邓小平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马天水是有着长期政治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着,口里就是不表态。他含含糊糊地说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他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过去了。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975年7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姚文元听罢沉吟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我早就讲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老马,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姚文元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告诉了张春桥和王洪文。
揭发邓小平“策反阴谋”,老马又立“新功”;升官在即,可惜是一枕黄粱。
邓小平在各条战线上的整顿效果是显著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赢得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因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革”的否定,是从根本上对“文革”的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
1975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把邓小平“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整理,直送王洪文。马天水的揭发材料中说邓小平于1975年6月12日与其谈话,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还点了张春桥的名字。
王洪文拿到这份记录,立即报送毛泽东,并说:“我觉得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从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不是光明正大,是一次挑拨策反。”这份记录被“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
会议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程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打气。张春桥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简报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恨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呢?”
经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球的皮球,在当晚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的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邓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叫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谈话。张春桥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你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泽东病重,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很快,揭批“四人帮”揭到了马天水头上。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
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精神失常了。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一年后的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
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决定派人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剩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
……”对抗日战争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大革命”,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叫嚷“安排工作”,“恢复党籍”。一听到“改革、开放”、“商品经济”这些字眼,他就会朝厚重的大门撞去,口里哇哇乱叫:“快把广播砸了,里面全是骗人的把戏呀!”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