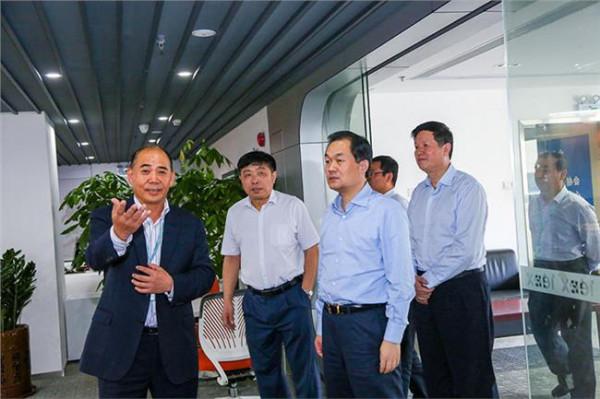许章润汉语法学 张曙光:简评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
对法律来说我是门外汉,现在是班门弄斧,之所以读这本书,我觉得有两个具体原因,一个是要开这个会,我想总不能光带个耳朵来,总得拿个东西吧。第二个原因,正好韦森的《语言与秩序》,让我给写了一个书评,我读了《语言与秩序》,对于语言学我也是门外汉,读了以后章润送我一本书《汉语法学论纲》,我觉得这两个总有关系。
社会科学里面哲学、法学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倒是落后了。所以我想从这书里面能看出点启示来。我读的感想,开始读章润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就想读下去。但是读到最后,我感到有点不解渴,就像今天说你这六个问题一样,我的不解渴会具体来讲。
我想讲三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的思想学说到底现在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我看近百年来恐怕还是一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一个如何能够汇通古今,汇通中西的问题。因为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这个状况。
我想原因我也不用讲了,因为咱们古代文化大家都说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但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农业文化,农业文明。近代从农业文明到了工业文明,所以中国落后了,经济上、政治上落后了,文化上生存的空间也受到了很大的挤压。
西学东渐以后,咱们看到咱们现在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西学里面来的,所以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确实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中国学界面临的一个根本任务,咱们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中国学术思想检验咱们的一个标准。所以我就想看了以后,章润在这方面是做了一些探索,这个探索还是很有益的。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展开,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章润的探索和贡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的贡献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他把中国的汉语法学发展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一个就是子学时期,一个是经学时期,一个新经学时期。子学时期就是春秋战国时候,经学时期就是秦汉以后到清。
近百年的状况叫新经学时期,我倒觉得这个新经学时期,或者新学时期这个概括都不大好,真还不如概括汉语法学的西学时期,或者汉语法学的中西融合时期,可能更好。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就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要这样来概括可能比你那个经学时期,因为经学就得说一大堆,而且经学又是过去的老的,现在新的怎么概括?我觉得这个概括有点毛病。
第二,这个书提出来三个世界,我觉得以规范世界作为中心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三个世界,一个叫生活世界,一个叫规范世界,一个叫意义世界。他用这三个世界来讨论汉语法学的问题。这三个世界,法治和法意处在两端,分别出动,作为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都来源于生活的世界,并且独立于生活的世界。
旨在规制生活世界,料理中国人生,招抚中国人心。法律又是一种意义体系,可以预人类心灵中最神圣而超越的理念和情感相连。
所以汉语法学在与中国的世道人心和世事人情,由此创造中国精神和智慧的现在中国法律文明,这是章润对这个问题一些论述。我觉得这三个世界的概括确实对包括汉语法学在内的法学和法哲学的研究对象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概括。
我们如果以这个规范的世界作为中心,能够从生活的世界提炼出规范的东西,而使他能够符合意义世界的要求,凸现意义世界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作为法学或者法哲学分析对象来说是说的很清楚,而且这个关系也讲的很清楚。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的一个探索和贡献,就在于对汉语法学的哲学基础的讨论,主要就是关于中国古典的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他在书里面论述了中国先贤关于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既善又恶,明确指出中国心性论,更加强调积善即善,对人性和人心保持理解同情的态度。
所以他是这么来解读这个事情,既不站在性善一边,也不再性恶一边。因为中国古典文献里面这些东西都有,怎么理解?这里面对恶和善做了一个解释,可能和一般人的说法不一样。他的所谓恶是不包含任何伦理谴责意义,仅仅是指人类有自爱和扩张本性,以自我为圆心,以私利做半径,将你做无限扩大化的倾向和可能。
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作为理性认,所以这个恶是这个意义上的事情。这里的善是指法律引导个体主义的理性人,根据利益的计算来处置自家的行为,从明理出发,步步甚行,最终守法,即为善境,这个善就是法律上的善,能做到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就是正确的了,当然进一步的善是更高的要求,咱们不说他了。
所以这个解释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认为法律以恶的个体作为源头之人,以社会化了的守法公民作为最后之人,实现从恶的预设出发,最终达至善的预期。
所以实际上法律上的人,无论是最初的人还是最后的人都是法律上的人,或者平均的常人,不是共产党讲得那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们的立法,我们的司法以这么个东西作为基础出发的话,我想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的状况可能都不是从这出发,要么从高的出发,要么从低的出发。这是我想他探索的另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他这里边汇通古今方面比较精彩的地方就是对天理、人情、国法的解释,这个作为汉语法的运用是和理论解释架构讨论的。天理就是一种德行本体,一种普遍的善,一种超越的意义实践,就是一般开放的、超越的自然之法,天理就是西方的自然法,我觉得这个理解是对的。
所以也就是一种基于人文主义的正义法的概念。这里涉及到的人情是指人类基本的情和义,而不是指那些中国人的人情,不是指的情面,不是指的私人私益,不是走后门、拉关系的情。
我觉得这样一个理解来看,把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作为一个法律的解释框架,即将三者等量齐观,又有所区分。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东西,经过近百年的一些批判、一些演变,确实能够回答法学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也能够对我们现实中间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借鉴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说到底天理和人情,人情根本上也符合天理,天理也必须符合人情,不然的话这三个东西就联系不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章润认为这三个东西是极高明,真是大智慧。
对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些分析,认为这个东西囊括了法治的基本因素,他的优点就是将现象世界和超越世界沟通,在内在上牵线搭桥,而且他提出这个东西对立法者和司法者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严防人们趋利枉法,而且这是中西合璧,古今一体的趋势。
我觉得对于这一点来说,确实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没有假借西方的上帝之手,或者一些超验的东西,而是直接付诸于世道人心,直接从人生伦常,从他的历史正当性推出正义法的观念,这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历史发展的。
再一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语言的问题。语言是一个表义系统,汉语法学的法规、法义、法言、法语都得靠汉语表达,汉语有它的简洁的好处,大家也有它的含糊的缺陷。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咱们的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语言的现代化和法律的现代化,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方面。所以这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点,第一章是他主要的一章,第二章讲法学历史主义论纲,这里面我倒觉得因为历史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观实际上也是一个方法论,所以其实把这章写成汉语法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倒是很有意思,但是你现在的写法,仍然在很抽象的层面上来谈,其实作为方法论倒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开拓。
比如作为方法论,比如作为一种叙述的方式,作为他的价值判断,作为他的相对性,这些关系我觉得都是可以从方法论上来讨论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没有讨论。所以我觉得不解渴,你前面讨论的和后面讨论得有些地方是重复的,只是不同说法而已。
我现在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最后一章,我觉得他是把中国和德国做一个比较,说明汉语法学的历史法学的品格,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像德国那样进一步占有历史资料,能够完成汉语法学的历史转型和现代化建设,这是最后一章。我觉得这一章也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如何把这个比较说的很清楚,我们从那能够借鉴什么,怎么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从这个角度讲。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他在汇通古今方面的一些不足,就是我看了以后觉得不解渴的东西。一个不解渴,就是他前后三章几乎在同一个层次上,没有分开增长。第二,汇通古今的时候只讲了中国一些正面的东西,而没有讲中国负面的东西,我想既然要汇通,不讲负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恐怕汇通不了。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把家国天下和天理、人情、国法并列,作为古今汉语法学精神境界和文明品格的一个特异之处来讨论的。我觉得他过分强调了家国天下这句话体现的世界主义和世界精神。
但是没有看到这句话缺乏的恰好是现在缺的,就是个体的独立、自由的基础。我觉得没有这样一个基础,那一套东西没有办法立足,没有办法生根。为什么这么说呢?缺少了这个基础,咱们现在的历史和现实往往是家国不分,从家国不分到当国不分,从家天下演变到现在的党天下。
所以作者其中的逻辑和机制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分析。这正是我们汉语法学转型要完成的任务。但是缺了这个以后光讲家国天下,这个问题说不清楚,还有一个,缺了这个基础以后,传统法治强调的是个人修炼,自我克制,把德治和法治对立起来,而不重视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衡。
所以咱们历史上和现实中,最高统治者既是政治上的王者,又是道德上的楷模,既掌握政治权力,又掌握话语权力,因为我们的政治权力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名君、贤相、清官、顺民的形象和意识。
我觉得这恐怕是中国现在转型里面非常大的问题,咱们这个会要开,通知那么多学者,我来这个会你也干预,不能来,你有什么权干预我?礼拜天我休息不行吗?我想说来了你能把我怎么办?我回去你把我怎么办?开除?停发工资?那样就有意思了。
但是这个问题反映的是什么呢?我们学者仍然没有独立意识,仍然是上面怎么说我们怎么听,怎么干,不用自己脑子去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是中国现在的大问题,你想想这些大牌学者如此,老百姓该怎么办?你们都是代表中国的精英,你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这么个思维方式,这么个行为方式,老百姓怎么办?中国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章润在这个问题上恐怕得考虑这个事情。
正因为咱们缺少这样一个基础,咱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往往缺乏平等精神,先是株连和连坐,后来就是血统论,现在是皇二代,这不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东西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真是咱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谈论家国天下,离开了个体独立恐怕很难说的清楚,而在这一点上恐怕我们要借助西学,而且怎么把两者结合起来,使得天下主义成为一个个体独立、合而不同,天下有一家,中国为一人的这种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考虑的。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思想,但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近代由于经济落后,中国经济学乏善可陈,中国几百年没有什么东西,现在的经济学都是舶来品。但是我觉得法学不同,中国古代有立法和行政,有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结构,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间出现一系列大家,这一系列法学大家提出一系列思想,有一系列著作。
我觉得在法学上中国的情况比经济学要好得多,基础要厚实得多,所以奠定了现代汉语法学基础,架设了现代汉语法学转型的桥梁。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是自己说话不腰疼,我觉得法学界同仁们应该确立一个雄心,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的东西真正学起来,不光是他们的精神,而且是他们那套理论,能够把中西古今真正能够汇通起来,真正完成汉语法学的转型和现代化任务,我觉得这一点比经济学要好得多。所以我希望我们法学界的同仁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作者简介】张曙光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














![张曙光任合肥书记 张曙光[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https://pic.bilezu.com/upload/7/37/73747fe74e61713df6cbb1fb6a8009b1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