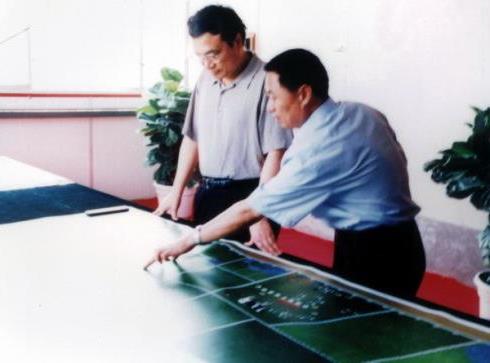闵惠芬教二胡 当代二胡与闵惠芬—为2006年7月“第二届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学
二胡的发展历史和其他民族乐器有些不同。它和琵琶、古筝、笛子等的发展不一样,和古琴更加不一样。二胡的发展特点是:历史短,起步高,发展快。和琵琶、古筝、笛子、古琴等乐器带有文人音乐、宗教音乐特点不同,二胡具有鲜明的平民、草根特色。
20世纪的中国二胡发展历史,以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为界,又可分为前半个世纪的现代二胡,和后半个世纪的当代二胡。
闵惠芬则是中国当代二胡的杰出代表人物。
百年二胡四阶段
二胡的主要发展是在20世纪,开山之人是伟大的民族音乐的开路先锋刘天华。在刘天华之前,二胡的发展虽然已有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但是它只是作为一种伴奏乐器而不能独立存在,也没有留下更多的传统二胡曲。比之古琴的代表作品《广陵散》、《潇湘水云》等,琵琶的《十面埋伏》、《阳春古曲》等,笛子的《梅花三弄》、《鹧鸪飞》等,古筝的《寒鸦戏水》、《出水莲》等,而二胡的遗产却显得太少——它留下的仅有几首“传统乐曲”中,《汉宫秋月》是刘天华在20世纪20年代末从广东音乐移植到二胡上面来的;《虞舜薰风曲》则是周少梅从琵琶曲移植过来的。
因此,传统留给刘天华的,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由刘天华倡导的“二胡革命”始于20世纪初,在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中,二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刘天华时代”。这是刘天华在二胡领域披荆斩棘、开创局面的艰难时期,以他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开设二胡专业为标志,特别是以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创作的《病中吟》、《苦闷之讴》、《空山鸟语》等二胡“十大名曲”为界标,这“十大名曲”是耸立在20世纪中国二胡发展之初的第一座里程碑。
与刘天华处于同一时代的还有阿炳和吕文成,他们也对中国二胡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阿炳是将民间的传统二胡发展到了极致,其代表作《二泉映月》、《听松》等成为中国二胡史上永恒的光辉。吕文成则对高胡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使高胡在广东音乐中成为主奏乐器,广东音乐中的许多精品,如吕文成的《平湖秋月》、《步步高》,易剑泉的《鸟投林》等,都是由高胡主奏的乐曲,因此也是广东二胡的代表作。
刘天华时代的二胡,是从传统二胡向新二胡的过渡。其风格继承了传统二胡悲凉凄婉的特色,这在《病中吟》、《悲歌》、《二泉映月》等作品中可以完美地体现出来。从风格来说,这一时期的二胡可以称之为“悲情二胡”。悲情的确最能发挥传统二胡的本色。
刘天华在北方闯出了一条专业二胡的新路,吕文成则在南方走着商业二胡的路子,阿炳却在无锡的一隅,继续默默走着传统二胡自生自灭的路子。他们三人都是优秀的演奏家,又坚持为自己所熟悉的乐器创作,这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了整个20世纪二胡音乐的发展。
刘天华的《光明行》在这一时期算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他竟然让二胡拉出了一首豪迈雄壮的进行曲,拉出了军号般的音调,这无疑是对二胡的一次大胆的革命!是二胡风格的一次大的转变。刘天华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谱写出《光明行》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展现和直接表达。刘天华的新二胡,从本质上说就新在这里。
20世纪二胡的第二个发展时期,是刘天华的学生的阶段。30、40年代,刘天华亲授的学生们,或者他的学生的学生陆续登上了二胡的舞台,如吴伯超、储师竹、王君仅、蒋风之、陈振铎、刘北茂、陆修棠、俞鹏等人。他们在战乱的年代继续开拓、创新、前进,又产生了《小花鼓》(刘北茂)、《铁窗吟》(王君仅)、《怀乡行》(陆修棠)、《雨后春光》(陈振铎)、《凯旋》(储师竹)、《平原竞马》(俞鹏)、二胡四重奏《凯旋》(储师竹)、二胡协奏曲《阳光华想曲》(黄锦培)等二胡作品,这些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虽然都无法与刘天华、阿炳和吕文成的优秀二胡作品相比美,但是也从比较广阔的领域反映了这个时代,并且还出现了二胡重奏曲和协奏曲这样的新体裁。
二胡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初期,时间在50、60年代。茁壮发展中的新中国音乐教育机构培育出了新一代的二胡演奏家,并涌现了一批能够代表这一时代的二胡新作品。从演奏人才来说,新出现了像黄海怀、项祖英、鲁日融、王国潼、蒋巽风等人,闵惠芬在这一批演奏家中属于“小字辈”。
就二胡新作品方面说,产生了像《丰收》(王乙)、《春诗》(钟义良)、《三门峡畅想曲》(刘文金)、《赛马》(黄海怀)、《河南小曲》(刘明源)、《秦腔主题随想曲》(鲁日融、赵震霄)、《豫北叙事曲》(刘文金)、《山村变了样》(曾加庆曲)、《湘江乐》(时乐濛曲)等等。
这些作品在题材上大多歌颂春天、歌唱丰收,表现欢乐的节日,风格方面大多从民间音乐中汲取鲜活的音乐素材,表达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强烈感受。
年轻的二胡演奏家们推动了二胡风格的一次大转变——由原先的悲情二胡转变为现在的激情二胡和欢乐二胡。这种二胡美学的大变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适应了民众的审美的变化。
这是百年间二胡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段。除了二胡演奏家继续谱写二胡新作之外,作曲家刘文金专门为二胡谱写了《三门峡畅想曲》和《豫北叙事曲》等作品,专业作曲家的介入,极大地提高了二胡曲的专业创作水平,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在这一时段中,由黄海怀移植的二胡曲《江河水》属于一个异数。就像刘天华的《光明行》在“悲情二胡”时代奏出了一支威武雄迈的进行曲,《江河水》则在“欢乐二胡”的时代唱出了一首凄切哀怨的大悲调。这两首乐曲在它们的时代都是属于“唱反调”的作品,但是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却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作品。
第三阶段的后半段是十年“文革”,二胡和其他的民族乐器在这十年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成为百年二胡发展的最为黑暗的时段。江青者流一方面大肆迫害民族器乐工作者,一方面又将民族乐器变成为“文革”政治服务的“战斗工具”。但是,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二胡仍然在顽强地发展着。创作方面,产生了王国潼的《怀乡曲》,陈耀星的《战马奔腾》,刘长福的《草原新牧民》等,使二胡在绝境中得以继续向前。
第四个阶段,即新时期的二胡,是二胡的又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文革”结束之后,在20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二胡获得了一次飞速的提高。这一时期培养出了一批技艺高超的青年二胡演奏家,如余其伟、姜建华、朱昌耀、邓建栋、陈军、周维、许可、宋飞、于红梅、马向华等人,他们将二胡的演奏技巧又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胡曲的创作方面,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并产生了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产生了一大批协奏曲形式的大型二胡作品,如《新婚别》(张晓峰)、《长城随想》(刘文金)、《第一二胡狂想曲》(王建民),《天山风情》(王建民),《第三二胡协奏曲》(郑冰、张小平)等;二是涌现了一批短小精悍的广受欢迎的二胡新曲,如《一枝花》(张式业编曲)、《陕北抒怀》(陈耀星、杨春林)、《葡萄熟了》(周维)、《姑苏春晓》(邓建栋)、《椰岛风情》(陈军)等;第三是产生了“新潮音乐”风格的二胡曲,如《双阕》(谭盾)、《梦四则》(何训田)、《索》(金湘)等,以突破传统的形式,开拓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
二胡演奏技术在这一时期又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将小提琴的炫技性乐曲如《野蜂飞舞》、《卡门主题随想曲》等移植到二胡上来,飞速的快弓走指让人叹为观止。
于是,在20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二胡又出现了一个全面兴旺发达、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出现了二胡艺术大飞跃的可喜景观。但是也出现了一种倾向——片面注重炫技二胡,而忽略了传统二胡特有的艺术表现力。
总之,经过了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中国二胡已经出现了全新的发展面貌,已经由处于民族乐器边缘地位而移到了中心地位,已经由纯粹的伴奏乐器走上了独奏乐器的舞台。由“地本庸微”的传统二胡而到处于舞台中央的新二胡,这一百年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从演奏美学上说,已经由擅长演奏凄怨惆怅、含蓄蕴藉的风格,而变为善于表达欢乐歌舞、激越奔放的新风格。
这就是当代二胡对传统二胡的发展和超越。
当代二胡与闵惠芬
上述二胡发展的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属于“现代二胡”,后两个阶段属于“当代二胡”。闵惠芬是中国当代二胡发展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闵惠芬四岁。因此她完全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二胡演奏家。在20世纪中国二胡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她学习二胡并在演奏上初露头角;而在第四个阶段,趋向成熟,走向辉煌。
闵惠芬出生于江南水乡宜兴,离无锡约50公里,离江阴约100公里。这是一片诞生和蕴育二胡名家的福地,就在以无锡为中心的江阴、常州、苏州、宜兴等地,20世纪前后曾诞生过阿炳、刘天华、吴伯超、储师竹、蒋风之、陆修棠、王乙、闵季骞、闵惠芬、许可、姜建华、邓建栋等多位二胡家,以至江苏省因此而被称为“二胡之乡”。
这片水乡钟灵毓秀、人文斐翠,也是孕育江南丝竹的地方。闵惠芬具有一种与身俱来的二胡素质,从小又在这里受到了民间音乐的熏陶,也得到了她的父亲——二胡演奏家、教育家闵季骞——的悉心教导。
闵季骞在南京国立音乐院学习时曾随储师竹学习二胡,而储师竹则是刘天华的嫡传弟子。因此,闵惠芬在一开始学习二胡时,就和刘天华天然地挂上了勾。从此她就抱定了一个信念:要让二胡走进千千万万“一般民众”的家庭。
她抱着这一坚定的信念苦学苦练,16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在王乙老师的指导下,技艺渐进,并在1963年的“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使她在二胡演奏上初露头角。
右起:获得1963年全国二胡比赛一等奖的闵惠芬、蒋巽风,获小提琴比赛一等奖的郑石生,获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优秀奖的陈稼华。 1964年升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后,直接随陆修棠老师深造,在演奏上和创作上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她所擅长演奏的曲目,是以第一阶段的《空山鸟语》、《二泉映月》、《听松》和第三阶段的《春诗》、《灿烂的五月》等为主的。这些曲目都以江南特色为主,然而她对第三阶段产生的西北风格的作品如《秦腔主题随想曲》、《迷糊调》等的特殊风格也掌握得很到位,对《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等新作品的接受和掌握也非常的敏捷。
这时的闵惠芬,小荷才露尖尖角,显示了二胡演奏方面的无限的发展潜力。然而好景不长,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陆修棠先生即因受不了红卫兵的污辱,8月底即投河自尽,而王乙先生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实行隔离审查。
闵惠芬担心王乙老师想不开而走陆修棠老师的路,因此她每天都到关押王乙老师的地下室的上面练琴。
她想:“绝对不能让王乙老师也死去,我要用琴声来陪伴他。” 关押王乙的“牛棚”上面是一个学生洗脸间,她就每天到这里“疯狂练琴”,甚至搬来四张凳子,晚上就在里面睡觉。她拉二胡、京胡、坠胡,甚至拉小提琴,进而又用二胡拉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
她用琴声来昼夜陪伴王乙老师,她还冒着危险让一个小同学带纸条塞给王老师,上面写着“要挺住,会过去的”等鼓励的话,让王老师放弃自杀的念头。
这对绝望中的王乙老师真是莫大的安慰!“文革”是师道尊严被彻底扫地的时代,难得还有闵惠芬对老师的这一份诚善至情。“文革”期间闵惠芬的二胡得到了一些特殊的表演机会。首先是1973年随上海交响乐团赴京演出,由她演奏了《二泉映月》等曲子。
6月24日江青在审看了这台节目后,对闵惠芬演奏的《二泉映月》还讲了几句赞赏的话,江青说:“《二泉映月》曲子还是好的。但可以动一动,出些新,有些地方云彩遮住月亮,有的地方月亮透过云彩,突出月亮,明亮点。
哀怨情绪要表现出来。”这样一来,原本担心受到批判的阿炳的《二泉映月》,从此可以公开演奏了,竟然在“文革”期间复活了起来。另一次,是1974年7月北京成立了“中国艺术团”,闵惠芬也被调入该团,此后,《江河水》、《喜送公粮》、《赛马》、《二泉映月》等二胡曲成为她经常演奏的曲目,她还改编了《红旗渠水浇太行》(与沈利群合作)等新的二胡曲目。
1975年3月,闵惠芬突然接受了一件极其重要的秘密工作:为病中的毛主席录制二胡演奏的京剧唱段,先给了三首:《卧龙吊孝》、《逍遥津》和《斩黄袍》,后来又给了《朱廉寨》、《文昭关》等,一共十个唱段。
这时,有关方面还专门派了京胡大师李慕良来指导闵惠芬。
在李慕良的悉心教导之下,闵惠芬用二胡移植了京剧唱段《卧龙吊孝》、《逍遥津》等十段音乐,全部录了音。这些作品成为后来闵惠芬的保留曲目,并启发她开始了一个重要的创作课题:“器乐演奏声腔化”。“文革”十年是非常特殊和反常的时期,闵惠芬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很特殊。
开始时由于主科老师陆修棠被迫害致死,王乙老师受到隔离审查,这些事情使闵惠芬感到震惊,她对“文革”有了直接的反感。她用琴声来陪伴老师、帮助审查中的老师度过难关的事情,充分体现了闵惠芬的正直和善良。
“文革”后期,她在参加“中国艺术团”的前后,又受到了特殊的关照:江青直接表达过对闵惠芬的关心,参加为毛主席移植京剧唱腔的事情,也是一件特殊的政治任务。
但是闵惠芬以她特有的正直品格,使她没有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路线斗的漩涡中失去方向。她真正做到了“常在江边站,就是不湿鞋”。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文革”中闵惠芬演奏得最多的两首乐曲是《二泉映月》和《江河水》。
这两首作品都是表现凄婉悲哀的情绪,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气氛大相径庭。上段文中亦提到《江河水》属于建国初期二胡作品中的一个异数。“文革”时期能不能演奏这类作品?演奏之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许多人是为闵惠芬捏一把汗的。
而闵惠芬自己对这些作品更有深一层次的理解。1973年她演奏《二泉映月》的时候,曾经给自己提出了“这年头,我这样拉适时不适时”的问题,冥冥中她似乎听到了阿炳的回答:何谓适时?适时者,乃合天意,合民心也。
你看天下,富饶的中华大地田园荒芜,哀鸿遍野,万民饥肠辘辘,前景无望,朝野上下,思潮混沌,人心浮动,国无宁日,今与昔何等相似乃尔!不堪忧伤,不堪忧伤。我和你们对这世道岂能袖手,岂能观望,岂能歌功颂德。
琴音含人心,哀音惊世人,这是人间正道,我等应立正祛邪,至少出污泥而不染。①这明明是借阿炳之口,道闵惠芬所想。这说明了:闵惠芬在“文革”期间顶着风浪反复演奏《二泉映月》,是有深意存焉。
而且,“文革”后期闵惠芬奉命改编的二胡曲《逍遥津》、《卧龙吊孝》等唱段,成了“文革”期间二胡曲创作的异数——这些唱段在当时全部属于“帝王将相”、“牛鬼蛇神”的封建主义遗产之列,悉数是该批判、该打倒的“封建毒草”!
就以那首高(庆奎)派老生唱段《逍遥津》来说,内容是表现汉朝末代皇帝献帝遭遇曹操逼宫时,悲愤欲绝的一段唱腔,不但是“帝王将相”,还是表现末代帝王穷困无路的戏,与“文革”音乐所要求的“革命性”、“战斗性”等相距甚远!
在“战斗二胡”盛行的年代,由于当时的特殊的政治需要,由闵惠芬改编、演奏的《逍遥津》和《卧龙吊孝》等曲,却作为“文革音乐”的一个特例而流传下来了。“文革”结束以来,闵惠芬的二胡艺术走上了完全成熟和超越,可以用炉火纯青四个字来形容她这一时期演奏的精深。
正如朱践耳先生所说:闵惠芬的演奏是“弦外有音,音内有心”。② 她的演奏,是她灵魂的歌吟,因而感人至深。80年代前期她因为重病,约有6年时间不能正常登台演奏,但她奇迹般地战胜病魔。
经历了炼狱,人生获得超越,演奏也获得了超越。闵惠芬在演奏舞台上再度辉煌,先后演奏了大型二胡协奏曲《新婚别》、《长城随想》、《川江》、《夜深沉》、《诗魂》等作品,为扩大二胡艺术表现力,为二胡创作的大型化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她并改编、创作了二胡曲《洪湖主题随想曲》、《宝玉哭灵》、《阳关三叠》、《音诗——心曲》、《寒鸭戏水》等作品。闵惠芬演奏的这些作品,就像是听她将音乐的生命向你细细述说。
她的演奏风格,也在由激越走向内敛,由奔放趋向控制,这正是她的演奏趋巅峰的表现。 闵惠芬病后复出,重新登台演奏。 新世纪以来,闵惠芬演奏、讲学的足迹遍及全国和世界各地,一方面是为了让二胡深入民众,一方面是为了让二胡走向世界,闵惠芬始终如一地在不知疲倦地奔忙着。
在闵惠芬出现之前。二胡基本上属于男性,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绝大部分是男性。自闵惠芬之后,优秀的女性二胡演奏家成群结队地产生。
80年代之后中国二胡女性化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的,但是闵惠芬的成功,她的榜样作用,也是当代“女性二胡”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闵惠芬在二胡事业上已经艰辛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她在当代二胡上建立起了一座丰碑,树立了一种精神——将二胡事业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的闵惠芬精神。
这座丰碑,是检视我国二胡成就的重要标尺;这种精神,永远会鼓舞我们在民族器乐方面奋勇前进。--------------①引自闵惠芬:《孤独的夜行者》。
载《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傅建生、方里平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②朱践耳为“闵惠芬从艺五十周年音乐会”题词(2003年冬),载《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傅建生、方里平主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出版,插页。











![[转载]致河南省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公开信](https://pic.bilezu.com/upload/4/d6/4d60358173ba3cea2865f3d29b0969d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