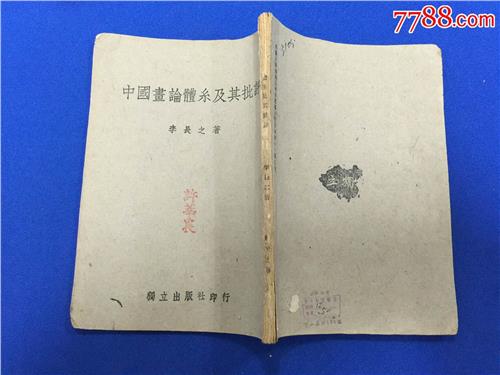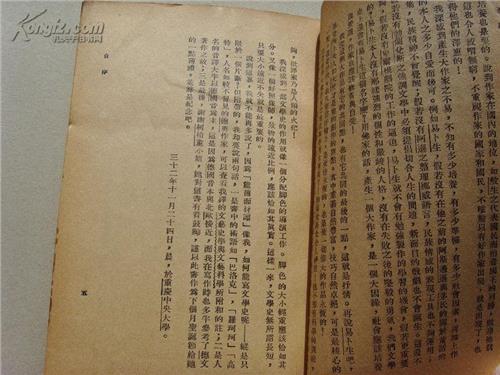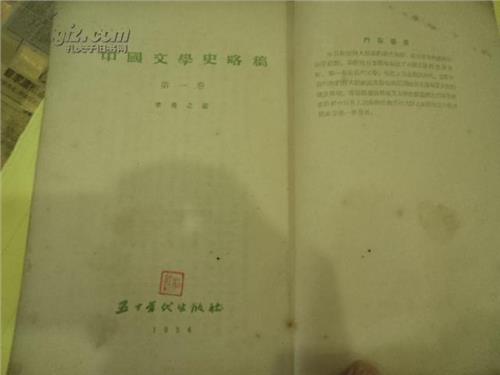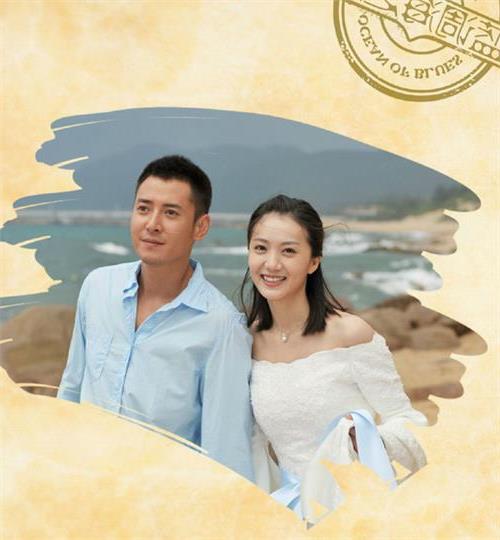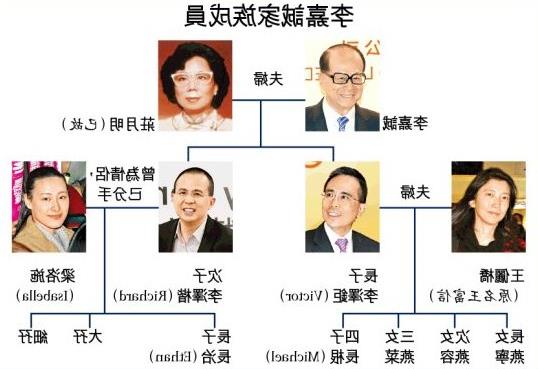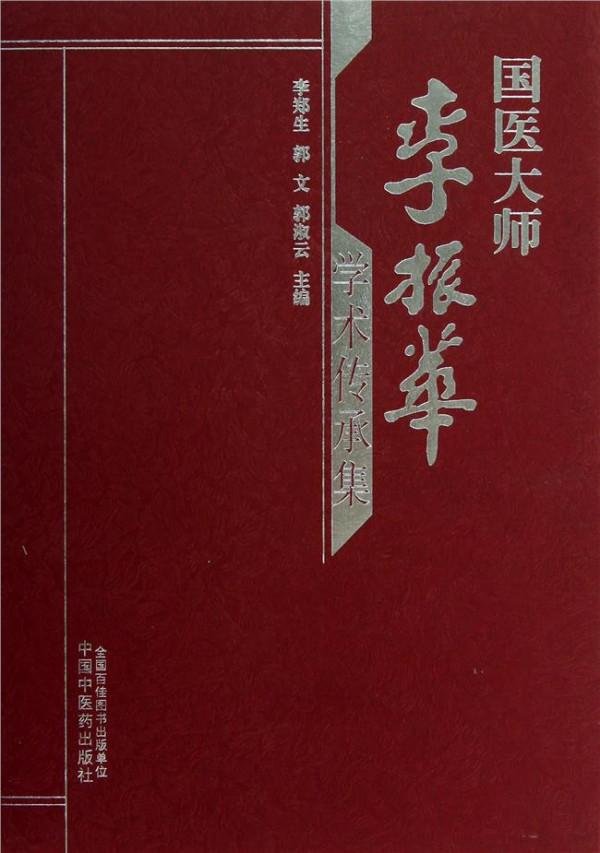李长之感情的型 试析李长之“感情的型''文学批评观的当代解读
论文摘要:李长之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卓有成就的美学家、批评家,一生著述颇丰,其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美学建构,是以“感情的型”为核心理念的。这一旨在建立中国转型时期的现代美学批评范式,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提供了新的话语和阐释空间。“感情的型”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理念,受到当代学人的关注,在今天也仍具有丰厚的诗学内涵和充分言说的必要,值得继续挖掘与探讨。
论文关键词:感情的型;批评范式;价值启示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才思卓越而且风格独特的批评家,在学术多元化和深入发展的当代,当他走出历史的尘封,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关于他的研究的实绩:在《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中,罗宗义先生肯定了李长之在鲁迅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温儒敏先生在《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及其传记批评》中,将其定位为“传记批评家”,首次明确了李长之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地位;郜元宝先生在《追忆李长之》中,进一步将他定位为“学者批评家”;张蕴艳在《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中,则颇有建树的为这位“传记批评家”做了传记批评,并对其批评理念做了详尽的论述;许道明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则把李长之同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梁宗岱等列为“京派”批评家,指出在推崇批评主体介入和情感动力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李长之是最突出的代表。
本文试图在以上阐释的基础上,着重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层面上探讨李长之“感情的型”的批评理念的学理内涵和价值旨归,探寻其批评理念在新时期的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正是左翼作家地位占据着主流的时代,但到了后期却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公式化与宗派主义倾向。与此同时,深厚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作为一份厚重的积淀,也成为当时批评者难以逾越的一个围城。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既有沉淀的模式,又有横亘的权威,然而李长之却勇敢地突破理论樊篱,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学理上的突围,他独有建树的提出了“感情的型”的批评理论,在文学理论界激起一股振聋发聩的回响,为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生机。一是它有别于当时左翼批评理论呈现的明显工具化倾向,二是有别于中华古老的印象式、感悟式、即兴式批评。由于李长之近承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远袭德国古典浪漫主义的美学堂奥,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的熏陶,使得他的批评理论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在强调批评理论应该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建构方面,李长之可谓早已具有真知灼见。
针对特殊历史时期文艺发展的走向,李长之在批评中突出了对文学中“情感”因素的注重,较少带有时代和阶级的色彩,在社会功利的价值批判标准之外强调审美一维;而针对在传统中过分强调审美一维又提出“理智的硬性”,旨在于情感和理性之问建立一种平衡,寻求一种张力,从而更好的指导批评实践。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他充满激情的完成了大量传记批评和理论著作的撰写,并有诸多译著和文学创作问世,“感情的型”的批评理念成为他文艺批评与创作中的一个价值准绳。
李长之认为,应该以“感情的型”作为文学批评的范式和尺度。他说“在我们看一个作品时,假设分析它的成分,接受物质限制的大小排列起来,我们一层层的剥,而发现一种受限制最小的层,根于某种程度而言,这近乎谈到文学的永久性。
”批评家首先要从“感情的型”的角度去审视和评价文学作品,而不能看重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因为文学作品有它独特性一面,它总是要表现“感情的型”,李长之所言极是,因为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中,都始终存在着情感的浸润与渗透 “一篇作品,所以能达到读者之前,是根于许多条件,我们可以先问这个作品的物质外壳,在剥去种种阶级、环境、时代的外衣之后,其次,我们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革命还是因为失恋,种种不一。
最核心的一层那只有令人把握的感情,它脱离任何对象而存在,同时又可以填入任何对象的感情,才是文学的实质。”李长之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所谓造型,既是情感形式化的过程,又是形式情感化的结果,“感情的型”作为内容与技巧的极致,是抽去了对象,又可填入任何对象的。
这种高度的抽象化、形式化,使“感情的型”可以从“外层”剥而显之,直至最后一层。也可以从“内层”穿而见之,因为“越下等的作品越使人注意了较外层而不能忘却,好的作品则闪耀着感情的光芒,收获情感的交流与触动,穿越外部感情的对象和质料指向永恒。
无论是从“外层剥”,还是从“内层穿”,“感情的型”都应成为文学批评实践的范式和尺度,因为“在感情的型里,是抽去了对象,又可填入任何对象的。”李长之说“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以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
李长之认为,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桃子,那么剥去了果皮、果肉、果核外面的坚壳后,剩下的果仁才是真正的核心与有价值的终极范式,进而言之,它甚至可以称为文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种子和时代传承的根源所在,是文学价值及生命力的源泉。
因为种子与根源的可派生性和繁衍性功能,才使横向维度——地域上的传播与纵向维度——时间上的承继成为可能。他把这种子归纳为两种极端的形态——“甘与苦”,或日“失望与憧憬”。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李长之写出了一系列传记批评和作家作品的评论,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少有的以自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批评实践的文学批评家。
有人将李长之“感情的型”的批评理念与苏珊·朗格“有意味的形式”做过比较,认为两位中外美学家颇具类似的心灵感应,但实际上,苏珊·朗格是从艺术的本体论层面强调艺术乃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即“运用艺术符号的方式把内在生命与情感经验的概念表现出来,从而创造一种幻象。
”而李长之“感情的型”则是旨在为具体作品确立一种审美规范与标准,是从方法论的层面所进行的一种剖析,具有更强的实践性。
如果说苏珊·朗格是在认识论的层面昭示了一种必然,那么李长之则解释了之所以然。苏珊·朗格鲜明指出构成艺术魅力的形式因,李长之则更注重阐释的是真正构成艺术本源并维系形式之维的质料因。
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却表现了李长之作为职业批评家所独具的辩识力与期许,他不但将“感情的型”发展修缮为完整的理论范式,并将其作为解读文艺甚至人生的试金石,始终指导并贯穿于自己的批评作品与创作实践。在《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中他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理路:“通常那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态度,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所谓不可以言传,是本没有可传呢,还是没有能力去传?本没有可传,就不必传;没有能力传,那就须锻炼出传的能力。对于中国旧东西,我不赞成用原来的名词囫囵吞枣的办法。我认为,凡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就是根本没弄明白,凡是不能用现代语言表达的,就是没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弄明白。”
“感情的型”的批评观旨在突出主体的能动性和心灵感悟的张力李长之认为,批评与对象的关系颇类似于产业领域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果说技术是对科学原理的功利性应用,那么与此相对应,批评家正是将美学规则应用于作品、作家分析的技术员,批评需要尺度。
比如在《孔子和屈原》中,他说“受了孔子的精神的感发的,是使许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光芒一敛,愿意作常人……反之,受了屈原的精神的影响的,却使许多人灵魂中不安定的成分觉醒了,愿意作超人。
他将中国的传统人格分成了两个类型,一类是像孔子那样代表着古典主义的人格特征,一类是像屈原那样代表着浪漫主义的人格特征。他们的区别在于如何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抹杀了个性,这样的群体也会腐烂朽败,反之,纯粹听任个性,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势必使这样的群体不得和谐安定。
李长之发现,在个人与群体这对矛盾中,孔子找到一个协调办法,那就是崇“礼”。“礼’可以说是情感与理智的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巧妙而合理的妥协。
孔子的基本思想就是保持个人和群体的和谐,不张扬,不狂放,既顺从社会的总体趋势,又适当地保持自己的个性,而屈原就不同了。“他的看法是,由个人到社会。于是他希望社会上各个分子都是全然无缺的,都是坚贞的,都是硬朗的,都是优美而高洁的。”
“可是屈原是不行的,它的社会理想既以个人为起点,所以对于个人的过失到了不能原谅,不能忍耐的地步。最后,他实在无从妥协了,于是出之一死。”屈原的个性特征使他只能选择自杀,“但他并不是弱者,也不是由于对世界淡然。
反之,他乃是一个强者,他未被世界上的任何邪思所征服,他没有妥协半点,最后,为了他自己的精神的完整,……才甘心葬身鱼腹。”然而,牺牲生命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不被人所理解。犹如鲁迅《药》中的革命烈士夏瑜,他为着中国人未来的幸福牺牲了,他的血却被中国人蘸着馒头做药吃了。
同样是不被人理解,孔子追求尽可能的让人理解,即“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屈原却清冷高傲,遗世独立。孔子和屈原都有理想,但孔子不仅有理想,而且能找到到达理想的途径。
屈原有理想,却不知道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所以,李长之认为“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
我们民族是幸福的。”这正是李长之对其“感情的型”理论的最好注解,他在批评实践中身体力行的运用“感情的型”的批评理念。他在理论中思考,在思考中进行理论与实践建树,走了一条用心灵感悟的路子,同时又用“理智的硬性”对情感加以清醒的认识和辨别,这是李长之所独有的可贵特质。
李长之对中国现代美学批评思想的建构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所强调的批评方法和为建立现代文学批评范式所做出的努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难能可贵的。如果说王国维建立境界说的参照系是中国古典诗词,那么李长之的理论参照系则是整个世界文学史,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是指人的生命感悟之高度,而李长之则将此种情思普遍化,并将之抽象为憧憬与失望两种元形态,不仅使之更具概括力,也使这一理念更加明晰,在文艺批评方法论上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
李长之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并未仅仅停留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新的视野,也体现在价值论上所追求的宏大高度。李长之在批评实践中强烈的价值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就对文本的解读来说,他以作家的情感、精神因素作为桥梁和中介,既发掘作家创作的外部因素,又能深入作品的内部世界,探寻作品的价值意蕴;从批评家的价值取向来说,他遵循着“文化——文艺——教化”的宏阔思路,希望文学批评能够起到教化人心、振奋民气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文艺创作原不只暴露黑暗,而且更重要的,乃是创造光明!
”抱怨旧天地不是文艺的旨归,文艺应书写梦想,并为人类呈示新天新地,才是根本追求。杨守森认为文学批评有四重境界,“第一层是复述归纳,第二层是体悟阐释,第三层是分析评判,第四层是提升创造。
与此相对应产生了文艺批评的四重境界,分别是传播文学信息,丰富作品内容,探讨创作规律,开拓思想空间。要达致第四重境界,除须具备广博专业理论与深邃细腻文学眼光的同时,还应具备对元理论的反思能力和超文学的批评视野。
应该说李长之是到达了第四种批评境界的。在李长之的传记文学批评中,始终渗透着强烈的社会道义感、文化使命感、启蒙责任感。李长之之所以把“感情的型”的理论演绎到传记批评实践中,其用意之一即在“立人”,也就是在古典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实现本土人格模式的现代转型,改造传统人格模式,挖掘传统人格中有利于人格现代化的基因,重建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完美、充实、健朗的现代人文品格,以实现新时代文艺复兴的梦想。
“感情的型”有两极终端的形式——“失望与憧憬”,这是李长之对生命的理解和生命价值的估量与期待,它既是作家独特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又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形而上的关怀与永恒情思。这一文化哲学命题,在学界热烈讨论“现代性后果”的今天,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价值启示。
人类现代性的张扬,导致了人类情感的失落,城市与资本的逻辑让人丢失了寻找意义的机会与空间,意义的缺失,复制、拼贴与解构,古典的遗弃,信仰的迷失,让人们无奈和失望,然而情感并不是单一的,它总是内含着失望与憧憬的两元,因此世界就不会成为死寂虚无的荒漠。
她是有着意义与价值内核的有机建构,是由失望和憧憬二者之间的张力而建构的动态磁场,人的终极关怀正生长在从虚无走向圆满的路途上,这一路途也正是人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
人类正是在失望与憧憬之间,经历多元的色彩和发展的形态,才演绎出人生百味与世界的精彩。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李长之的立场异常坚定,那就是,人类应当审慎的正视光明。李长之深刻论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纯文艺抓到的即是永恒,于是超时代,于是无变动不居可言,要它探索的只是人类对自己,对环境,对自然,对文化,对最后之物,对神之最后的关涉。
“人们不能因为时代而放弃对永恒的追求。”穿越历史,我们缅怀李长之的身影;回首人类探索的路途,我们应当记住李长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