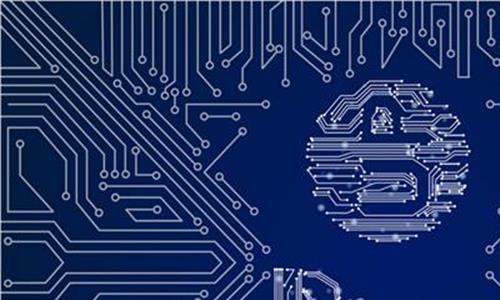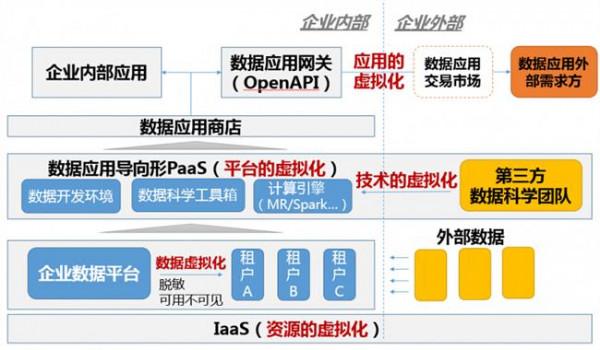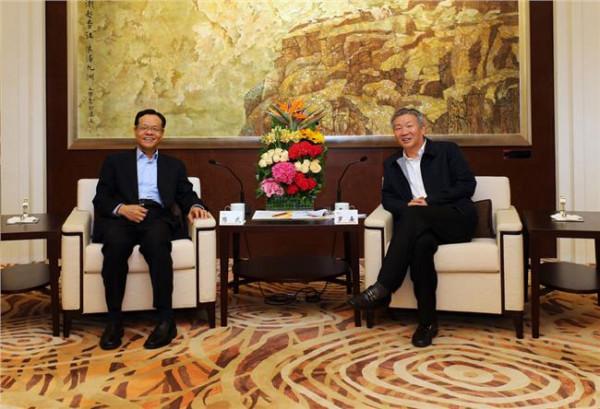龙宗智电子数据 【谏评】龙宗智:评“两高一部”电子数据证据规定|批评与建议
未明确区分取证行为性质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是允许初查时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同时对取证行为未规定方法限制。
根据“规定”第六条,“初查过程中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文义分析,该规定有两点含义:一是授权,即侦查机关在立案前的初查阶段可以收集、提取电子数据;二是赋予证据能力,即允许此阶段获取的电子数据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而不是仅仅作为立案的根据。
结合“规定”第一条关于电子数据定义和范围的规定,在初查阶段允许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如果在取证对象与手段上不作限制,实际上已包含大量的权利干涉型取证行为。
因为如前所述,对规定第一条所列四种类型电子数据中,除第一种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外,后三种类型电子数据的取证,不可避免地干涉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权,因此其中必然会包含强制侦查行为,甚至包括技术侦查行为,已如前述。对于公权力行使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如法律或法规已经授权,且未设置限制性规范,在实践中,权力行使机构必然会在授权范围内充分行使此项权力,而不可能自我设限。此一后果,可以想见。
由于刑事立案需要一定的条件,侦查机关接到各种立案材料后,就是否能达到立案标准常常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查核实。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条件下,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核实立案材料的有效方法,因此,笔者并不反对在立案前收集、提取电子数据;为提高证据效益和诉讼效率,也不反对将立案前依法收集的电子数据作为诉讼证据。
[8]甚至也不否认初查中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行为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利干涉性,如获取通话对象、时间的历史记录,以及当事人商业交易记录等,都可能干涉公民隐私权。
笔者认为,干涉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应当进行适当划分,一般的个人生活和商业活动情况即使属于个人隐私,也可不列为重要权益,因此,调取相关资料应作为任意侦查而不视为强制侦查。
但如住宅内的隐私,以及私人通信活动中的个人信息,因为与宪法保护的住宅权、通信自由和秘密权相关,则应当属于重要权益,在初查阶段不得干涉,否则属于程序违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在初查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这一规定基本反映了笔者前述观点,即初查采任意侦查方式,不得妨碍初查的人身权、财产权、住宅权及通信自由和秘密权,但其一般隐私权可能受到干涉。[9]有学者将任意侦查理解为并无任何侵权性,认为初查时收集电子数据只能采取不干涉公民信息权、隐私权、财产权等权利的任意调查方法,因此提出“电子数据的收集绝大多数不能在初查中进行。
”并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关于初查中方法限制的规定作为佐证。
[10]笔者对此一观点不太赞同,理由如前所述。再需说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规定仅限制对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的妨碍,并未提出干涉隐私权的限制问题。而上述规定中允许“调取证据材料”,必然涉及隐私权干涉。
而且这也是核实立案材料以决定应否立案的需要。如反贪局接到对某干部受贿的举报,为核实举报内容,调取其家庭交易记录及存款等资料,这是初查时常态和必要的做法。其中虽有隐私权干涉,但不认为是重要权益侵犯,不属于财产权妨碍,因此不宜列为强制侦查。
但另一方面要求,反贪局在查询其财务资料时,即使发现巨额受贿嫌疑,在立案前也不能冻结其财产,因为,强制侦查只能在立案后实施,这是一项必须强调的重要法律原则。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然后根据情况分别做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
法律并未赋予公检法机关在立案审查中采取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的权力,逮捕、拘留等对人的强制,搜查、扣押、冻结等对物的强制,只能在立案后的侦查程序中实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就技术侦查还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只能在立案后针对特定犯罪依法定程序实施技术侦查。由于立法意旨明确,立案前不能采用干涉重要权益、妨碍公民权利行使的强制侦查手段,已成实务界与学界共识。
为何强制侦查须以立案为基础,不立案不得实施强制侦查。是因为强制侦查直接干预公民基本权利,为防止滥用公权损害私权,必须遵循一定法律程序。制约强制侦查的基本法理,是前述司法审查原则和令状主义,即原则上由中立、独立的司法官员审查批准强制侦查,并以其颁发的,具体指明执行对象和执行方式的司法令状作为执行根据。
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和司法令状制度阙如,只是设置了一道立案程序,通过立案审批和办理立案手续,宣告刑事案件成立,确定犯罪嫌疑人,并为强制侦查提供法律依据。
一旦立案,强制侦查之门即被开启,全部对人和对物的强制侦查措施,除长期羁押(逮捕)可能需要一种准司法的外部审批以外,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并实施。
这种强制侦查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的制度,难以抑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效益而过度强制的冲动,因此并不符合司法人权保障的现代要求。不过,在现行体制中,立案程序毕竟设置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以防止国家调查权力毫无约束地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规定”未限制初查中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方法,在规定拟制者方面,可能也有其自身的考虑,即担心这种限制,会**减损侦查机关在初查中调查电子数据证据的能力。而且对某些问题,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其一,“在线提取电子数据”中的通信和人员行踪监控,以及通过“网络远程勘验”提取电子数据,是否作为或以何种标准作为技术侦查管理,并是否应当禁止在初查阶段实施;其二,扣押电子数据载体,能否在初查中执行;其三,能否在初查中冻结电子数据。
等等。类似问题,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也可能因此影响在文件中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对上述问题,笔者的初步意见是:其一,按照划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标准以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信监控以及通过“网络远程勘验”进入已采取防止进入措施、权属明确的信息系统提取电子数据,属于强制侦查,有些甚至是高强度的强制侦查,因此应纳入技术侦查管理,不能在立案前实施。
而以常规方式对网站远程登录查访,则应属于一般调查措施,可以在初查中实施。对人员行踪的电子监控,因为并不妨碍当事人人身自由,且基本属于公共空间的活动信息,权利干涉性较弱,不宜纳入技术侦查程序管理,可以在初查阶段实施,但在初查时不能实施具有严重侵权性的住宅内监控。
其二,扣押证据具有强制性,属于强制侦查,不能在初查中实施;初查中可以经相对人同意以提取笔录提取证据(此为普遍实践方法)。
也可用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但在初查阶段的调取证据,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证据持有者应当向办案人员提供,但不属于强制扣押,不产生强制执行效力。如要强制执行,需在立案后以扣押证据方式实施。其三,冻结电子数据与冻结财产不同,如果冻结电子数据不妨碍电子数据占有者的数据活动,则可在初查阶段实施,反之则因妨碍权利,不能在初查中付诸实施。
当然,笔者上述意见不一定正确,不过,划出法律界限,进行初查手段规制十分必要。否则初查中的随意性就难以避免,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取证程序规制的底线就可能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