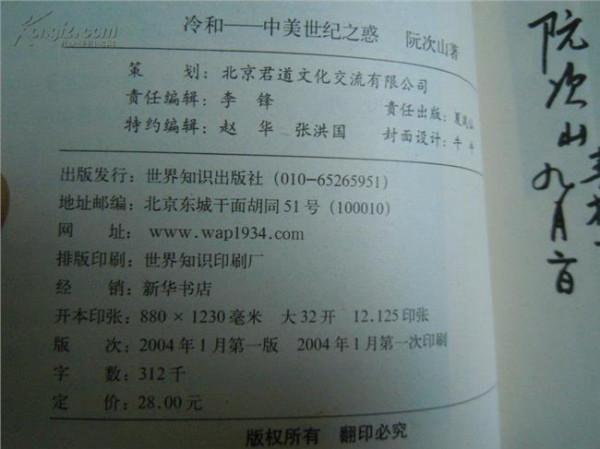朱良志书画 朱良志:传统文人画的价值是智慧之画
朱良志,1955年生,安徽滁州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1999年底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出版有《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真水无香》、《中国美学十五讲》、《曲院风荷》等著作10余种。
倘要概括朱良志教授研究中国绘画的状态,或许可以用诗人翟永明《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入山幽致叹何穷》一诗中所写来形容,“……到画中去、作画中人、自徜徉/没有一个美学上级可以呼唤你!/你不是从画中走下,而是/从人间走入、走上、走反/从虚无中逃脱/向植物隐去”。近三十年来,他的研究将文人水墨画的深刻、丰富、细致以及画家的人生寄怀充分展现出来。
做人文研究并不为攫取名利
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院是朱良志的办公室,原来是燕京大学的职工宿舍,物理学家周培源曾居住在这里。经过重建的这座美丽的院落,屋中有假山、翠竹、小桥、流水、游鱼,通透的天窗外,树影婆娑,富有诗意。不远处的灯光在傍晚升起的雾气中闪烁,遥远而迷离。朱良志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安静地读书、喝茶、会友、写作,“万物皆备于我,不是在物质上为我所有,而是一种心灵的腾挪。心中通灵活络,是处皆为山林”。
朱良志的新著《南画十六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洋洋近70万言,选取了16个关键词来介绍元明清的16位画家,如黄公望的“浑”、沈周的“平和”、董其昌的“无相法门”、陈洪绶的“高古”、金农的“金石气”等,探讨支配文人画发展的根本因素——生命真性问题。
“南画,特指中国传统文人画,文人画家所追寻的这种超越形似的真实,只能说是一种‘生命的真实’。”在第七观里,朱良志用“幻”来形容陈道复,“文人画不是对幻形的抛弃,而是超越幻形,即幻而得真……在他(陈道复)看来,绘画表达的是生命的觉性和智慧,而不是拈弄花鸟,涂抹山川。”
“即幻而得真”听起来玄而又玄,朱良志则结合画家的画作和经历、文章,从中国哲学和美学层面,揭示“生命的觉性和智慧”是如何在绘画中呈现出来的。书中400多幅插图多是朱良志到国内外博物馆收集得来的,“自己去跑才有感觉,靠别人做终究隔了一层。
我以前做八大山人研究,到江西去住了好长时间,我在他曾生活的地方流连,追踪当时可能发生的情景。我研究石涛也是,我曾经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读了8个月的书,每天从北大骑自行车到北海,在那个古色古香而又沉静的地方读书,度过了辛苦而又极幸福的时光。”同时,朱良志作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研究员,可接触到在国外的中国绘画,“中国古代的书画有四分之一在美国。”
朱良志年轻时在安徽南部学习、工作,皖南山水的滋养和桐城派重视义理、考据、辞章的潜移默化影响,与他后来细腻的艺术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良师教诲下,他从1984年开始研究中国绘画。“我的老师大都是在‘文革’中被下放的,当他们回来重新站在讲台上教书,把这个当做生命一样重视。
我有一位老师祖保泉先生,他原是黄侃的学生,于书法、篆刻、古体诗词都有很深造诣。他当时是我的系主任,我大学毕业就做他的助教,那时的助教真是名副其实,我帮他擦了7年黑板,他上课,我就坐在他旁边,讲完之后我上去擦黑板。当时心情时有郁闷,为什么不直接让我上课?现在想来,这真是对我最好的训练,对我后来的学术有极大影响。”
《南画十六观》文辞优美,富有卓识和洞见。“我就是把我自己内在的感觉写出来,比如说你看倪瓒画中的亭子,空空荡荡,四面都没有,站立在萧瑟的天幕中间,那种内在的动感就是在寂寞中寻求对话而无从对话。我有时读到他,真的感觉这个对话正在进行,在跟自己对话,跟天地对话,跟往古对话。有时,我就不敢再写,不敢再画,生怕打破了这种千年之梦。我的这些文字,呈现的是我的思考,以及我的生命状态。”
朱良志虽研究古代艺术,但并非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无关当下。“我觉得中国艺术太有意思了,但是研究的力量非常薄弱,做人文研究并不是为了攫取名利,这毫无意义,而是解决人的生命的困境。”
传统文人画是智慧之画
记者:《南画十六观》写了16位元明清的画家,是如何选择的?
朱良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叙述方式,因为我写的是一个观念问题,是追踪文人画的真性问题,所以我选择一些在画史当中并不是最有名,但是却跟我所追踪的观念密切相关,通过这种叙述作为本书的主干。
文人意识是一种自我体验的意识,是一种和庙堂相对的山林感觉,是一种在束缚之外的叙述,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关切。艺术中文人意识的开始可能追溯到中唐时期,理论的揭示是北宋时期,比如苏东坡、米芾、黄庭坚,但比较形式化,并不能完全在自己的艺术中贯彻,比如黄庭坚,法度对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文人意识一开始体现于书法,然后到绘画,由绘画影响到整个中国艺术,包括园林建筑、音乐。元代是文人意识比较成熟的时候,在艺术创作中贯彻这一观念,主要从元代开始,尤其是绘画,有一些伟大的画家出现,比如倪瓒、黄公望。
文人绘画引起轩然大波是明代中期,地域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南方文明,像沈周、文徵明,一直到董其昌,以及康熙时期的八大山人、石涛、龚贤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到雍正之后就渐渐消歇了。
记者:在探讨文人画的真性问题时,你写到一个画家,会涉及他的经历、性格、思想,但跟传统的知人论世不太一样,你是怎样表现的呢?
朱良志:对,我一般抓突出事件,比如陈洪绶(老莲),他的生平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所抓的一点就是明代灭亡以后,他的朋友如祝渊、祁彪佳等都自杀,还有他的老师黄道周。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大量的诗反映生命处于极端状态中。
同时艺术镌刻下这些痕迹,他通过绘画来思考人的生命价值,他似乎将一切都放下,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在9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我就是抓住这个点,来观察老莲绘画所追求的高古之境,它包含了超越和还原两层含义,表现的是他当下的感觉,解决的是他人生的困境。
记者:喜龙仁说,中国艺术总是和哲学宗教联系在一起,没有哲学的了解根本无法了解中国艺术。具体而言,艺术和哲学的内在联系是怎样的?
朱良志:中国文人画可以说是智慧之画,是思考的结果,它不是简单的图像呈现,不是物的排列,也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通过简静而又明澈的笔墨形式表现出来,蕴涵很深。
文人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程式化。程式化就是语言的形成,“江岸待渡”表达什么,人们一看就知道,不同的人在画,有不同的意思,但主体的意思大家能够知道。倪瓒的“一河两岸”,明显是程式的东西。熟悉这个程式是进入这门艺术根本的东西。空灵、简洁、淡远、损之又损,都是这种程式化的要则。绘画要通过程式来交流,每个人运用这个程式都赋予它新的东西,就是以故为新,生生不已。
枯木寒林也是一种程式的语言,从五代北宋开始,绘画中枯木寒林屡现,这跟道禅哲学有密切关系:葱郁的世界不去画,为什么要画枯木寒林?萧瑟的天际中几棵枯木站在那里,你进入这个世界,理解这样的语言,会获得深层的交流。要了解这套语言,如果对传统哲学的智慧不大了解,就很难走进去。
比如说讲拙,不仅仅是用笔技法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世界的态度的问题。金农说“损之又损玉精神”,他画梅花,把损之又损的精神作为一种标识,他几乎是拒绝春天,他家里有个亭子叫耻春亭。人们都向往春天,为何他以春天为可耻?这里面蕴含的就是哲学问题,艺术家面对的也往往是哲学问题。黑白的水墨画本身就是个哲学问题,放着绚烂的世界不去画,用水墨来表现,知白守黑,就是个哲学问题。
记者:现在程式化还在中国画当中起着作用?
朱良志:当然,20世纪应该是中国绘画的黄金时期,出现了比如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等一大批画家,影响还是很大的。绘画领域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性,有的人把近现代绘画看得很低,其实五四运动之后,反传统的思想虽然造成对传统的否定,但也激发了思想的活跃度,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发掘。比如黄宾虹,他直达八大山人、董其昌,然后到黄公望,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中国画叫丹青,很重视色彩,后来水墨画出现,对色彩本身是排斥的,有的人认为是中国最有价值的东西失落了。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因为正是基于水墨的出现,打断了中国画色彩发展的内在秩序,逼迫色彩语言在另外一种形式上呈现,原来的浓墨重彩经过改制,在水墨和色彩的结合中间,探讨一种新的路径,这样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色彩呈现。你看李思训、李昭道的浓墨重彩绘画和黄公望的浅绛山水,你会觉得黄公望的作品更耐看。
“没心没肺”不是好画家
记者:书中提到,“中国文人画有普遍的担当意识,不是道统式的担当、道德式担当,而是生命的觉解。”我们该怎么去领会文人画“生命的觉解”?
朱良志:文人画主要是从道禅哲学生发出来的(当然也有儒学的影响),不仅仅是解决个人的困惑,而是要解决人类生命的困惑,是一个脆弱的生命体独临寒风的体验。艺术家将这种困境交代出来,然后怎么从困境中挣脱或者超越,这样的东西给人以启发。所以,金农讲文人画有强烈的先觉意识。先觉意识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一种将真实生命沉浸在其中的体验。
今天我们读他们的作品,在艺术品赏中,也可以得到鼓舞的力量,我们还在分享这些伟大灵魂的思考。比如八大山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在“污泥浊水”中,他仍然想有对清净精神的追求,对人与人之间没有苟且、没有虚与委蛇的状态的向往,对人的真实状态的呼唤,这是很伟大的。
记者:在目前的商业社会,有的艺术家很浮躁,你觉得艺术家应该怎样去建构他们的艺术世界?
朱良志:我写了《南画十六观》之后就觉得,中国的文人画至少告诉你,一个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告诉你浅近的、真实的、能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这样一种东西,脱去外在形式的桎梏,走向生命纵深。我们不能够一切都唯利益来考量,为了权势,为了做秀,为了煊赫自己,假模假样去继承传统,搞几个老子骑牛这样的东西,这种表象性的阐释远离中国文明核心,跟生命也没有关系。
艺术关键不在外在形式,而在于你真正的体会,找到适合表达自己的方式,笔墨精纯是基础,心灵体悟是根本,没有真实的生命感悟,八大山人画只鸟,你就画只鸟,你那永远是笼子里的一只鸡或者野鸟,跟八大山人没有关系。他那个东西是他独特体会出来的,所以仿作只是形式上的仿作,你必须要有自己真实的体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画家。
当然你不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不一定诗穷而后工,人在生活平顺中间,心灵也可以沉静下来,像弘一法师,家境那么好,像董其昌、沈周,也是非常有钱的,所以不在于家富还是穷,还是在于你自己对生命本身的体会,做个真性情的人。
我读沈周,有两点对我印象特别深,他那样一个有身份的人,一生没有出过苏州,他画的东西很亲切,多是自己的生活;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读了他的文集以后发现,他动不动就哭,看到一草一木,发现花要死了就哭起来,完全是个忧郁诗人,是被眼泪浸染的。
没心没肺的人没有这样一种真性情,整天油脑肥肠,大话连篇,没有真实的体会,然后搞几个东西吓唬人,就成了“大师”,那样不可能出来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