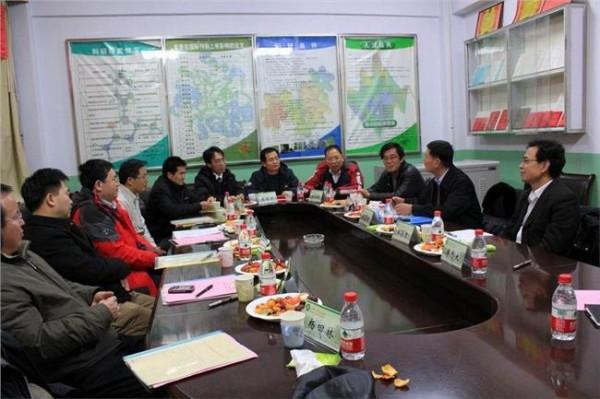劳东燕教授 劳东燕:法益衡量原理的教义学检讨
法益衡量说是结果无价值论用以说明违法阻却的实质根据的理论。它与结果无价值论的理论立场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随着结果无价值论在我国学界的强势崛起以及对实务的有力渗透,法益衡量说已获得广泛的影响力;它甚至开始超越结果无价值论的阵营,脱离作为根基的结果无价值论而受到追捧。
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务中,到处充斥着与法益衡量相关的话语。即使是结果无价值论阵营外的论者,也往往不自觉地运用法益衡量的原理,来解说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被害人同意等事由的正当化根据与其成立要件。
正是在法益衡量说的支配之下,诸多为通说所主张的见解,比如偶然防卫的行为构成犯罪,为拯救多人生命而不得已牺牲一人生命的行为仍属违法,经被害妇女同意的拐卖行为不能阻却犯罪等,正受到严重的质疑。依据法益衡量说的逻辑,前述行为都将由于存在优越的法益或者欠缺值得保护的法益,而得出阻却违法(或构成要件)的结论。
不可否认,有关前述行为的定性,立足于法益衡量的辩驳与论证看起来无懈可击,似乎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体系化理由;相反,通说的见解则在说理上粗糙单薄,简直处于不堪一击的境地。
围绕此类行为定性所产生的质疑,其症结在于,法益衡量说是否果真如支持者所设想的那样,足以承担起作为违法阻却的一般根据的重任?法益衡量说认为,在涉及利益冲突的场合,只需将冲突的法益纳入考量的范围,且其中的法益限定于涉案主体当下的现实法益,两相比较后便可对行为的违法性做出判断。
然而,试图通过如此狭隘的“利益衡量”,来一刀切地处理违法性判断的问题,其合理性未免让人生疑。
基于法益衡量说在当前的广泛影响,无论是从理论推进还是从实务需求考虑,对其展开全面的审视与反思均有其必要。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在前述行为的定性上,通说的见解在教义学层面存在充分的根据,真正有疑问的是将法益衡量说当作违法阻却的一般根据的做法。
本文的主旨不是要对结果无价值论展开批判。不过,鉴于法益衡量说与结果无价值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法益衡量说的教义学检讨,势必波及到结果无价值论,故客观上会起到批判的效果。尽管如此,本文关注的重心并非结果无价值论,也无意涉足于其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的立场之争。
通过检讨法益衡量说在实体层面所面临的疑问与其在方法论上所存在的缺陷,本文真正关心的是利益衡量在刑法中的适用问题。法益衡量说不过是对利益衡量理论的不当理解的产物。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方法,与刑法体系的实质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刑法理论日益实质化的今天,对利益衡量在刑法中的适用如何进行控制,以确保法的安定性价值,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
考虑到利益衡量与法益衡量之间的纠葛,而这种纠葛乃是源起于结果无价值论,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论述我国的结果无价值论如何将利益衡量与法益衡量相混同,并对其法益观展开必要的考察。第二部分从实体层面入手,探讨法益衡量说作为违法阻却的一般原理,在适用于具体的正当化事由(也称违法阻却事由)时,会面临怎样的教义学疑问。
第三部分意在揭示,法益衡量说背后的利益衡量观所存在的方法论缺陷。第四部分对作为方法的利益衡量在刑法中的适用进行定位,并试图提出一个体系性的框架来解决利益衡量的控制问题。
一、利益衡量与法益衡量的混同
耶林的目的论与利益概念,不仅在方法论上开启了由概念法学向利益法学的转折;[1]以李斯特的理论为主要媒介,刑法学的发展也深受其影响。[2]耶林第一个提出,法律是调和个人和群体目标、平衡个人和群体利益的社会机制。
[3]此后,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界定违法性阶层,逐渐成为德国刑法理论的常规做法。相应地,对违法性的典型理解便是,“在违法性层面,人们探讨的是相对抗的个体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需求之间产生冲突时,应该如何进行社会纠纷的处理。”[4]换言之,法适用层面对违法性的理解,要求以利益为思考基点,对法规范背后的各种冲突利益进行实质的比较与权衡。
所有的正当化事由都建立在利益衡量(Interessenabw?gung)与必需性的原理基础之上。[5]利益衡量理论表明的是这样的立场:在为维护更高价值的利益时,牺牲较低价值利益的行为是合法的。建立在利益衡量基础上的优越利益原理与利益欠缺原理,可谓正当化根据问题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说。
不同于一般的正当化事由,在同意的场合,既不涉及行为者与同意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涉及行为的必需性。同意的这种结构性差异,促使梅茨格(Mezger)发展出正当化事由的复合体系;据此,在多数情形中正当化是根据优越利益原理,而在同意的场合则遵循利益欠缺原理。
[6]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对优越利益的维护不允许与对较高位序的法益的保护相等同,因为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中,“利害的倾向”(die positiven und negativenVorzugstendenzen)并非单独由所涉法益的抽象价值所决定也取决于许多进一步的因素。
[7]换言之,与利益法学中的利益概念一样,[8]利益衡量中的利益被认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含在具体冲突情形中相互对立的所有价值,它并非由具体的法益来反映,而是由普遍的法原则来反映;因而,其衡量的对象范围超越冲突的法益,而应当包含“所有的利害倾向”,包括行为对于法秩序整体的意义,以及维护最高法价值与普遍的法原则的共同体利益。
[9]由利益衡量入手来构建正当化的一般原理,以及对利益概念进行宽泛界定的做法,尽管受到某些学者的批判,[10]但并没有影响利益衡量理论在德国的主流地位。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利益衡量具有妥当性,它也并非结果无价值论所独有。行为无价值论将违法性的评价重心放在行为之上,本身便可谓是对所牵涉的各种利益进行审慎考量之后做出的价值选择。不过,与行为无价值论偏重于行为本身对规范的违反相比,结果无价值论对结果意义上的法益侵害的高度关注,使得利益衡量之于结果无价值论而言,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且在实体层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
在违法性的判断中,具有实体意义的法益衡量(Güterabw?gung)的原理,被结果无价值论当作阻却违法的实质性根据。
利益衡量理论对行为效果的关注,恰好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基本逻辑相契合。它的以结果为核心与思考起点的逻辑,决定其在违法性本质的问题上,也必然要围绕结果而展开。由于违法性涉及的是不同利益之间形成冲突时的评价,对结果无价值论而言,即便行为侵害法益也不构成违法的原理,只能是“依据社会生活实态的利益衡量。
”[11]同时,由于犯罪的本质被认为是法益侵害,若要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按其逻辑便必须消除其法益侵害性。因而,建立在利益衡量基础之上的优越利益原理与利益欠缺原理,很快便被日本的结果无价值论奉为圭臬;同时,基于法益概念在其违法论中的核心地位,日本学者在解读这种复合论时,往往下意识地以法益概念来替代其中的利益概念。
可以说,对利益衡量与法益衡量不加区分,是日本结果无价值论的特点。[12]受其影响,我国刑法理论也普遍这样看待利益衡量与法益衡量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相关论者的论证中,所谓的利益完全等同于法益,相应地,利益衡量的概念被认为可直接由法益衡量概念所替代。
按张明楷教授的说法,在两种法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法益的衡量来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使违反了某种规则,但只要保护了更为优越或者同等的法益,就成为正当化事由。[13]简言之,从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出发,法益衡量原理构成违法阻却的实质根据。
一旦以法益衡量的概念取代利益衡量的原理,如何进行利益衡量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其一,既然此间的利益是指法益,则所谓的利益衡量,不过就是对不同的法益进行比较。其二,对此种法益必须做具体的界定,其指向的是涉案主体当下的现实的法益,而不包括与涉案主体无关的其他法益。与之相应,在违法性的判断中,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往往就转变为对法益本身的价值排序问题。
由于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念并不完全重合,人们会面临是按客观的一般人标准还是按法益主体的主观标准,来判断法益的价值排序的问题。一般人标准与法益主体标准,涉及的是社会整体的视角或法益主体的个人视角之间的分歧。比如,生命法益按一般人标准,会被认为在价值上高于人身自由的法益;不过,对于坚信“不自由,毋宁死”的自由斗士而言,自由的价值显然高于生命的价值。
同时,就具体的个人而言,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高估自身法益价值,而低估他人法益之重要性的倾向。这意味着,至少在某些场合,是依照客观的一般人标准,还是采取法益主体的主观标准,在法益的价值位序判断上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于拥护社会功利主义的结果无价值论而言,客观的一般人标准总是更受到青睐。它既简便可操作,又整齐划一,无需考虑个案的特殊情形,有助于确保法秩序的统一性。据此,在违法性判断中,原则上只要运用生命法益优于身体法益,身体法益优于财产法益的简单原理,便被认为足以完成对冲突利益的整个衡量过程。
换言之,依据法益衡量的原理,与民法中复杂的利益衡量不同,刑法中的利益衡量,只要单纯比较当事各方主体的法益的客观价值大小就足矣。
如果说民法中的利益衡量需要一套复杂的、综合的、法学家专属的技艺,那么,按法益衡量说的设想,在绝大多数的场合,刑法中的利益衡量犹如小学生都会做的算术。只要对冲突的两个法益的大小进行掂量,在一方法益高于另一方法益的场合,就应当说存在比该侵害法益更值得保护的利益,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被消除。
[14]西田甚至给出了更为简洁的公式:在保全法益(A)与侵害法益(B)之间存在B—A≥0的关系时,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就可将该行为整体予以正当化。[15]
然而,在违法性的判断中,将利益衡量化约为法益衡量的做法,会面临一些明显的疑问。其一,仅仅着眼于冲突法益的客观价值,根本不能说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更不可能对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其二,在冲突法益涉及同一法益主体的场合,单纯通过对法益的客观价值进行比较,也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
比如,在肾病患者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行为人为救助其性命而实施拘禁,强制在其身上连上透析设备做血液透析。对于此类行为,从法益客观价值的比较入手,势必得出行为阻却违法的结论,但法益衡量说的支持者往往也肯定行为的违法性。
其三,法益客体的客观价值并不等于法益本身,拋开主体的处分自由来界定法益的内容,势必使法益概念成为僵化的存在,容易得出荒谬的结论。比如,在A基于B的请托而损毁后者之财物的场合,倘若将法益理解为财物的客观价值本身,必然得出A侵害B的财产法益之结论。
有的结果无价值论者意识到了这些疑问,所以试图对前述法益观做出调整。其调整意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①违法性判断中的法益衡量,并非是以一般的、抽象的法益的价值序列为基准,而必须是根据相应法益的具体的保护价值来进行衡量。
[16]②在同一法益主体内部的“法益冲突”的场合,不能依照客观上的保护价值而进行“法益的衡量”的判断;既然属于法益主体内部的问题,且由于价值的内部序列只能根据法益主体的意思才能决定,故法益衡量的判断必须遵照法益主体的意思的基准而进行。
[17]③关于法益处分的“个人的自由”,并非是与法益不同的东西,而是法益本身的构成要素。[18]简言之,相关的修正主要包括:一是以法益保护价值的比较来取代法益本身的比较;二是对同一法益主体内容的法益冲突,采取法益主体标准;三是将对法益的处分自由解读为法益概念内在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