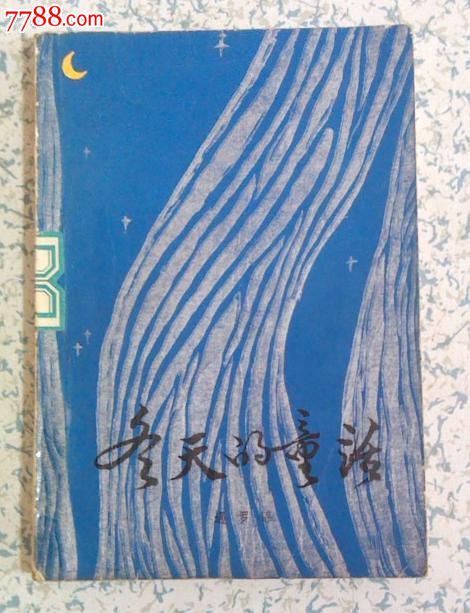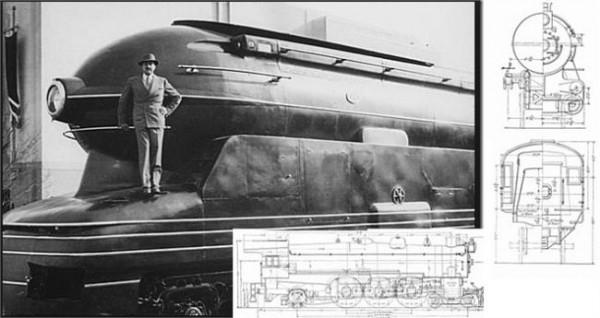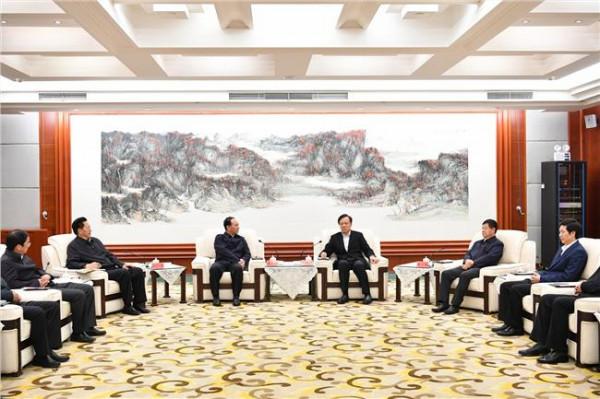遇罗克遇罗锦 遇罗锦:我的哥哥遇罗克是如何被杀害的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轻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啊!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咏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了。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急需的时候能把它设法交给毛。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迸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牟志京,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
罚不当罪的绝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
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那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绝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这儿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
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若,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呆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悄悄的、溢着桔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十二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谁也不知道,他在本子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公安狠狠地用电棒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他们毒打他,要先让他尝尝厉害、要先让他恐惧、屈服;他们毒打他,用电棒将他打得昏晕过去。
同一个早上,郝治也被“轻工业学院”的联动分子们毒打,然后关进该院地下室,他们天天毒打他,三个月,郝治硬是闭气不吭,最后以绝食抗议。这个早上,罗文也被学校的联动分子毒打,被打得晕死过去。同一个时刻,母亲又一次被关入工厂的地牢。
孙刚,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岁的青年,从东北省坐火车来北京,一心只想见见哥哥,表示仰慕。次日哥哥被捕,警察来抄家时将他抓走,仅因这一面,他被判刑十五年。
被捕的那天,在小屋的桌上还放着哥哥未定稿的《工资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预审)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问:你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问: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答: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问: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监视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学了。元旦社论我学了,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问:你没有问题吗?
答:我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答:我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
问:你最好把背后写的那些东西亮出来。
答: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问:你不用讲好听的……
答:我的日记被《红旗》杂志拿去了,你们可以看。我的日记中是表达我对“人民”的热爱的……
问:……不管你多狡猾,群众也会把你揪出来。
答:……我请求你们让我给毛主席写封信,毛主席知道《出身论》是我写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毛主席绝不会说我够专政条件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问:你的日记为什么烧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问: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烧呢?
答: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就烧了。
问: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答: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问:这个日记下落哪儿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给我妹妹了。
问:你把情况谈谈。
答:这本日记记的都是我们厂子的真实情况。
问: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答: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问: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问: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答: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问: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答:应当“尊重。”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答:没有。
问:你这个人思想一贯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日记中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答: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地方?
答:没有。
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答:我这本日记由头看到尾,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祖国和人民了。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反动内容?
答:无论如何我对祖国和人民是热爱的,尽管我思想上还是有错误的。
问:你七月三日记,把学习毛选当作为残酷野蛮,这反动不反动?
答:这我有辩护的余地,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问:……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
答:我指厂里拿学习毛选来压制运动。
一月十日
追查“反革命小集团”时,预审员问到两个人时。
答: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问: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问:这已经定论……你不交代,是你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份子。
答: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可以保证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没有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一月十二日
问:几千封读者来信的地址,你为什么抄在本子上?
答:我也不知为什么。
问:你放肆!你不交代,还想不想活?!你是要搞党派!这是铁的证据!
答:我从来没想过搞党派,你们没有事实。
问:我们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对我们的仇恨很深。
答:没有。
一月十三日。
问: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含走得更远。
答: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写彭德怀翻案。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我没有事实。
问: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怎么没有事实?
答: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问:……你的问题不交代,也跑不了,……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顽抗到底。
问:那你这算什么?
答:我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也没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我真有这样的事,你们可以最严厉的处罚我。
问:将来我们把大量事实摆出来你怎么办?
答:那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问:你现在这样顽固,到了时候有你后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处理你。你听见没有?你讲不讲?
答:(拒绝回答)
问: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们再警告你,抗拒,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在人民法庭你继续放毒……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
一月十六日
问:你考虑了吗?
答:……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级我九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
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
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
(关于劳模)时傅祥他是掏粪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报纸上常有他的报导和他的文章,文化革命时听说他组织捍卫团保刘少奇。江青说他是工贼,于是天天挨斗。掏粪工人出身当然清苦,可是一挨斗,祖宗也要变,现在说他出身是粪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们工厂里游斗,我见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两旁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小伙子,卡车绕场一周,大家都跑出来看,他是个胖胖的五十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副听其自然的态度,并不显得怎样不安。
关于时傅祥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握手,大概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画了一幅“同志”这样的画,座中两人,左边是刘,右边是时,上角题词摹拟刘的语云:“你是掏粪工人,我是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
”文化大革命时,李琦便成了“黑帮”。虽然他也画过毛主席,那幅画还是我所见过的他肖像画中最有风格最好的一幅,但也无济于事。
建筑业的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张百发。几次出国,被当作专家聘请。他原是普通工人,组织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是砌砖能手、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共产党员,三天两头做报告。现在参加过人大会堂劳动的人,大都还记得,张百发怎样教他们捆钢筋,据说的确有两手……以后张百发被宣布为工贼,原来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问:你讲了半天,并没有讲到点子上!你不要跟我们兜圈子!……只许你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