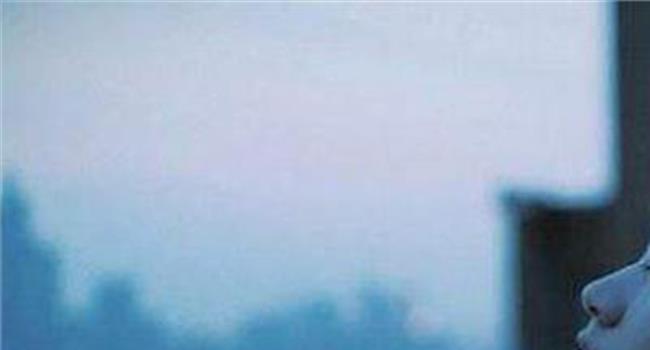萧功秦主义大爆炸 萧功秦:“主义”大爆炸的时代里中国何去何从?
二十世纪是不平凡的一百年,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如何看待这一百年的思想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百年中国的思想界是不是有一条贯穿的线索?
这个问题确实促使每一个关注中国百年命运的思想史学者深思。就中国而言,二十世纪相对于春秋战国以来的任何时代而言,都可以说是一个思想最为丰富的时代,是一个“主义”大爆炸的时代。二十世纪与春秋战国时代相比,至少有三点相似,首先,是丰富的问题资源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困境与矛盾,从而为思想者为解决这些矛盾与困境进行着思想上艰难求索。
其次,此前旧时代的原有的思想传统又无法为解释与解决这种困境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探求新的方式进行反思。第三,两个时代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与内容资源。
思想的本质则是对解决问题提供的建议与意见。因此,当一个时代与社会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前人的思想与概念又无法为人们解决自己面临的生存危机与问题得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法与选择时,当已经发生的历史经验事实又进而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得以解释的例证时,思想家就会应运而生。
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由于历史中的种种内因外缘,中国同时存在着三个最基本的困境,把握了这三大困境,研究思想史就有了凭依。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第一个困境,就是专制对个人权利的压抑,这就促成人们对个性自由与解放的追求。
第二个困境是贫富两极分化与上层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腐败,这就导致人们对公平理想的追求。第三个困境是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传统价值的解体所导致的脱序与失范危机。于是人们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与珍视也就应运而生。
正是由于本世纪的中国人不断面对上述的专制压迫、两极分化与社会失序这三大困境,中国人中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思想主张与选择。这众多的思想与主义的“大爆炸”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大思想流派或思想系统,它们是:针对专制压抑个人这一矛盾而激发起来的自由主义;其次是以国家权威来实行社会分配与干预经济的左翼的平等主义;第三是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防止社会文化失序的新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左翼平均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新保守主义以秩序为核心价值,这三大思潮彼此之间相互对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响曲。我们概括地说,本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正是持续地受这三种思潮的吸引,并以它们为主轴,形成自己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运动的,而这些政治运动与政治选择,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对于寻求解决中国问题之道的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以这三大主义之间的互动、竞争与此起彼伏,来作为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运动与思想运动的主线。
作为世纪末的我们这一代,确实要比以往几代人更有资格对这百年的思想演变作出这样的概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几代人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坐在世纪思想列车的最后一排。我们对思想列车前面就坐的乘客的活动看得更清楚。
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左翼平等主义的社会生命力
为了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三大困境,为什么是由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左翼平等主义这三大主义,来各自提出对应之道。为什么正是这三大主义流派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持续的吸引力?
这三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最大,其原因要从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的三大困境来认识。首先让我们看看自由主义。当我们这个民族意识到专制政治的压迫而形成的困境时,首先对这种专制政治进行批判与挑战的是自由主义,早期的严复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最早代表者。
正因为中国的专制政权对个体的压抑,使国民失去主动力与自主性才导致中国应付西方挑战的失败,从而引发了严复在《原强》、《论世变之亟》、《辟韩》中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积极肯定。
中国自由主义从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体,对民间社会的自主性的提扬中,获得了批判专制集权政治的立足点。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自由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以集体的名义对个人的压抑所产生的反向运动,是对专制政治的批判判运动。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与西方本土的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没有布尔乔亚阶级的阶级背景。中国自由主义在描绘中国的兰图时,恰恰是没有西方自由主义的阶级与物质基础。这就使中国的自由派往往免不了有些“无根”与苍白。
中国早期自由主义很难进入操作实践。尽管如此,只要存在着以家族的、宗法的国家的或者集权主义的名义来压抑个体的主动性与自主性的情况,那么,这种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就一定会借助于西方自由主义提供的理论概念而再次出现,并以西方来源的价值坐标,成为中国人反抗专制主义的立足点。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在对专制压迫特别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知识分子本性上更追求思想上的自由空间。他们最敏感地意识到专制或“集体”的强大禁锢对人性的摧残。然而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Middleclass)本身就十分弱小,没有多少活动的空间。
作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也同样使中国反专制式的自由主义难以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难以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中具有影响力。
许多政治家之所以不受自由主义的吸引,在于他们认为自由主义“陈义甚高”,然而却“无补于实际。”当然,我这么说决不是否认中国反专制的自由主义所具有的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在一个“集体”不断淹没个体的自主性的社会中,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在传统专制体制内部找不到批判这种体制的参照点,从外部世界找到一个批判的参照点,无疑是必要的合理的。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新保守主义。百年中国面临的第二大困境是现代化的断裂所形成的失范、脱序与整合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失范型危机,就会有人主张从传统文化中,从权威的秩序中,寻找出某种杠杆或支点,通过这种杠杆或支点,来重新整合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并在这种秩序得以存在的条件下,渐进地推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本质,就是从传统文化与权威形态中,寻找国家与民族凝聚的新的资源与整合的基础,以此来避免社会出现“新者未立,旧者已亡”的社会脱序与政治危机。
总的说来,这种新保守主义是在克服文化与政治断层的意义上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与政治权威的功能作用的,其次,其基本价值走向是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的。而不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这就是它与传统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义相比的新意所在。
更具体地看,新保守主义内部分为在文化与政治上,存在着两种类型,即从文化上说,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则在一种开明专制主义或开明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后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股相当有影响力的思潮。
它主要强调的是通过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来防止文化断裂与文化失范。新儒家可以作为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至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在清末新政时期主要是梁启超、杨度等人提倡的开明专制的权威主义,在民国初年则表现为提倡强人政治的强人权威主义。
民国初年的严复本人可以算是这种新思潮的典型代表。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力求利用传统的或现存的权威体制对受治者的权威整合力与镇制力,来重建政治秩序,达到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因为只有在这种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新的经济生长机制才有可能得以成长发育。
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对激进政治的反动而出现的,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变革的现代化思潮。严复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最集中地体现了新保守主义(包括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的价值内核。
第三种思想力量是左翼平等主义。其中包括中国的平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九十年代崛起的中国的新左派思潮,这种平等主义的产生也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原生态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恶性膨胀而形成的反向运动。资本主义所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使一种运用国家的力量调节社会生产,并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的,以实现人人经济上平等的公正社会的理想得以产生。
而自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没有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工业化大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集中与两极分化,但却有着旧秩序瓦解而出现的失范性的两极分化,自民国军阀混战以来,这种失范性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远比马克思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欧洲更严重得多,因而广大下层民众对腐败了的经济精英的反抗,以及传统的“吃大户”的政治诉求也强烈得多。
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平等主义的价值诉求,与西方起源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最为切合。正因为如此,左翼平等主义在中国就具有了其社会生长条件。中国最初的左翼平等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
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工业化的大生产导致的市场竞争的两极化,那种原生态的、以反资本主义为宗旨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并不具有生长的文化与经济生态条件。中国的左翼平等主义乃是一种以国家为实现经济平等价值的载体的平均主义。它的出现自然需要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作为基础。
这一条件到了二十年代开始出现,那就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至上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认为,当民族面对生存危机时,在一盘散沙状态上来鼓吹个体反抗集权,无疑是南辕北辙,在民族大敌当前时,只有整个民族聚合为一个整体,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才能以集体的力量抗衡列强的侵凌。
换言之,由西方列强的压迫形成的险恶生存环境,激活了的,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个性至上主义,而是以国家以本位的,以集体为本位的“社会板块化”的、凝固为团队式的组织化的冲动。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民族主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的集体主义与均贫富的社会主义思潮得到了结合点。原先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俄模式的左翼平等主义被中国人视为范式以后,这种主义中最具特色的东西是,它认定公有经济的建立,无须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充分发展为条件。这种平等主义被视为一种可以超越经济条件限制的良好的、放之四海皆可行的制度结构。
这种思想一旦被中国人接受,它就会成为“穷过渡”理论的出发点。这一理论“基因”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产质性影响。但这一基因却存在下来。建国以后的穷过渡实施时期,走向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只要存在着贫富两极化与失利民众对腐败化的经济精英的反抗,就会产生这种左翼平均主义的土壤。
至于是否会出现平均社会主义的再次生形态,即国家主义的穷过渡社会主义,则要取决于另外一些条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广大农民为主体的、存在着精英腐化的极大可能的社会环境,再次生态平均社会主义出现是不难理解的。
三大思潮在二十世纪中此起彼伏的原因
为什么这三种思潮在近百年中总是不断出现,并相互冲突?难道人们争论了近百年的问题还不能解决?人类的智能居然如此无能?
从逻辑上看,既然存在着这三种思潮,就应该有一种是最合理的最正确的思潮。而事实上,历史不同于初等数学,它太复杂,充满了太多的矛盾乃至悖论,以致于并没有唯一的解。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来分析问题,这三种思潮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都有其不得不己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说,各种相互对峙的思想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与合理性,这与二十世纪中国生存环境中存在的许多矛盾与两难性的悖论有关。下面,让我们对这三大思潮分别进行分析。
中国的自由主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民主主义思潮对旧体制的专制独裁的批判是有相当的力度,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指出的,这种无经济与市场之根的自由主义却无法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社会载体。西化的民主虽然有其示范与启示作用,但对于市民社会还没有出现的中国,并不是合适的药方。
在广大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土地上,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以自由主义的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化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失败,决不是单是袁世凯这个“坏人”破坏的结果,其实,在袁世凯集权以前,这种议会制由于先天不足已经陷入多次内阁危机,连正常政务都无法推行下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严复、章太炎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都会由于对议会制的失望而认定,当时中国需要的不是华盛顿与卢梭,而是克伦威尔与张居正的原因。
中国自由主义在批判专制独裁有其独特贡献,但作为施政方法则使这个缺乏自由主义的基础条件的社会无所措手足。西化的自由主义与议会民主主义的不切实际,反过来则会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引起新保守主义的与左翼平均主义的反击。
一方面,新保守主义至少从传统中转化过程的新型权威中找到维系政治整合的载体,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政治操作性,因而在批判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方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一个两极分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的社会,某些自由主义者为保护个人自由而引用英美自由主义的经典理论,来为私有财产神圣性辩护,则无意中成为两极分化中的得利的有产阶级的义务律师,于是授左翼激进派以把柄。
左派攻击他们是“为虎作伥”。
其次,让我们分析一下新保守主义的生命力。新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比其他主义更能提出一种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稳定秩序的杠杆,而运用这种权威作为杠杆来实现经济发展与引入外国资本,并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民主所需要的利益分化与契约性的交换原则的生根,无疑是现实可行的。
许多后发展国家,从日本到后来的东亚国家,均以不同的形式的新保守主义来实现了本国的现代化转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以秩序为本位的思想,以稳定为核心价值的观念,可以降低现代化整合所需要的政治成本,对于民族的生存、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均具有重要贡献。
然而,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却找不到解决权力的监督与防止权力的腐败的办法。一个受新保守主义保护的政治强人却有可能在新保守主义提供的权威正当性的庇护下,侵占公共利益并实行个人独裁。形成新的专制政治。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也很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两极分化的问题。
这是因为,权威政治下,权钱交易形成的排它性的利益集团会比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更快的恶性膨胀。这是新保守主义固有的两大困境。这就同样会引起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自由主义攻击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强人走向独裁专制因而失去合法性。左翼社会主义则攻击权威体制下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公正。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第三种思潮,即左翼平等主义。左翼平等主义对社会公正与平等的追求,体现了人类的理想,它在抵抗自由主义对下层民众切身利益的忽视方面,在反对权威主义造成的精英腐败方面,具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
然而,左翼平等的政治诉求却无法以抗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理想本身的不切实际的诱惑。这种主义面临的两难矛盾在于,一方面,为了实际平均的资源分配,平均主义必须以国家为依托,以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它所要求的公平而平均的分配,然而,另一方面,国家的公职人员或国家官僚在掌握权力在手以后,则可以利用公共的名义来化公为私,并可能从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其结果又会走向反面。成为一种新的在公共名义下的个人专制,导致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与社会不公正。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引起自由主义把异化了畸变了的平均主义当作文化专制主义来批判,同时,也同样引起了新权威主义通过确立新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来挑战平均主义的左派。
由此可见,贯穿二十世纪的三大思潮冲突,具有极为丰富的现实内涵。三大思潮面对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范(脱序)危机、专制权力的腐败与对人性的压抑,以及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化、社会不公与不平等,必然引发了知识分子与思想者们从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从不同的价值关怀的角度来加以批判,并各自提出相应的解决矛盾与困境的办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当一种思潮主张成为主流的政治选择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而走向畸变,引发另外两种思想选择作为对主流思潮的批判运动而再次崛起。并主导了下一轮的政治选择,如此互动形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大变动与思想大变动的丰富内容。
这些思潮各自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在当下中国继续以各种新的形式存在。三大思潮的对峙不便没有消逝,而且继续给予当代中国人以深入思考与启示。它们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思想活力。
三大思潮互动的历史启示
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历史对当下中国人有什么启示?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思想史会给予人们什么新的智慧与历史经验?
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存在着传统专制主义与权威主义以集体的名义对个体的压抑与摧残,并使个体丧失了自主性,从而也使国家整体的活力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就会作为对异化了的专制政治与权威主义的反叛者与批判者而出现,自由主义者力求维护个人权力与保护个体利益,来达到民族复兴。
这种自由主义也会有不同的变种,它的一种形态是退出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放弃个体对集体的承诺。也有的是完全的食洋不化的激进西化派,完全不顾中国的条件,纯粹以西方的价值尺度批判现实,以为如此就可以解决中国复杂的问题。
只要存在着脱序与经济上的强大的分化所引起的贫富不均与民众对精英主义的逆反心理与反抗心理,左派的激进的平均主义,就会有其思想市场。这种主义主张可以通过民众主义的方式,来对财产进行社会再分配。至于这种平均主义者是主张用国家组织化的方式,还是用过渡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分配,则取决于各种条件。
只要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脱序,那么,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或政治资源来寻找新的聚合力,以实现文化秩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并力求以这一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导向的发展目标的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保守主义者。
这些思想选择由于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各持一端。并彼此对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可以说,是为三种思潮彼此对立、冲突、消长与替代的历史。
研究这一思潮互动的过程,理解特定思潮与社会中特定困境的对应关系,(例如,专制困境与自由主义,无序困境与新保守主义,失范条件下的社会不公与左翼平均主义的对应关系。)特定思潮与主义走向畸化的后果如何引发另一种相反的思潮崛起,并走向主流,(例如,自由主义造成无序,导致新保守主义崛起,新保守主义的权力个人化与官僚腐败化,导致左翼激进主义的崛起,左翼平均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导致自由主义的发难。
等等。)我们就可以把握历史变动的基本趋势,这是因为思想史政治史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以致于我们只有把政治史放在思想史提供的框图内,才能对其发展演变过程予以清晰的理解。
作者附记:
在本文里,我只是从价值中立的角度来分析各种思潮产生的不得不然,无宁说我是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分析三大思潮的崛起是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的。这种同情的理解对于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现代思想史是绝对必要的。当我在分析其中每一种思潮或主义都具有其两面性,都有其走向蜕变的可能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自己的价值倾向性。
在三大主义中,我个人较倾向于新保守主义。三害相权取其轻,新保守主义虽然可能导致权力个人化的历史祸害,例如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可能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第一波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相对而言,新保守主义的畸变较为易于纠正,而自由主义造成的失范危机与无序化,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造成的乌托邦工程的历史后果则远为严重。
我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批判研究,以及我对新保守主义的基本肯定,可以参阅拙作《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我对左翼激进主义的的批判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