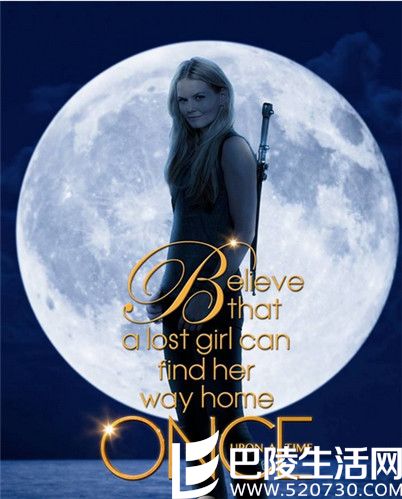伯格曼采访 卫报采访众人怀念伯格曼
没有人像他那样拍电影 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於昨天逝世。他的作品曾给几代电影爱好者以灵感和震撼。这里是几位敬慕者对伯格曼的解读。 摘自2007年7月31日 《卫报》 里克穆迪(Rick Moody)小说家 作为一个艺术家,伯格曼的创作不仅基于电影的制作传统,还基于欧洲艺术与哲学的伟大传承。
像易卜生、契诃夫、托马斯曼和尼采都影响过他。他立足于欧洲三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电影史上无人具备这样做的气质。
他无所畏惧地按照他的需要来探讨人生的基本问题,前无古人,后鲜来者。这就是他,我印象中的伯格曼,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把他与欧洲的传统导演如戈达尔、特吕弗和费里尼相提并论。
但后来我们检讨发现,他是独特而固执的。他的作品是如此的阴冷。他只制作过一部好莱坞电影(1971年的 Beröringen,即《触觉》,由Elliott Gould, Bibi Andersson, Sheila Reid和Max von Sydow主演)。
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他把它处理成了喜剧,似乎他并不具备发笑的神经。 我从未因写作成名而快乐,伯格曼的电影似乎很合我的口味。我喜欢他电影中的阴暗,那种对仇怨与愤恨的精妙表演。
有一个Liv Ullmann和Erland Josephson演的电影《结婚》的电视版场景,他们彼此厮打,向对方尖叫,持续了近六个小时。(1974年的影院版是167分钟长,瑞典电视台的DVD版本是299分钟长)。
我看得目不转睛,太迷人了。 当我想到电影工作时是我第一次体验伯格曼,在布朗大学。我在课上看了很多好电影比如戈达尔的,还有《第七封印》。伯格曼的作品能立刻吸引我。
很能说伯格曼在我写作上影响的程度,但他在他的电影中所显示的那种对于上帝、灵魂和疏离等等重大事件的探求的渴望,为我点亮了一条道路。他并不担心在电影里讨论这些问题,尽管他冒着被称为自命不凡的风险。
那种顽强,那种胆量,是前所未有的。 我依旧很喜欢他的电影《范妮和亚历山大》,不像他的其他电影《叫喊》和《窃窃私语》那般阴冷。它(《范》)集合了严格的现实主义——这要感谢Sven Nykvist的摄影和服装师——与民间叙述中对梦境与幻想的提示,所有都是为了展示一个小男孩如何长大。
那是近乎魔术的现实主义,类似于托马斯曼,Heinrich von Kleist,弗兰茨卡夫卡,Bruno Schulz和August Strindberg。
伯格曼在当今无人能及。西科塞斯有着某种连贯性的风格,所以即使《纽约黑帮》并不完美,但它仍旧是西科塞斯艺术全貌的一部分。伯格曼也如此:即使他的作品时期更早,数量更少,但依旧是真正的艺术丰碑的一部分。
其他导演像特吕弗、塔科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尽管他们的作品都曾涉及重大的严肃主题,但无人像伯格曼的探索般始终如一。 比班 基德隆(Beeban Kidron)电影导演 我是他的铁杆影迷。
我向别人借了《野草莓》想今天看一整夜,以从中唤醒属于我的发现。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能唤起时间与死亡,你年轻时光阴飞逝,你年老时度日如年。它(《野草莓》)言有尽而意无穷。
他建构隐喻。对话中隐喻并不多,有足够的空间留给观众去反思和想像。我最近在长途火车上又看了《范妮和亚历山大》,伯格曼真的是一位大师。特别的是,他酷爱电影却以戏剧为职业。听到他逝世我很伤心,尽管他可能早有准备,因为他拍摄了那么多的关乎死亡的电影。
托马斯 冯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电影导演 我在三年前看了《范尼与亚历山大》。我认为那是史上最好的电影。我把这部电影介绍给比我年纪小很多的人看,她看得泪流满面,她说那是她看过的最好的电影。
她才19岁,我还担心这部电影对于她来说是否节奏太慢,是否老掉牙,但显然,我多虑了。 多年以前我和伯格曼交谈过。他情绪很好,是个很开心的人。他吊儿郎当,嬉皮笑脸,玩世不恭。
他给了我很多不错的建议,像如何把握成功和失败。每个字我都记得。他问我是否决定了拍电影之后干什么,当我回答不知道时,他说:“你真傻。”我问为什么,他说:“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你失败了,虽然这会让你自信心受损。
但成功就更糟了——你会被搞瘫痪的。所以在每个电影开始拍摄之前你最好先决定下个电影的事情。”他是对的。你永远都不要变成一个事业的领航员,不要被成功和失败所左右,只卜问于你的内心。
吸引我这个电影导演的是,在我无法决定是拍摄丹麦电影还是拍摄英语电影时,伯格曼坚持他自己的东西——他在瑞典用瑞典语拍片,用瑞典演员。并不像某些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伯格曼留下了并为国家作出了很值得让人骄傲的贡献。
当然,世界很大,伦敦和纽约很遥远。我想只有在斯堪地那维亚伯格曼才有他最伟大的创作灵感,就像在电影中一样。 《范妮与亚历山大》是对我情感影响最大的影片。我在电影学院时看了他早期的8、9部片子,感到很烦,因为那时很躁动,因为年轻。
同时我觉得他也在成长。然后,当我离开电影学院几年之后看到《范妮与亚历山大》时,我就爱上了那部片子。我的电影《Festen》的主要灵感就来自《范妮与亚历山大》。我对伯格曼很崇拜,甚至抄袭了他的一个场景,他笑了。
之后不知是他还是别人告诉我他那个场景抄袭自《豹》,那个他们围着房子跳舞的场景。丹麦和瑞典的传统文化是相通的,所以真的就像是抄袭了一个传统。但是,那依旧是一种抢夺。
我喜欢《范妮和亚历山大》的地方是我后来认识了整个一个家庭,就像他们真的存在一样。那些人让我永生不忘。我经常回忆起他们,常常想起怪叔叔放屁。那是真实生活的一瞥,也正是我所推崇的。 Hari Kunzru小说家 某个午后,老师拿出两个版本的研究来向我们展示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我看到Max von Sydow在海边同死者玩象棋(这是电影中最重金属风格的画面),随后我意识到我想看这个导演的所有作品。
尽管至今我还没看全,但是伯格曼却能够在我生命中某些关键的时刻闪现,给我以启示。电影《结婚》中那个露台上的沉闷的场景让我反思我与我身边的女人之间的一切。在《狼人时刻》(瑞典文片名则更短小精悍,即Vargtimmen)中扮演那个痛苦的艺术家的演员Von Sydow曾经说:“一瞬间也如同永恒——从现在始。
”我从中领悟到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场景时间虽短,却是观众与剧中角色分享体验的时刻。伯格曼是伟大的,因为他是如此的精准,没有偏差。
迈克尔 维那 (Michael Winner)电影导演 在剑桥的日子里,我几乎是整天看着伯格曼度过的。他的电影是如此的精于思考,长于创新,对我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不仅是一个电影天才,他特立独行。没有人像伯格曼一样拍电影,他是唯一的。他电影中那种深刻的思考和奇幻的视觉风格,极有魅力。 我还记得我曾在剑桥郊区一个不大的影院里看伯格曼的《夏夜微笑》。影院老板说没有会来看了。
可事实上人们蜂拥而至,因为影片中有15秒长的裸体女人在海滩奔跑的镜头。在那时候(1955年),这是革命性的。排队看电影,这是那些人对伯格曼的唯一记忆。 我最喜欢他的《第七封印》,有着绝妙的哥特式象征符号。
它不是对我影响最深的电影,却使我永生难忘。 在今天你再也找不到伯格曼那样的人了。今天我们只能见到那些机械化的、特效炫目的电影,艺术电影却难觅芳踪。 希拉 雷德Sheila Reid 演员 我曾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伯格曼的《Hedda Gabler》中扮演Elvsted夫人。
之后他的助手和我说伯格曼希望我能出演他的电影。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高兴得发抖,无论如何我都愿意与他再度合作。
我想我是伯格曼电影中唯一的英国人。起初,我在他的首部英语电影《接触》(the touch)中饰演一个小角色,剧中集合了Bibi Andersson,Max von Sydow和Elliott Gould这样的演员。
奇怪的是个子很小、皮肤白皙、来自苏格兰的我却饰演了剧中艾略特的妹妹:一个个子很高、皮肤黯淡的犹太人。 有个镜头是安德森来拜访我。我喝醉了,动作失控。伯格曼问我:“英国人要搬家的时候房间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会放着我没来得及搬走的瓶子、椅子和窗帘。
”他说:“很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如果有人按响门铃呢,你会说什么?”我说:“请进,很抱歉没咖啡招待了。”我们就这样计划着拍摄内容。 我有一张他喊“开拍”前的照片。
他扶着我的肩膀,目光炯炯。你会感觉到他是在将他的力量传输到我的体内,我在接收。六个月前我还在晚餐时见到他。我问他是否愿意再谈谈我饰演的角色,他说:“不了,你已经很了解她了。”的确,那个角色他几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在听讲时他也在观察我。
连我的不快他也会注意到。 从调度那些少不经事的男孩子到目不转睛地盯着拍摄镜头,电影中的工作是极不寻常的。影片的调度也常常需要充沛的体力。在导演《Hedda Gabler》时的伯格曼也是如此。
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我们只在午饭时休息20分钟,饭后便要全神贯注。他给了我很有帮助的提示,并说“她是不灭的蜡烛(状态一直很好)”和“她脖子以上那里有个小屏幕”那样的话。我很荣幸我不但在剧院而且在电影片场都能与他一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