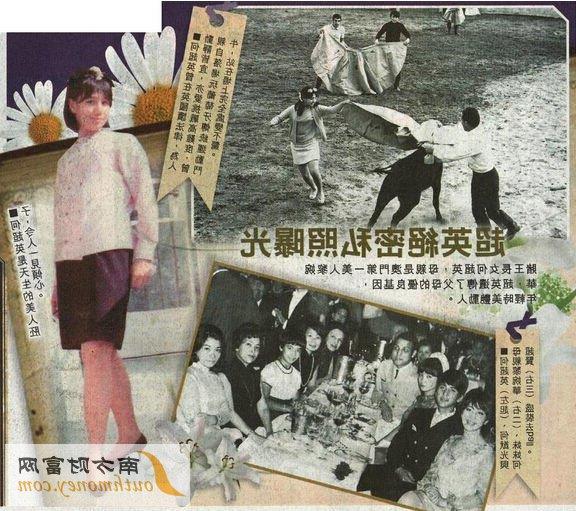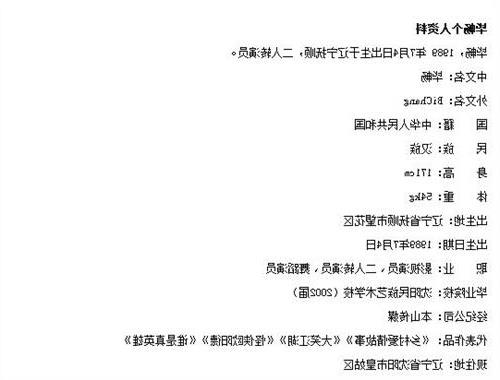【金龟子老公王宁去世了吗?】金龟子老公王宁去世了吗?
核心内容:金龟子老公王宁去世了吗?最近因为王宁有几期新闻联播没有出现,因此很多人都说王宁去世了,其实这些都是谣言,王宁没有在主持主要是为了给新人机会,众多网友以为王宁逝世,其实是和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宁同名,所以才造成误会而已。
王宁,1964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1983年进入青岛电视台实习。1986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调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一直主播《新闻联播》至今。曾代班《新闻30分》、《晚间新闻》、《整点新闻》等央视新闻节目,并多次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报道。
王宁和刘纯燕虽然已经结婚多年了,但是两个人生活十分的幸福,刘纯燕经常会在微博中晒出两个人幸福的合影,王宁是央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由于每天的央视新闻联播中都能和王宁见面,因此王宁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都十分的高,同时王宁也是金龟子的丈夫。
王宁作为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已经在新闻联播中奋斗了二十多年,现在王宁已经开始有退居幕后的想法了,而关于王宁的老婆是谁?其实王宁的老婆同样是央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金龟子刘纯燕。王宁和刘纯燕两个人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当时两个人都是班级里面成绩的佼佼者,因此还没毕业就已经在恋爱了。
毕业后一直主播《新闻联播》至今。曾代班《新闻30分》、《晚间新闻》、《整点新闻》等央视新闻节目,并多次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报道。主持风格端庄、大方、得体,语言规范,吐字清晰、播音自然流畅。“金龟子”刘纯燕丈夫。
王宁是山东青岛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庞,轮廓分明的五官,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的性格沉稳,生活中很少见到他喜形于色或者挑剔什么。用一句歌词形容他很恰当,那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在大多数人眼里,王宁和我“反差”太大了: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好静,一个好动;一个说话惜字如金,一个话篓子。可是,正是有了这样的反差,生活中我们才有如此和谐的互补。
“王科长”与“小不点儿”“王科长”这个绰号是王宁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送他的。因为那时的王宁总是正儿八经的,一身中山装,不苟言笑,烫着个卷花儿头(自己用电夹子鼓捣的那种)、还总拿着个公文包。“小不点儿”是我同学冲我这身材,这长相,送给我的绰号。
我和王宁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同班同学。王宁是先在青岛电视台工作,之后才考入中传的。当年他们青岛市招播音员,一心想当歌唱演员的王宁幸运地在1000多人中被选上了,名副其实的千里挑一。我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本可以保送上北师大的,因为小时候有在少年电视演出队的经历,就选择了报考中国传媒大学。
开学了,来自全国电台、电视台的青年骨干组成了一个集体。我是班里唯一的“北京妞儿”,因当年配音有点儿名气,老师比较照顾我,而大两届的同学也很喜欢我,都把我当成小妹妹似的。我的性格很豪爽,喜欢踢足球,当时还是我们播音系女子足球队的“优秀女运动员”,人称“金左脚”。我和班上的男生一起玩扑克儿、跳“怕死”(当年的水兵舞)、踢球、去香山游玩……相处得挺融洽,跟哥们儿似的。
“美味儿”的爱情:我当“月下老人”
别看当年我人小,还挺爱张罗事儿的。王宁虽然平时话不多,但在班里还是挺出色的,有位女同学一不留神掉进了感情的旋涡,想必也是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连课也不上了。我知道后,虽然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但看到同学备受感情煎熬,我还是自告奋勇地充当起了“月下老人”。
一天晚自习后,我就把王宁给约了出来。我们在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交界的地方见面了。因为我性格开朗,所以和班上的男同学关系都不错,王宁看我约他,兴致很高,我们一路走,一路聊,我差点儿把来干什么都给忘了。王宁问:“咱们这是去哪儿呀?”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使命来。话到嘴边儿,竟不知如何开口,我有点儿心虚,说话也支吾起来。
王宁见我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更奇怪了,就使劲儿刨根问底,我只好如实说:“班上有位女同学喜欢你……”话没说完,看到王宁突然露出“王科长的样子”(很严肃),我就打住了。他站在原地半天没说话,一阵窒息一样的沉默,我的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半天,他才说:“对不起,我在青岛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是干什么的呀?”我急忙问。
“是个医生。”王宁答。
……
“噢,那就算了吧。”说完,我转身就走了,把王宁一个人丢在了夜色里。
这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那位女生也去上课了,我和王宁见面也总是客客气气的。不过我心里很好奇,老想问他真有女朋友吗?可是话到嘴边几次都没有说出口。后来,我们俩真成为两口子的时候,我还在追问这个事儿。王宁只是随便地应付几句:“那只是个借口。我妈妈是医生,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心思识破
介绍对象的事情很快过去了。奇怪的是,自从那个傍晚以后,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漫过了心堤。王宁成熟、真诚、稳重,像个可信赖的大哥哥,平时就觉得他挺不错的,如今王宁那种帅气、沉稳的身影总在眼前萦绕,我变得沉默了。
鬼使神差,王宁宿舍的老大竟然看出了我心中的秘密,他张罗着让王宁来“安慰安慰”我。一天晚上,我在小课教室录作业,王宁和老大(王宁在他们宿舍排老六,我在我们宿舍也排老六)走了过来说:“小不点儿,还没走呢?”随后从兜里掏出一瓶有红橡皮圈儿箍着的、胖胖的小葫芦瓶子装的酸奶,递给我,“我们见灯亮着,随便过来看看。
干吗呢?噢,录音呢。”虽然看上去他一副很随意的样子,可我感觉那眼神还真有点儿不太对劲儿,我想说点儿什么,没说出口。他想说点什么,也没说出口,真别扭!从这以后,别扭别扭着就别扭到一块儿去了(哈哈,像个绕口令吧)。
方便面的故事
渐渐地,我和王宁走得比较近了,在班里也比较关注对方。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我因为临时有配音任务,就没有和同学一起去。早晨从男生宿舍经过的时候,看见王宁了。上午录音的时候,心里就一直惦记着他:“他怎么也没去呀?”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回到宿舍准备煮方便面,忽然想起王宁还在宿舍呢,肯定也没吃饭,于是就带上了方便面、西红柿,还有用粮票换来的鸡蛋,跑到王宁他们宿舍去看看。一进宿舍,就发现王宁捂着胸口在上铺躺着呢。
“王宁,你怎么了?”我关切地问道。“我上午到医务室看了一下,说是胸积水,有一点儿炎症,没事儿。”说完他就从上铺跳了下来。这时他才看见我手里拿着的东西,什么也没说,他就开始忙活起来。王宁很会做饭,一会儿,一杯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面就做好了。我们一块儿吃,一块儿聊天儿,感觉比去春游有意思多了。吃完面我问他:“好点儿了吗?”王宁笑了笑回答:“别说,你这一来,还真好多了。”
后来我想,那时他得的肯定是“心”病。
“特殊”待遇
那时,班上只有我一个是北京的学生,所以总能回家过周末。返校时,还会带上两罐子妈妈做的地道的四川泡菜和陈皮兔丁。王宁他们男生宿舍和我们女生宿舍是友好宿舍,经常会在一起聚餐。带来好吃的,自然也少不了叫上他们男生一块儿过来吃。王宁是表现得最爱吃的一个。
开始王宁只是比大家多吃一点儿,后来渐渐就成了王宁的特供品了,其他同学就再也见不到这两样好吃的东西了。当然,王宁有时也会邀请我去他们宿舍吃方便面。这样一来二往,我们单处的机会就多了,在同学眼里,我们俩自然就是一对儿了。
至今,四川泡菜仍是我们的最爱,但陈皮兔丁自从女儿娃娃出生后就不吃了,因为娃娃属兔。
特殊的信
我们的恋爱在毕业的时候面临着一场最严峻的考验。那时候,学校有纪律规定,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家里也都持反对态度。一是因为年龄太小,再加上一个青岛,一个北京,将来分配、调动都是问题。妈妈坚决不同意我与王宁的这场恋爱,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要珍惜能回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好机会,不能因为谈恋爱而耽误了将来的前途。
毕业的时候,要分开了,我们抱头痛哭,只感觉前途迷茫,不知道以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王宁离开北京之前,我的父母邀请他来我家,就我俩的将来和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父母把以后我们所要面临的困难一一分析给我们听。我边听边流泪,王宁本来话就不多,这时就更没话了。
回到青岛后不久,王宁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王宁的信字字都是真言,它让我感到欣慰,又感到酸楚。欣慰的是他对我的一片真情,对我们感情的珍惜;酸楚的是我们天各一方,有着许多不可预知的未来。
进行曲
从中传毕业后,我留在了中央电视台,王宁回到了青岛电视台。我们几乎每两天一封信来往于北京和青岛之间,我们的信都是编着号码的,我们之间的情感只能通过书信来表达。我每次去青岛看他,他的同事都嚷嚷着要我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费。原来王宁在办公室不爱说话,但会突然爆发性地猛吼一句:“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把周围同事都吓坏了。
大家都知道,王宁那是想我想的。他那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贴满了我的照片。王宁告诉我,是我的执著在支撑着他,除了想念我,别的他似乎也无从做起。我暗暗打定主意:如果王宁真的不能调到北京来,我就到青岛去!
1987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分来的大学生,我参加了最后一批中央讲师团,到山区支援那里的教育。当时,我是译制部的骨干,手头有很多的工作,本不打算去的,但那时台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去支教的人台里或多或少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生活或工作中的困难。于是我提出了调动王宁的事,台里答应有机会一定帮助解决。这样我就随着中央讲师团来到了安徽六安,开始了一年的支教工作。
在安徽支教的日子里,白天,我和学生们在一起,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教同学们普通话。有时也在六安电教馆协助工作,或主持、或拍摄、或讲课,每天倒也挺充实的。可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时候,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孤独和思念之情袭来。我常常望着窗外发呆,期盼着能够早日和王宁团圆。
那时我最喜欢的歌就是苏芮的《牵手》:“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黑皮鞋,红皮鞋
终于,1989年,王宁调到了北京,我俩也结束了两地的相思之苦。
刚来中央电视台上班,王宁每周还要值几个《早间新闻》的班。每天早晨4∶20起床,5∶30到班,太痛苦了。我家要上三个闹钟,到点儿时,铃声响起一片,此起彼伏,就这样,他也听不见。没办法,醒不了,我就用脚踹他,不然他还醒不来呢。
“不好,快到点儿了!”迷迷糊糊中,只感觉他起床后一阵拳打脚踢,嘁哩喀喳,冲下楼去。他刚一走,我就像个木头人一样,“扑通”一下往床上一倒,又接着睡过去。至于他上没上班,播没播新闻,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七点多钟,新闻播完了,王宁来了个电话:“老婆,回不了家啦。”“为什么啊?”“脚上的皮鞋颜色不一样,一只黑的、一只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