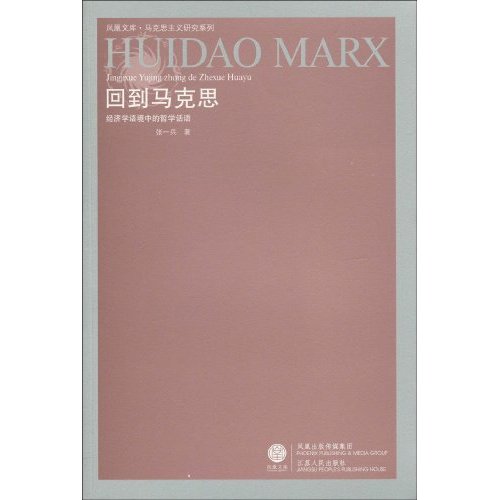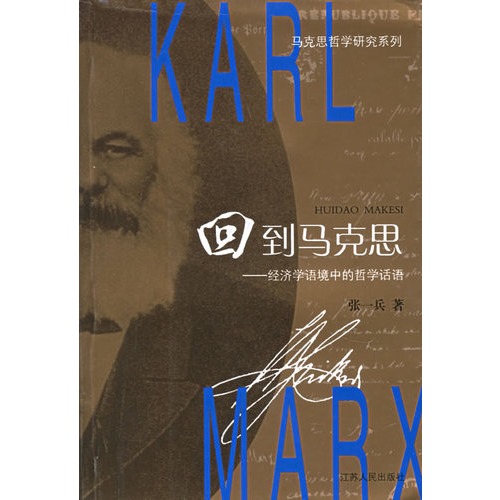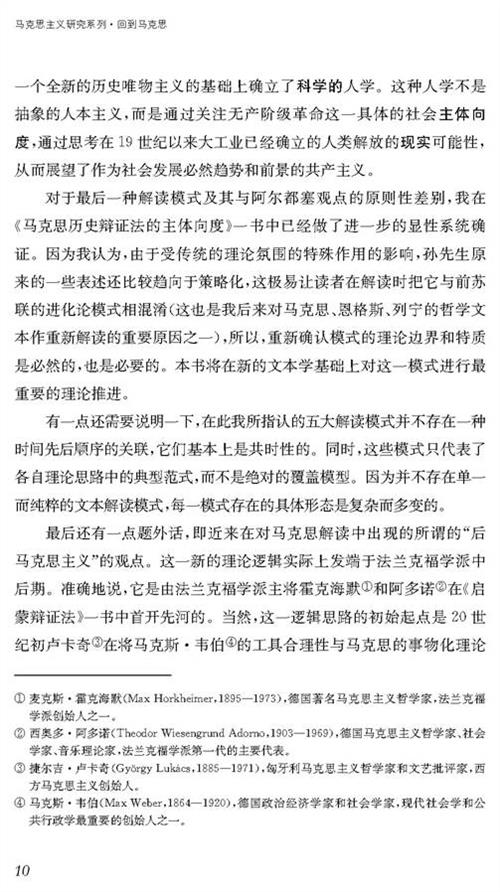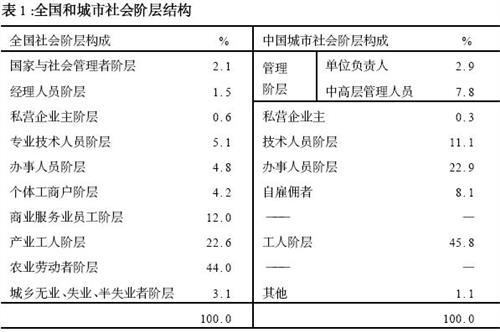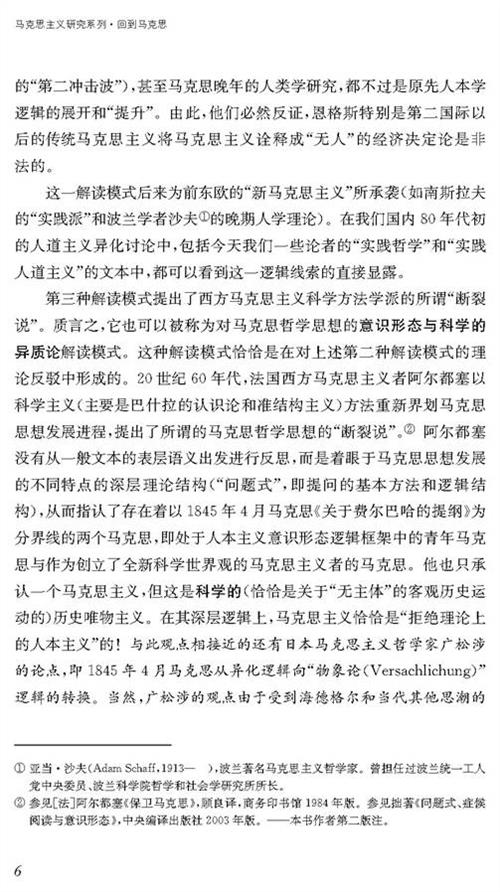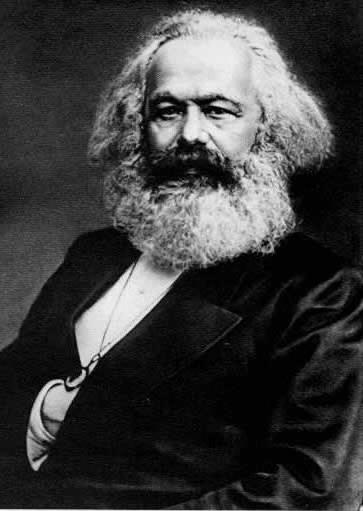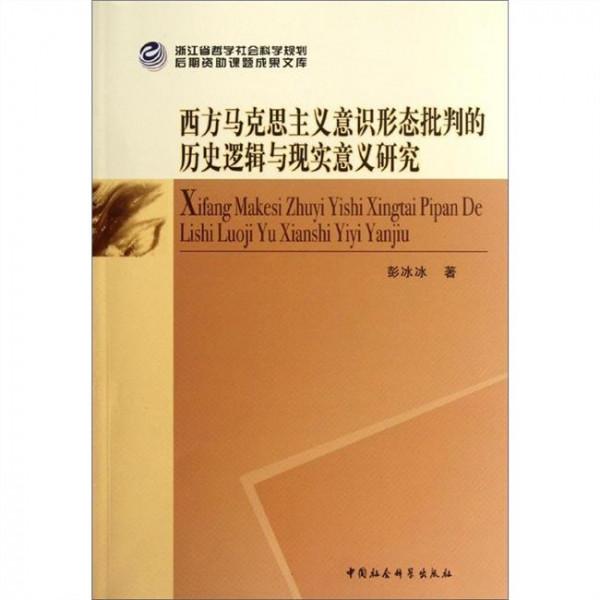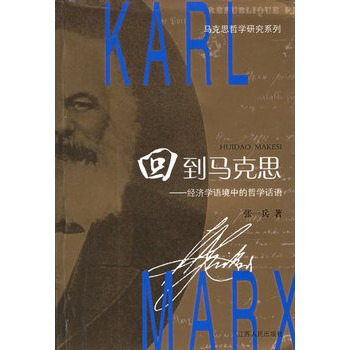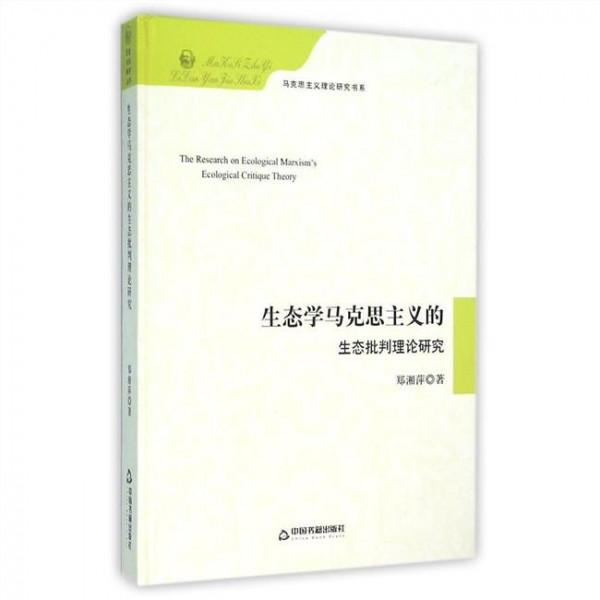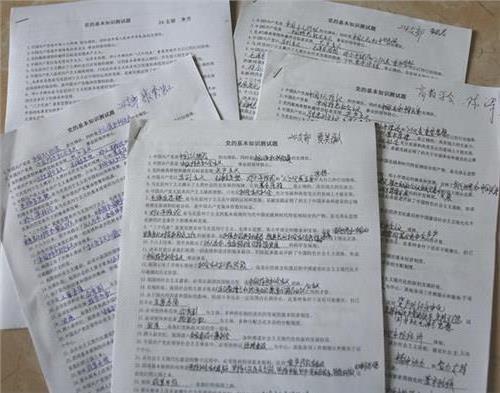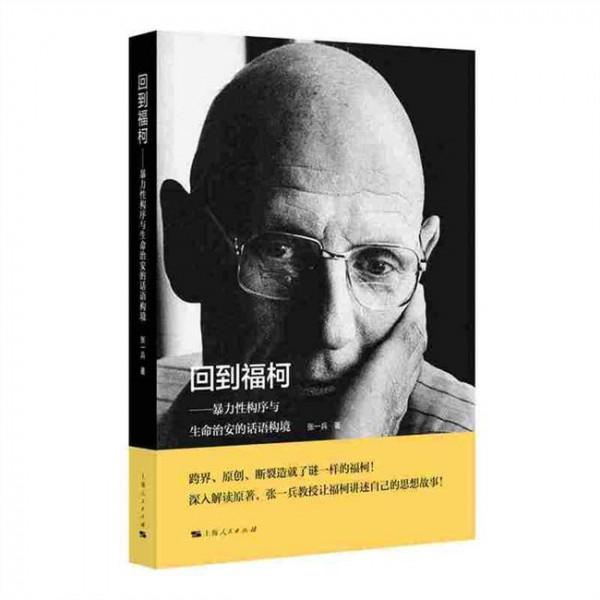孙凤武的婚姻 孙凤武:“回到马克思”新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定位和框架调整
摘要: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应当看到马克思做为普通人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有必要调整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框架,以真正实现理论创新。
关键词:普通人 基本原理 变革型 叙述框架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理论历程中,“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二三十年代,由被后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第二国际的那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战争(一战)中陷入困境,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和平主义与护国主义,造成了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瓦解。
而以列宁为旗帜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信奉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在战争中成功地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随后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第三国际。
但是,信奉列宁暴力革命论的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当时所领导的起义,如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起义,却遭到了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既不满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又对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意大利)、科尔施(德国)、卢卡奇(匈牙利)等共产党人,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判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很少谈论的关于人的本性、人性的异化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地位与意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而在1932年发表了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后,又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派,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
不过,这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活动,影响十分有限。对于正处于革命战争时期而又把列宁主义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另一次是在八九十年代,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的学者所掀起的思想理论浪潮。这一浪潮的背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的带有革命性质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疑问和责难,有人问道:“我们要同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打交道”?[1]p50后来又发生了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这种令世界震惊的重大事件。
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连同它的强有力的一支——列宁主义一起,从居统治地位的宝座上被拉下来,打入冷宫。世界政治格局大变,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在西方一些政要和学者那里,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崩溃”或“终结”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和原苏联、东欧一些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怀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如一向认为“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沙夫(波兰)和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为己任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法国)等人,公开指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求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
人们不难看到,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人、人性、人的解放的思想被突显出来。
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值粉碎了“四人帮”,进行着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而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正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的理论界对“回到马克思”的活动,予以积极的回应。
本来,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理论界已开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初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国内外出现的重大变故和重大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流行了几十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包括写进教科书的那些原理,许多已落后于时代了,有些甚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和马克思的原意。
这样,在应对“回到马克思”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时,就不能不面临种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的复杂情境。
这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进一步正本清源,而且要大胆创新。这里的正本清源,不是梳理出若干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要人们到处套用,更不是重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陷入低潮时遭到贬损的马克思的“圣人”形象,重建个人崇拜。
这里的大胆创新,不是轻率地否定马克思的既有理论去标新立异,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西化”成某种时髦的新教条。“回到马克思”可以被视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原则。研究和运用这些原则,对于搞好这一工程,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做为普通人的一面
要“回到马克思”,就不能不回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他的“第二个我”[2]p569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点、理论、情感、意志的体现。因此,人们在评论马克思主义时,不管赞成、反对与否,都总要对马克思本人做出评价来。
在欧洲人中流行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谚语,它反映了对个人的主体性和判断权利的确认。但是,任何人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固有的客观属性,从其言论和行动中即可表现出来。而对一个人的评价,也大体上有相对确定的客观标准。
对于现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伟大思想家、革命家和导师,是在一切方面都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中共在解放前,曾把马克思的生日五月五日定为学习节,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这种理念,在批判了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仍无大改变。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一点,即使在马克思的敌人中,也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得到了认同。例如巴枯宁在与马克思决裂并激烈攻击马克思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渊博的学者。
他是一个有根底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热情地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这个事业。
”[3]p232直到现在,世界人民还是承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以致几年前英国一家新闻机构在进行对前一千年最有影响的世界名人排队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占据了第一位!对马克思做为杰出人物这一面,人们大体上已熟知了,但对其做为普通人这一面,人们往往知之甚少。而不了解后一面,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就难以正确地、全面地掌握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而又文明的家庭,自幼便受到了基督教新教所宣扬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熏陶,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带给莱茵地区的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精神的影响。他之天资聪明和做为唯一存活下来的男孩所受父母的偏爱、呵护、教诲,他之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实现了成功的恋爱,对于形成他的自强、自信的品格,培养他对受难者的同情心,以及对美好生活、崇高事业的热切追求与成就感,起到了最初的推动作用。
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时,对哲学和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
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物质利益”问题,深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群众的疾苦。他在刚刚出版的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启示下,迅速脱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转向了唯物主义。
马克思之勤奋好学和积极进取,使他对所受到的各种思想理论的影响,都采取了批判态度。当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认真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后,便迅速越过了费尔把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并与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在他们随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正式宣告了科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满怀青年人特有的激情返回德国参加了实际斗争,期望并促使革命取得胜利。
然而,这场革命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在伦敦流亡期间,如社会主义史学家梅林说的那样,马克思“退到书房”(大英博物馆),集中精力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并继续关注欧美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但工人运动的消沉,毕竟使他感到孤独和寂寞。
特别是他同昔日的战友、冒险主义者维利希、沙佩尔的决裂,使他在伦敦的朋友极少,而在他的祖国德国,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拉萨尔是唯一还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
”[4]p278有一次他埋怨住在曼彻斯特经商的恩格斯说:“我的一些嫉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4]p314马克思的好友和学生李卜克内西曾记述过他们这些流亡者的一次恶作剧:他和马克思在晚间酒后曾蓄意打碎了伦敦一条街道的四、五盏路灯,警察赶来时,他们迅速逃离,消失在黑暗中。[5]p117-118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尽管有恩格斯的经常、大量、慷慨的帮助,马克思一家仍然常常陷入贫困之中,并受疾病的折磨。马克思有一次苦恼地说:“没有家的人真是幸福。”[4]p371不久又说:“对于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没过于结婚。
”[6]p274他和妻子燕妮都不善料理家务,家庭开支常常出现亏空,当得知燕妮的伯父患了不治之症时,他告诉恩格斯:“如果这头牲畜现在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困境。”[4]p29不久这位伯父果然死了,马克思说这“真是一件大好事”[4]p436,因为燕妮得了100英镑的遗产。
有一次,马克思还“做起‘股票’投机来”,并高兴地告诉恩格斯,说他“赚了四百多英镑”。[2]p662他对正在替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的恩格斯说:“重要的不在于文章写得深刻,而在于写得长”[6]p463,因为写得长了,稿费也就多了。
由于物质生活上的困难,马克思对于二女儿劳拉的婚事颇为操心,他告诉恩格斯:“今天我用法文写了一封长信给拉法格,告诉他,在把这件事继续下去并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我必须得到他的家庭关于他的物质情况的明确报告。
”[7]p254在他得知拉法格的父亲邀请他的三个女儿同去波尔多后,写信给恩格斯说,让拉法格支付旅费“是不体面的”[7]p324,并再次求助于恩格斯。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库格曼的信中又讲了这样的话:“为了孩子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8]p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