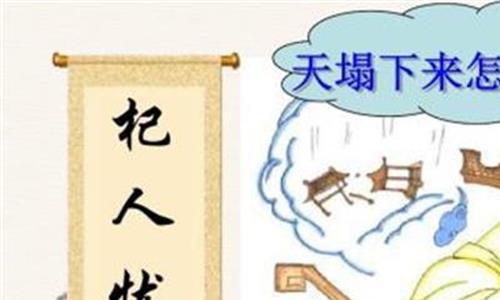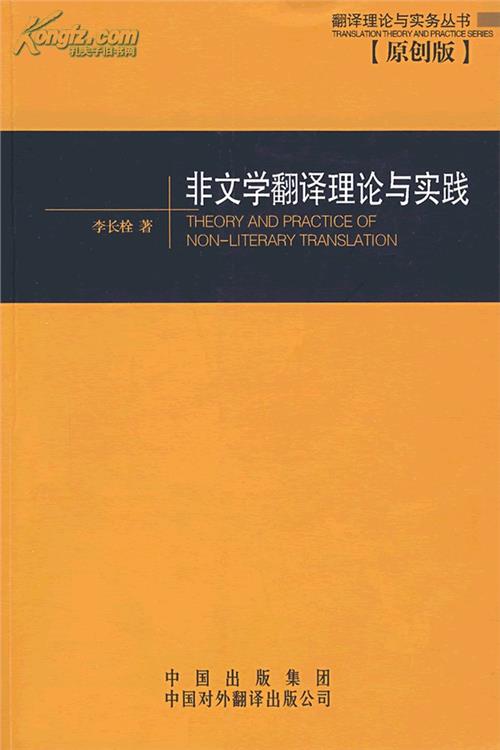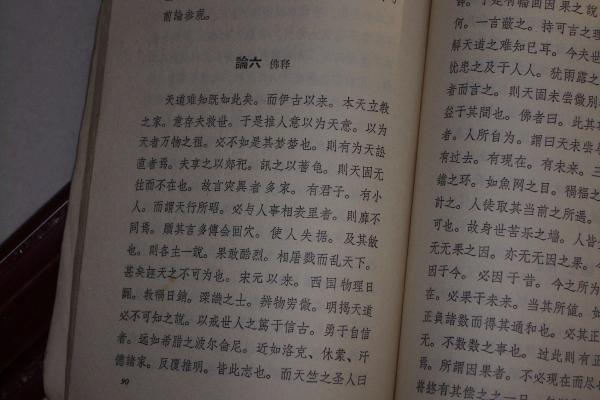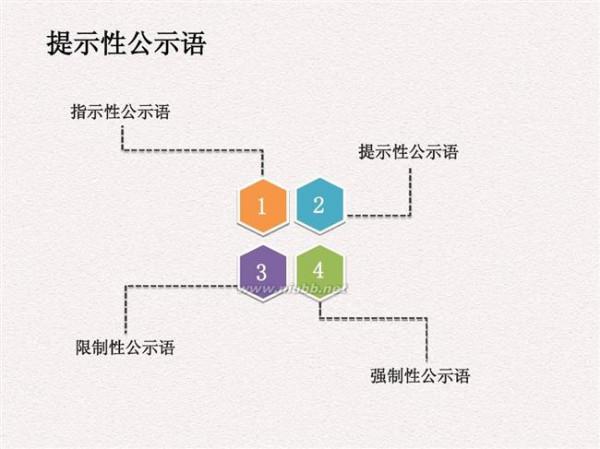翻译姚媛 姚媛:翻译给了我什么
译文同样如此。首先,翻译起始于并非一成不变的原作。其次,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语言本身和语言之外的东西都会发生变化。一方面,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完全的对应,其含义在翻译中不同程度地会丢失、添加、改变。
另一方面,既然原作并非一成不变,那么译者翻译的只能是他/她在此时此地所理解的作品,而译者的理解必然受到自己生活环境、知识阅历、思想观念、甚至性格爱好的影响。最后,译文和原作一样,完成后必然经过读者的阐释而成为新的作品。
《身着狮皮》重构了一座新的多伦多,这座城市的文化既吸收了不同移民群体的文化,又不同于任何一个群体的文化,是经过了不同文化交叉转化之后形成的新文化。翻译的过程则建构了一部新的作品——它不是凭空而起的“新”作品,它的形成是有依据的;但它又经过了阐释和转化,不是对原作的照搬。它非此非彼,也非亦此亦彼。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身份也变动不居。当我沉浸在作品中时,我真切地经历了人物的生活,与此同时,我又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思考他们的生活,并用自己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当我细细咀嚼作品时,我不断地、无限地接近作者的思想,他/她的思想仿佛成了我的思想,可我知道,我在译文中表达的是我所理解或领悟的作者的思想。
我既在书里,也在书外;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我在不同的世界穿梭,不断地用别人的思想经历丰富、改变自己,不断地将自己的思想经历融进——而不是强加进——作品之中。
译文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沙砾坑旁边。不是那种用庞大的机器挖出来的大坑,不过是一个很多年前某农场主一定用它赚了点钱的小坑。实际上,它太浅了,会让你认为它可能有别的用处,也许是房子的地基,只是后来房子没盖成。坚持让大家注意那个坑的是妈妈。
“我们现在住在加油站那条路上的老沙砾坑旁边。”她对人说,然后哈哈大笑,因为她很高兴摆脱了和镇上那座房子有关的一切,街道,丈夫,她过去的生活。我几乎不记得那段生活。也就是说,我清楚地记得某些部分,但无法将之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我脑子里关于镇上那座房子的记忆只有我以前房间里画着玩具熊的墙纸。在这座新房子里——其实是一座拖车房——姐姐卡萝和我睡两张很窄的小床,上下铺。我们刚搬去的时候,卡萝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以前的房子的事,努力想让我记起这个那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她会谈这些,通常说到最后我什么也不记得,她就会很生气。有时候我想我其实记
起来了,但因为我记得的和她说的相反,或者因为害怕记错了,所以我假装不记得。我们是在夏天搬进拖车房的。我们把狗带来了。布丽兹。“布丽兹喜欢这儿。”
妈妈说。这是真的。哪只狗会不喜欢把镇上的街道换成开阔的乡村呢,即便镇上有宽敞的草坪和高大的房子?它迷上了对每一辆开过的汽车吠叫,好像这条路是它的,还时不时叼回家一只被它杀死的松鼠或土拨鼠。刚开始,这让卡萝感到很苦恼,尼尔和她谈了一次,向她解释了狗的天性,以及某些东西必须吃其他东西的生物链。
“可它有狗粮啊”,卡萝争辩说。但尼尔说:“假如它没有呢?假如有一天我们都消失不见了,它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呢?”“我不会”,卡萝说,“我不会消失不见,我会永远照顾它”。
“你真这么想?”尼尔说。然后妈妈开始干涉,让他转移话题。尼尔总喜欢开启美国人和原子弹的话题,而妈妈认为我们还不应该谈论这些。她不知道当他谈论原子弹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原子蛋。我知道这个理解不太对劲儿,可我不愿意提问,然后被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