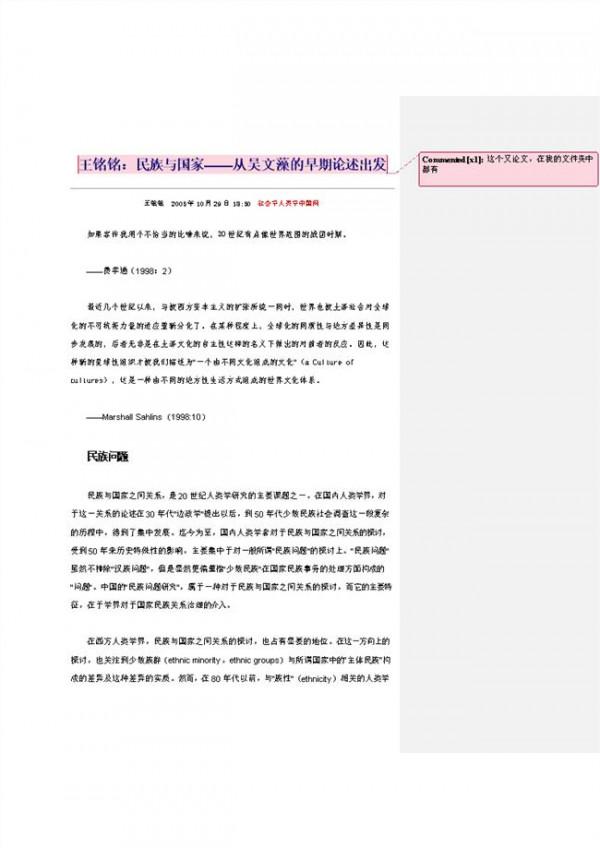翁文灏后人 北大名人后代忆北大——我的伯父丁文江:20世纪的徐霞客
北大名人后代忆北大——我的伯父丁文江:20世纪的徐霞客
北大人物
北大人物
本文选自北大出版社新书《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31—1934年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本文作者丁明远为其侄。
我国近代自然科学起步较晚,但地质科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与我国几位地质学先驱者的辛勤创业、呕心沥血、兴办教育、培养英才、奋发图强是分不开的。我的伯父——丁文江就是其中之一。
小镇神童 知县看中
伯父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侨镇。伯父在父辈七人中排行第二。从小聪明伶俐,备受祖父母宠爱,还在襁褓之中,祖母便教其读书认字。他五岁入私塾,尤喜读古诗词,读起书来朗朗上口,过目成诵。
塾师惊其资性(智力)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伯父脱口而出:“还读我书。”塾师击掌叫绝,又曰:“虎哮地生风。”伯父又对“鸠鸣天欲雨”。师遂叹其:“年才髫龄,志趣不凡,赞为神童!”
他九岁时,就好浏览《三国演义》等古今小说,还读了《纲鉴易知录》、《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经典著作。他最崇拜陆贽、韩愈和苏东坡、史可法等几人。到十一岁时,他竟然作出了《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这样洋洋数千言的文史论文。由于我祖母的谆谆教诲、塾师的殷勤指导以及他自己的博览自修,在十多岁时伯父就已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在伯父十四岁时,发生了影响他命运的一件事。当时初上任的泰兴县知县龙璋(字研仙,湖南攸县名士,谭嗣同的表兄弟)提倡新法,重视人才。听说少年丁文江有奇才远志,就叫我祖父带着二伯父到县衙,对他进行面试,出了一道考题叫《汉武帝通西南夷论》。
伯父当场作文,论述中多所阐发,龙叹为“国器”,当即收他为弟子,并极力劝我祖父送伯父去日本留学。这在当时的泰兴简直是破天荒的事!不少守旧亲戚朋友都心存疑虑,从中梗阻。但龙璋以恩师的身份和父母官的力量来不断劝导,又托他的湖南同乡胡子靖带伯父去日本,终于使我祖父下了决心,借债也为他凑足了盘费,把伯父送上了出国求学之路。
东渡西泛 艰苦求知
1902年秋,伯父随胡子靖乘船去日本,住在东京神四区平民住房里。伯父一面学日语,一面活跃地参加中国留学生“谈革命,写文章”的活动,曾任江苏留日学生的杂志《江苏》第三任总编辑。他写的文章很流畅,慷慨激昂,富于革命情调,很受我国在日留学生的欢迎。
一年后,伯父的同学庄文亚常接到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留学的朋友吴稚晖(敬恒)寄来的信,说那里是一个生活消费便宜、科学发达的地方。因此庄文亚找到伯父及另一友人李祖鸿商定同去英国留学。
他们三人身上一共就只剩十几个金镑,却开始了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乘的是德国船去英国,但听说到伦敦下船后,再乘火车去爱丁堡还需很多钱时,才开始着急起来。
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当船靠新加坡槟榔岛时,他们听说维新派政治家康有为正流亡在此,就上岸去拜访。康知道这三位青年的事情及来意后,对伯父几人极为关怀,先送给他们十个金镑,然后又具函一封,叫伯父他们到伦敦后去找他的女婿罗昌。后来,罗昌在伦敦见信后,又资助他们二十个金镑,伯父他们才摆脱了窘境。接着他们去爱丁堡找到吴稚晖,得知吴已为他们安排好住所,才松了一口气。
伯父初到爱丁堡,无意中幸运地遇见一位叫斯密勒的医生。这无疑是伯父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斯曾在陕西传过教,知道伯父是从中国来的穷学生,就劝伯父去他的故乡——英国东部一个叫斯帕尔丁的小镇读中学。伯父邀朋友李祖鸿一起去了斯帕尔丁,发觉那里的生活费和学费确实便宜,于是便留了下来。
斯密勒是本地乡绅,为人很好且热情,常常关心伯父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他对伯父很照顾,他的亲友也都待伯父如同家人。伯父每逢节假日,便常去各家串门,与他们一道喝茶、聊天、吃饭……就这样,伯父不但巩固了英语会话能力,交了许多朋友,也全面了解了英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生活。
伯父一年跳三级,两年就学完了英国中学的课程,还获得几枚紫铜奖章。他有个同学叫斯金诺(后来也成了文学博士),多年来蝉联全班第一,伯父跳级到他这班后,却夺走了他的魁。他不服气,到教员桌上偷看伯父的试卷。看了以后,才彻彻底底地服了。不但无话可说,反而和伯父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对伯父极为钦佩。
伯父读完中学课程后,于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英国剑桥大学,但由于剑桥大学学费昂贵而转读格拉斯哥大学。经过伯父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学习,1911年,伯父取得了格斯拉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文凭。
异国学成 徒步考察
1911年4月,伯父满载留学的收获,登上了返国的路程。他和一般留学生不同,不是从欧洲搭船直航上海,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经老街而入云南的河口,踏上了祖国大地。他在昆明住了半个月,作了一些准备,就开始了返国的第一次徒步为主的大旅行。
他从昆明向东经沾益入贵州,经贵阳、贵定而到镇远,然后乘船入湖南,经黔阳、常德到长沙,再经汉口、南京而于8月初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这次旅行历时两个多月,行程约万里。饱览了祖国壮阔的山河,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兄弟民族的奇装异服、特殊习俗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
他在云南平彝地区起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清康熙年间的地图一直被沿用至今,那上面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错误了两百多年,如今才被他纠正过来。这次旅行为他在以后的两次西南考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兴办教育 培养人才
1913年,当时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是位很有远见卓识的人士,深知地质事业对国计民生之重要,聘伯父去北京担任司属的地质科科长,并把回国的地质学家辜鸿钊和翁文灏都请了进来,共商筹办地质调查所,首议是如何培养地质人才。
在章、丁、翁三位的通力合作下,他们办起了工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由章任所长,伯父和翁文灏都在那里任教,伯父主讲古生物学课。他是开这门课的第一个中国人,常率学生外出实习,他不辞劳苦,以身作则,“登山必到顶峰,移动必须步行”,使学生理论知识及实际操作能力都受到了全面培训。
该所只办了一期,招生三十名,毕业二十二人大都进入地质研究调查所,不少人都是中国地质事业早期的骨干和后来的权威巨子,例如叶良辅、谢家荣、李学清、徐渊摩、徐书曼、芦祖荫、朱庭枯、刘季辰、王竹泉、李捷、周赞衡、谭锡畴等。
1931年秋,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之聘,伯父任北大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地质学通论》等课程。“在此课程中,被充分使用中国地质实例,借以解释各种侵蚀、沉蚀、沉积、火山、地震诸现象。先生并亲自率领学生作野外旅行,所有地质问题,均就地商讨。
”当时北大地质系在四月放春假期间与七月放暑假期间,一般都安排有为时几天或个把月的野外地质实习工作。他对于野外实地工作非常重视,要求严格,亲自参加指导,生活上也和学生一起,他为自己准备的野外工作午餐,也只是一两张烙饼卷些炒鸡蛋来吃,而从不携带面包、奶油及罐头之类的高级食品。
他在北大任教情况,当时的助教高振西曾写道:“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对于标本卦图之类,都全力罗致,除自己采集、绘制外,还要请托中外朋友帮助,务求美备。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在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
据当时在北大的学生蒋良俊回忆:“我是在1930年秋考入北大地质系的,次年秋,丁先生到北大任地质系教授,同学们久仰先生的大名,都很高兴,但当时丁先生担任的是一年级的普通地质学,这门课程对我们进入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是刚刚学过了的。
记得当时担任地史学课程的美国人葛利普先生说,在美国的大学,各系最基本课程,都是由所谓Lead Professor来担任的。他认为丁先生学问渊博,由丁先生来担任讲授普通地质学是最恰当的人选,机会难得,所以建议我们同学再听一遍。
果然,丁先生讲课,确实内容丰富,尤其是我国实际材料多,对在他自己所做的许多实地工作中,见到的地质现象,讲述时都有分析,有自己的看法,讲得非常生动,吸引人,不但能为同学们学习地质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能启发同学如何进行思考及分析问题,听了丁先生的讲课,我们都感到受益不浅。”
1918年底,伯父随梁启超、蒋百里赴欧洲考察战后形势。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开,他们成了中国的“会外声援团”顾问,配合国内的五四、“六三”爱国运动,督促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等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在和会上,伯父认识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所率代表国的科学顾问、地质学家里斯。他通过里斯的介绍,认识了大地质学家怀特,通过怀特推荐,聘请了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华。葛于1920年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双肩挑起教学和科研的两副重担,作出重大贡献。
在欧洲时,伯父知道李四光是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专学地质的,特地找到李四光,希望他回国教书,并告知中国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不久,李四光接到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主讲岩石学、矿物学。
这样,北大地质系教学质量显著提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包括钱声俊、王绍文、杨仲健、王恭睦、赵亚曾、张席提、侯德封、俞建章、王恒升、王炳章、徐光熙、斐文中、黄汲清、李春昱、季荣森、潘仲祥、高振西、王钰、李连捷、高平、阮维周、卢衍豪、叶连俊、岳西新、杨敬文、陈恺等著名的地质学家。
伯父以地调所所长和北大地质系教授的身份,长期有力地支持了北大地质系,曾筹巨款为北大地质系建地质馆,并充实、更新图书设备,使北大地质系在抗战以前已成为亚洲著名的大学地质系,并招收了日本、苏俄的博士研究生。
崇尚科学 反对玄学
1923年,当时《努力周报》讨论的问题较为广泛,该报每月增刊一期《读书杂志》。伯父在那上面也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最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莫过于科学和玄学的论战,也称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这场论战是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周刊》发表长文《人生观》而引起的。张在该文内提倡抽象的唯心主义“人生观”,谈到:“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曰单一性的。惟其有五点,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试验室而已。
”又说:“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测试室与工厂遍国中,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知也……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鲜矣!
”张把梁启超早几年认为“欧战是科学的罪恶报应”的错误论点发展到了“科学破产论”,主张“菲薄科学”,说“我国立国之方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反对“富强政策”,反对工业化、现代化。
直接目的是反对和阻挠青年学生学习现代科学,而要去膜拜那些“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
面对玄学对科学的挑战,伯父奋起迎击,发表了《玄学与科学》(1923年4月15日、20日)、《科学答玄学——答张君盛》(同年5月27日、6月3日),《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同年6月10日)等长篇论文。
他在给章鸿钊的信上曾说:“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又在《玄学与科学》一文的“引言”里说:“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
伯父的《玄学和科学》一文共分十段,归根到底主要回答了两个大问题。即:第一,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第二,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
就第一问题,他指出,在西方,科学与神学的斗争源起于古代,延续至今,他认为:“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战争不能废止,也是如此……到如今,欧洲的国家果然因为战争破产了,然而一班应负责的玄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而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务外逐物’,岂不可怜!
”
对第二个问题,他深信“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最好的“处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他说:“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
无论见到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导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直知道生活的乐趣。
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这便是真正懂得科学精神的伯父的人生观的写照。
伯父给玄学下了个定义:“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上排论出来的规律。”并说:“言心言性的玄学,‘内心生活的修养’,所以能这样哄动一般人,都因为这种玄谈最合懒人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理与分析。顾亭林说得好,‘……以其龚而取之易也’。”真是一语道破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
这次论战,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如梁启超、任叔永、胡适、孙伏园、林宰平、张东荪、朱往农、唐钺、吴稚晖、陈独秀等,都纷纷著文参加论战。以后曾辑成专书两册出版,书名为《科学与人生哲学》。
任总干事 改革体制
1934年6月,伯父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应蔡元培之邀请,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伯父当时刚从美、苏参观讲学归来,目睹苏联建设的辉煌成就,衷心敬佩,原拟回国后投身舆论界以推进国家的根本改革,故不愿从事此类机关工作。
在蔡坚邀之下,才勉强担任。他在短短两年不到的工作期间内,大刀阔斧地对中央研究院进行体制改革,财务上根据研究院的科研任务制定预算,组织上则组建评议会,院内重大事项均须经由评议会讨论决定。这样就为当时这一全国最高科学机构奠定了科学和民主的基础。这些事,许多老一辈科学家都是熟知的。
翁文灏在193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近年来在君先生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的工作第一在促进各研究所切实研究,把不能工作的人撤换了,把能工作的人请进来,而且与他们商定应解决的问题,应进行的步骤。第二在详实规定各研究所的开支,各所的预算很真实的按照他们一年度应做工作必须数目来规定,省下来的钱用以举办以前未做的工作,其结果是工作加多而开支减少。
他并成立评议会,实际完成了全国科学院应有的组织,做这种事不但要热心毅力,而且要有充分的专门科学的知识与经验。”
对此蔡元培先生曾说:“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遍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遍能办事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
挚友缅怀 闪光感人
1986年4月20日,湖南省各界在长沙举行纪念伯父丁文江逝世五十周年大会。
伯父没有子女,也不立嗣(也就是不立继承人),我们的伯母史久元已于1976年逝世。当时由我们的七婶母史济瀛率领我们侄辈们前去参加这次纪念会,并由我代表家属发了言。我们非常荣幸地拜见了伯父生前的同事和好友黄汲清伯父、曾世英伯父和李春昱伯父,他们长途跋涉、不辞辛苦从北京前来参加这次纪念会,以真挚的感情回忆与伯父相处的日子,叙述了很多生动的事迹,使我们后辈受到了伯父爱国爱科学的生平事迹的教育,这也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汲清伯伯称:
文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的徐霞客。
1913年他会同梭尔格、王锡宾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填绘分幅地质图,这是中国人开展系统的野外地质和地质填图的开端,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1914年他孤身去云南,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调查、研究滇北、滇东和四川全理、贵州威宁一带的地层、地质构造,还专门调查了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展边远地区的大规模地质工作,是地道的探险工作。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从他写的《漫游散记》中可以窥见一斑。1928年的广西之行,以及1929—1930年的贵州、四川之行,虽然说不上是探险,但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地质勘探的处女地,他的开创性工作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他生平最佩服徐霞客,而他自己就是20世纪的徐霞客。当然他处的时代不同,所以他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此外,他在发现人才、培育人才、爱护人才、提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成绩很大,影响深远,他是20世纪的伯乐,这一点更是徐霞客所不能及的。
曾世英伯伯讲:
《徐霞客游记》现在有好几个版本。这一杰出的科学文献,今天受到广泛的重视,和丁先生首先的发掘是分不开的。丁先生对《徐霞客游记》不仅在文字上作了整理,而且撰写了年谱,并附加地图。这是相当繁重的任务。去年为了纪念徐霞客,商务印书馆将丁编本《徐霞客游记》重印。这可以说一方面为了纪念徐霞客,另一方面也是纪念丁先生。
丁先生其实是现代的徐霞客。丁先生由英留学回国时,只身取道云南、贵州、湖南返乡,途中进行地质考察。有过这么一件趣事,我们在川广铁路调查时虽备有乘骑,但丁先生为了实地考察,测地层倾斜走向,敲岩石标本及化石,绝大部分行程都是步行。有人笑说丁先生是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
在我与丁文江和翁文灏两先生合编的《中国分省新图》(时称“申报地图”),试用了等高线分层设法表示地形。丁先生相信群众,放手让我们工作,这也是丁先生在用人方面有他杰出的领导方法的表现。如果说《申报地图》在读者对锦绣河山认识的提高上起过一些作用的话,则是在体例订定以后。
正编本《中华民国新地图》在欧美被称为丁氏地图(V.K.Ting Ahas)这又很能说明丁先生在国外的声誉。
丁先生非常爱护人才。1929年11月15日,到达贵州大定的当晚,我正在院内观测星象定经纬度,忽闻丁先生在屋内放声痛哭,乃知传来了赵亚曾在云南昭通遇难的噩耗。我对丁先生多方安慰,无济于事。等我测毕回屋,他还在哭,几乎哭了整整一夜。以后丁先生一直为这位在地质研究上已作出贡献并大有前途的科学家罹难而惋惜。
丁先生积极参与筹募“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共有一万七千多元捐款,以利息来奖励在地质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学者,同时又筹集了赵亚曾的“子女教育基金”,以照顾赵的遗孀及三个孤儿(两儿一女)。丁先生本人无子无女,他常把赵的长子松年带在身边,有时一起去避暑,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丁先生之爱惜人才及与广大地质工作者之间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李春昱伯伯讲:
丁文江先生非常关心对青年人的培养,对此我深有体会:1934年我考取河南省公费赴英留学,其时丁先生在南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我动身之前,他发了一个电报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嘱我去上海上船时,到南京去见见他。
我遵嘱于一天早晨到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宿舍去看丁先生。丁先生一人住在那里,他正在吃早饭,边吃边与我谈话。他劝我改赴德国,一是因为地质调查所学英语的人比较多而学德语的人比较少,为着地质调查的前景,应该多学几种语言。
第二个理由是他在1933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地质会议上见着了H. Stile,Stile是德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很适合作导师,但他辅导学生极其认真,不同意他的学生在他不能来去指导的地方作学术论文。
丁先生问我有没有勇气学一个新的语种,怕不怕困难。一个青年人在长者面前,怎能说没有勇气,怕困难呢?我便回答说:“不怕困难。只有几个问题须待解决,第一,河南教育厅初试和教育部的复试派遣留学生名单中都是英国,现在改换德国,须得到教育部和教育厅的批准;第二,我的护照签证是签的英国入境证,现在要改签德国入境证;第三,我的用费都已汇到英国,进德国手中无现款。
”丁先生说:“这都容易解决。第一个问题,我替你办理。
第二个问题,你到欧洲下船后,先到瑞士去找汲清(黄汲清),瑞士是不需要签入境证的。第三个问题,写信给伦敦中国银行请他把钱转汇到柏林就可以了。”他又问我乘坐的哪国的船和船名,我作了回答。船行至新加坡时,我接到丁先生电报,说教育部已同意改往德国,一切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我便往瑞士进德国直往柏林。丁先生怕我初到德国,不免感到困难,他另外写信给中国驻德公使(丁先生的朋友),托他照顾我。丁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了。
1986年,我在上海特地访问了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国际原生物学家协会名誉会员、华东师大生物系名誉系主任张作人教授,他已八十几岁了。当我一提起伯父丁文江时,他非常热情而兴奋地告诉我说他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与我伯父丁文江先生的教学方法的启迪是分不开的。
张教授年轻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当时该系的遗传学开不出,我伯父自告奋勇执教这门课,张教授说,他对第一堂课的印象特别深刻,终生难忘。伯父上课时首先讲到:“我不仅是来教你们遗传学的,更重要的是教你们如何学会科学研究方法的。
”随后举了八仙之一吕洞宾和一个叫花子的故事。叫花子问吕洞宾要东西,吕洞宾拿了一块石头,用手一指变成了金子,给叫花子。叫花子不要金子,而要吕洞宾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因为金子总会用完的,而有了那个宝贵的手指头,就不愁没有金子了。伯父又说:希望你们同样不要那块金子,而要的是那个能点石成金的指头。
伯父的办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旧充满活力,对当前教育界强调培养学生能力、发展智力、造就科学人才同样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与伯父生前好友的黄、曾、李、张(留法)四位的访问中,有种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我,这几位长辈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掌握多种外语,甚至可以之谈笑风生,使我肃然起敬。从他们的谈吐中我也强烈感到伯父提倡多学几种外语这一导向意识的正确。
而伯父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能阅读英、法、德、日、俄等文字书籍,能说英、法、德三国语言,英语尤为流利。人称伯父是一位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孜孜不倦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精通多种外语是分不开的。
以身殉职 痛惜早逝
伯父在他最后一次去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实地调查时,不幸煤气中毒,抢救无效,于1936年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他为了国家的兴旺,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享年只有四十九岁。当时还处在壮年,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他走得太早了,是我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也给我们后辈留下无尽的悲痛!他的以身殉职值得我们纪念,也是我国科学家应感到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