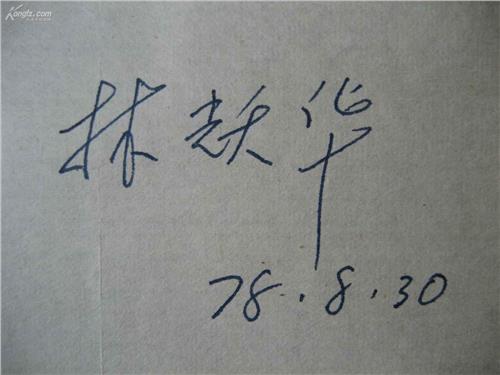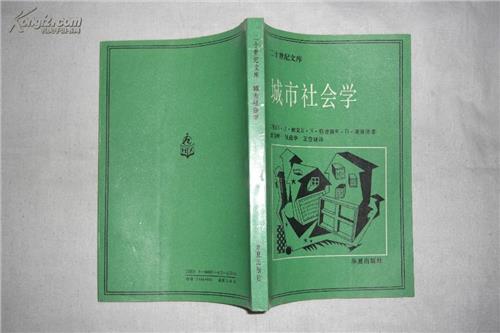林耀华义序的宗族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摘要】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
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义序是1935年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半世纪以来,学术界包括林耀华本人未能对建国后的义序进行跟踪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人类学回访高潮背景下,阮云星对义序“后制度性宗族”进行了回访研究。
但是,阮先生是基于人类学关怀对义序“文化宗族”进行现时性研究,缺乏对其历时性研究。宗族乡村是一个自治的团体、政治的单位。建国前后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国家政权下沉,宗族瓦解。对此,学术界有所研究,如柯昌基认为家族阻碍社会前进,应毁灭。徐扬杰认为革命摧毁了家庭制度。冯尔康认为,土改瓦解了家族。这些成果大多关注建国前的革命对宗族的影响,并倾向于宏大叙事,而缺少个案实证的支撑。
一、义序的土地分配状况与土改过程
乡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区域特征和产业结构等均不同程度上影响基层土改的进行。
(一)解放初期的义序
义序位于闽江下游河口地带、福州南部的南台岛上。南部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水陆通道穿南北两座小山丘而过,将南部聚落一分为二。水流北面的山丘叫后山(雅称鲤山),南面的小山叫外山(雅称榴山、义山);外山临江,后山北面的乡道可通福州,接官道与外界相连。
义序是由黄氏主导的宗族村落(十五个房派,数千族众)。20世纪30年代,黄氏占义序人口的98.4%。1949年8月17日,林森县解放。1950年4月19日,林森县复名闽侯县。
闽侯县分区(12区)管理,而义序属于第一区。1955年4月,义序镇26个自然村改属盖山区,划归福州市区行政办事处管辖。义序以小河为界,前后分为两乡:居前为中心乡,由中亭、中山、新安三村构成,共1127户,5215人,土地2211.9亩,人均土地0.42亩。居后为榴山乡,由浦口、竹榄、尚保三村构成,共1124户,5049人土地2134.7亩,人均土地0.42亩。
(二)义序土地分配状况的探析
1、公田未统计入封建剥削阶级时,土地极度分散
土改的原由是中国土地制度的极不合理性。1950年6月14曰,刘少奇认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
”訛但是,土改前,占闽侯县人口的7.6%的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占全县耕地的20.1%;92.4%的贫农、雇农、中农等占全县耕地的79.9%。輰占第一区人口的3.
8%的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占全区耕地的16.63%;96.2%的贫农、雇农、中农等占全区耕地的83.4%。訛占榴山乡人口的3.1%的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占全乡耕地的18.8%;96.9%的贫农、雇农、中农等占全乡耕地的81.2%(见表1)。可见,不管是县、区,还是乡,基层土地较为分散,与中央的估计相差甚远。
2、公田统计入封建剥削阶级时,土地相对集中
基层土改实践者一般将公田纳入封建阶级范畴内,其依据是“所谓公地是豪绅私产”土改前,公田比重:闽侯县23.7%,一区22.5%,榴山乡11.4%(见表1)。将公田纳入封建阶级中进行统计时,闽侯、一区、榴山封建阶级占总耕地的比重分别为43.8%、39.1%、30.2%。可见,这种统计方式修正了上述“土地极度分散”的结论,不过修正后的结论与中央的估计仍有较大差距。
(三)义序的土改与土改中的义序
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较为发达,农业人口量占总人口之半,群众一般带有小聪明的城市人民的思想意识。”这是义序土改的自然社会经济背景。义序是新区,没有立即进行土改,而是先剿匪反霸、减租减息。1950年8月,闽侯县在四区兰圃乡进行土改试点。
訛一区于9月至1951年1月25曰,分三期进行土改。其中,敖峰作为实验乡于10月15曰结束。第一期,9月下旬,工作组梅花形的安排了7个乡(城门、胪雷、黄山、下洋、林浦、盘屿、台屿)进行土改,至10月20曰结束。
第二期,开辟潘墩、龙江、谢坑3个新基点乡。第三期,对中心、榴山、乾元、吴山、螺州5乡进行土改。从全区来说,这5个乡是落后的。这样布置把这5乡包围起来,以周围的土改事实来教育这5乡的干部与群众,从而提升大家对土改的信心。义序作为“落后乡”,其土改是置于县-区土改战略布置之下,是由先进乡所包围而带动的。
二、土改中族田的征收与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
(一)族田征收:土改阻力的减小与动力的增加
1948年2月25曰,毛泽东指出在新区土改中,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訛因为“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就是在封建阶级中,也“只动地主不动富农”。
在榴山乡土改中,11户地主原占475.7亩,11户被没收161.1亩,减幅达33.9%;18户工商业者原占94.8亩,16户被没收41.8亩,减幅达44.1%;1户半地主式富农原占18.7亩,被没收1.
7亩,减幅达9%;38户小土地出租者原占231.3亩,22户被没收39.4亩,减幅达17%;2户富农的土地没有被没收;309.6亩的公轮祭田,被征收291.5亩,减幅达94.1%。受损最大的是公轮祭田,其后的是工商业者、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半地主式富农、富农。
“打击面”的户数为68户占总户数的5.3%;人口为368占总人口的7.3%。基本符合毛泽东关于新区土改的打击面的限制要求。没收征收537.5亩,其中征收的族田291.5亩,占54.2%。輦可见,族田的征收避免将打击面扩大,从而减小土改的阻力。
在土地分配中,66户雇农原占30.13亩,63户分到66.69亩,增幅达221.3%;215户贫农原占167.1亩,198户分到319.23亩,增幅达191%;228户中农原占571.806亩,86户分到140.
464亩,增幅达24.6%;187户手工业工人原占115.345亩,83户分到46.235亩,增幅达40%;132户商贩原占116.861亩,62户配到42.32亩,增幅达36.2%。受益最大的是雇农、贫农,其后的是手工业工人、商贩、中农,受惠面达72.1%。輦而这些阶层受惠主要源于族田的征收,因此,族田的征收增加了土改的动力。
(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族田征收的阶级选择性
1950年6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但在基层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族田都被征收。族田形式多样,有总祠、支祠、房等占有的族田,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并不同。
大公堂一般由大家推定或由地主阶级指定专人管理(以族长为多),小公堂一般由农民自己轮流管理。前者具有封建性,后者则不一定有封建性。关于中共的族田没收政策,应从族田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收益权的分离角度来理解。
“管公堂是一种剥削行为,但应分别地主、富农、资本家管公堂与工、农、贫民管公堂的不同。”“地主阶级及富农,借着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财产,成为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凡属这种为少数人把持操纵,有大量封建剥削收入的公堂,管理公堂的行为,当然是构成管理者阶级成份的一个因素。
但有些小公堂,为工农贫民群众轮流管理,剥削数量极小,则不能作为构成管理者阶级成份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而由农民阶级管理的族田则保留不变。
义序族田有总祠、支祠、房等占有的族田。总祠创立时没有祭田,至20世纪30年代,其祖产每年利息收入约三四百元。总祠祖产由族房长绅衿等管理,大部分用于祭祀,所余充为公用。可见,总祠的族田数量小,其收入基本上公用,但由于它是由地主乡绅管理,所以它被征收。
支祠和房的族田一般是轮流管理或耕种的。其中,四支祠祖产颇多,仅祭田一项约66亩,四房按序轮流耕种。輮由雇农、贫农、中农轮耕或管理的支祠、房的族田,保留不变。以1951年5月一区土改工作组的〈〈中心乡公轮祭田征收〉〉为例来说明:
宝钰家,轮祭田:单冬田13.8亩,占有者为2户地主、2户商人,故予全部征收。
慈钧家,轮祭田:双冬田1.8亩、单冬田4.8亩,菓地1.62亩,占有者为2户地主、1户中农。地主部分没收,中农部分保留。
可见,族田的征收并非一刀切都被征收,而是根据族田管理的阶级性进行有选择的征收。
(三)族田的征收: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
族田使祭祖有经济保障,而祭祖是宗族结构完善和运行正常的重要体现。赈济族人、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等也是族田的重要功能,如义序总祠的族产的用途除四时祭祀会餐之外,所余无多,或用于开浚浦道,或用于津贴赋税。輰四支祠的每年收入千余元,一部分纳入支祠,用为祭祀及其他公费,余润则归值年耕种子孙享受。
輧这样,族田的存在不仅可以敬宗收族,而且强化了宗族认同。但是随着族田的征收,宗族上述的功能丧失殆尽,可称之为宗族“去功能化”。
而宗族“去功能化”的过程也是国家“补功能”的过程。以〈〈中心乡1951年3月工作汇报〉〉为例来说明•拨款来自于国家,对象是贫苦农民,用途是购买生产资料、公共产品(见表2)。群众对国家发款感到非常满意和感激。如尚保三林嫂说:“不好生产对不起政府。”可见,国家救济取代宗族救济,促使了宗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
三、祠堂的征收: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
祠堂是宗族中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祠堂是宗族的标志,是全族立法、司法、行政的机关。义序有3个祠堂:1个总祠,2个支祠。1950年6月30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祠堂等得由当地政府管理,并充为公用。
訛因此,3个祠堂都被征收。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的“集合表象”被消解:首先摧毁了祭祖的场所;其次消解了族权行使的空间;最后转变了祠堂的功能。消解是指宗族整体性“表象”的肢解,但在这过程中却留下许多宗族碎片,特别在心理层面上宗族文化并不会随之而消失,仍起着潜在的宗族认同的作用。
当它受到某种剌激时,有可能爆发出巨大能量来。如1953年8月闽侯县十二区芹洲乡祠堂拟改做仓库,结果引发群众闹事案件,有人乘机煽动群众对抗工作组,直至县决定不做仓库时,群众情绪才基本安定下来。
土改后祠堂被征充公,区、县曾以为祠堂是国家财物可以随意处理,而“族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祠堂依然安放着祖宗神牌,所以在“族人”心里,祠堂依然是宗族的象征,是宗族认同的心理归属。
四、宗族内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
宗族之所以有强大的基层控制力,是在于宗族意识从血缘向地缘的延伸。因此消除宗族观念在基层政权上的延伸,是中共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其办法是灌输阶级意识,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宗法性定位转化为阶级性定位,明确划分阶级,将民众从宗族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不再以血缘认同自我的身份,而是以阶级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是,在宗族里,人们是根据血缘关系确定其社会位置,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宗族内部是不会自动地划分出阶级阵营来。
土改正是对宗族进行强干预下进行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将家庭从宗族中剥离出来,并纳入不同阶级阵营之中。通过“引苦”、“诉苦”、“论苦”,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分清阶级界限。以榴山乡土改中阶级形成过程为例来说明:
在土改中,急于求成,没充分发动群众,对地主阶级未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征收没收不够彻底。农民内部不团结,又增长了宗派的意识。地主阶级乘机反攻,不法地主黄春官盗卖没收石头百余块,并想将农民没收的木料百余根夺回,要干部给他作证明。
可见,在义序土改中,人们从宗族中剥离出来,纳入不同的阶级中。但是,阶级边界并不清晰,阶级意识未能形成,所以,阶级斗争无从开展。基于此,1951年6月4日到7月17日,进行了土改复査:
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民黄依保说:“黄永雪从来就没有劳动,抓桔虫挑土都是雇工,以前大家没提起,我也不敢说,现在我觉悟到,以前太傻瓜,他明明是地主,竞让他漏了,这次一定坚决地向他斗争。”检举了4户漏网地主。
他们以隐瞒土地、假分家、假劳动、隐瞒历史等,逃避农民的裁判。在群众伟大力量下,他们低头了,开了3次斗争会,斗了8个地主,参加的群众3670人。诉苦的有13人。哥俤诉黄葆祥地主为洲田股头,霸占洲田,每年每股可收十一二担,只给二三担,还说:“这是我照顾你。
”有一年哥俤病得要死,想卖洲田,但葆祥不让卖。哥俤记起以前所受的剥削,气得跳起来大叫:“你以前这样剥削我,今天你也有这样的下场,快把欠我的谷子还给我。”今天能够诉出心头的苦水,多亏解放军共产党。
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而是通过诉苦等表达技术来弥补阶级框架与乡村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輨。义序正是通过诉苦来激发阶级觉悟,但是,最初诉苦指向是停留在“生存伦理”,并未达到阶级意识高度。由个人的痛苦上升到阶级的痛苦是需要一个动员的过程訛。
因为在农民的价值标准里,居于首位的往往不是人们的政治立场,而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行訛。因此,在土改中,必须使农民的社会关系的判断由道德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并重塑乡村社会内部的话语輨:由最初“难以辨识阶级的概念”訛到阶级话语的转变,最终实现阶级斗争。义序漏网地主的检举正是基于:重塑昔曰的道德话语而转向阶级话语。
五、族权的瓦解:由祠堂会到农会的转变
(一)祠堂会:族权与政权、绅权、夫权的重叠性
在义序,15房的房长由房内男性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担任,在15房长内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担任族长。各房房长是族长主持的宗祠会议的当然成员,族长并无薪俸,但有特别的祭祖的权力。族权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通过辈分和年龄来体现。
血缘关系在维持宗族秩序上起重要作用,但事实上,财富和权力却起主导作用。“宗族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但在等级身份的划分标准上,血缘以外的财产因素却起到了重要作用。”族权只有与政权、绅权、夫权、财富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
主导义序宗族乡村秩序的有:年龄,没有年轻人可入祠堂会;身份,族房长是按自然递嬗方法产生;学识;武艺;世阶;性别,重视男权,女子不得参与祠政;财富,是最重要的一条,因有金钱,就有势力。可见,“宗族的实力,往往与其领导人的财富和地位成比例;最发达的宗族,是由有势力和富裕的士绅领袖所主持。这些绅士可以向宗族捐赠大量的土地,也可能为之开办学校、建义仓等,从而巩固族权。”
(二)族权瓦解的逻辑:族权与政权、绅权、夫权的重叠性的拆解
毛泽东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农民的四条绳索。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政权被打翻后,族权等便跟着动摇起来訛。先将政权、绅权、夫权和神权拆解开来,然后通过打击政权,使族权因失去了政权依托而被消解。
族权虽与政权紧密相连,但毕竟不是一种正式的国家权力,在族权的行使过程中,是非强制性,是温情脉脉的教化。族权的人格化代表即族长、祠长等由于年龄及社会阅历,他们的权威往往会得到族众的认同。輰因此,要消解族权,除了打击地主政权外,必须在宗族内植入阶级观念和进行阶级斗争;并结合族田、祠堂的征收及族谱的销毁以及农会、乡村政权的建设等。
(三)农会:传统型权威(族权)向法理型权威转变的桥梁
权力是指个人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但是权力并不等于权威,权威是得到社会认可的权力。根据权威的来源,马克斯•韦伯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靠风俗和伦理道德来统治;魅力型权威是建立在领袖和信仰基础上的;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科层制上。
至1951年7月,榴山乡农会迅速发展。会员从原346人增至976人(全乡5044人)占19.3%。经过土改复査整顿,农会领导管理层由中农与雇贫农主导转变为雇贫农主导:农会委员、干部原有雇贫农3人、中农9人,清洗掉雇贫农2人、中农9人,现有雇贫农18人(表3)。
农会的构建实现了乡村权力的转移:由地主乡绅掌握变为贫雇农掌握。“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1950年7月14日,《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规定:“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有关农会法规的出台使农会组织有了“科层制”特征。
族权属于传统型权威,因为族权是依靠伦理道德来统治。它的行使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而是有广大民众的心理认同。依靠族谱和宗祠内的祭祀活动,宗族会成为村落社会认同的基础。因此,族权能够维持宗族乡村的秩序。而构建在农会和乡村政权基础的权力本应是法理型权威,但是贫雇农通过农会而得到的权力是在国家强制力的干预下实现的,因此,这种权力未必得到众人的认可,即权力不能转化为权威,这使权力的获得和权力的行使效力并不统一。
如在中心乡,“农会的组织虽然成份历史上问题不大,但是太过于老实,不能领导群众对地主斗争,乡农会主任黄风营,他是中农成份,对地主、农民一样看待,人家外号叫做两面光。中山村分会主任黄国耳也是太过于老实,自己没有主张,容易被人掌握,做落后群众的俘虏。
”可见,虽然通过农会建设,族权转移给雇贫农,但是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农会是符合“科层制”特征,但是,雇贫农在农会中的主导权是在国家政权干涉下而获得,这种权力除了获得国家认可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众人的认可,包括权力获得者自身的认可,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