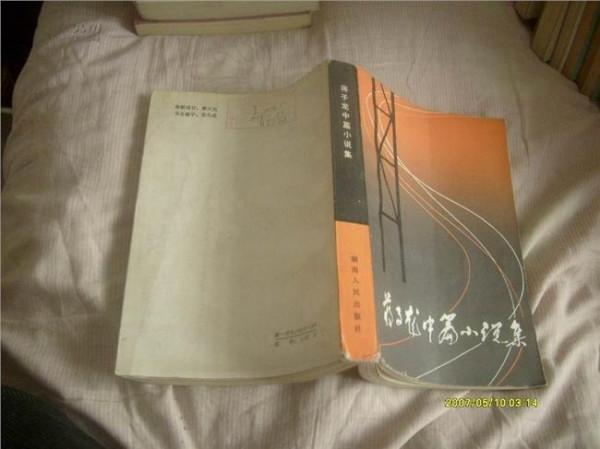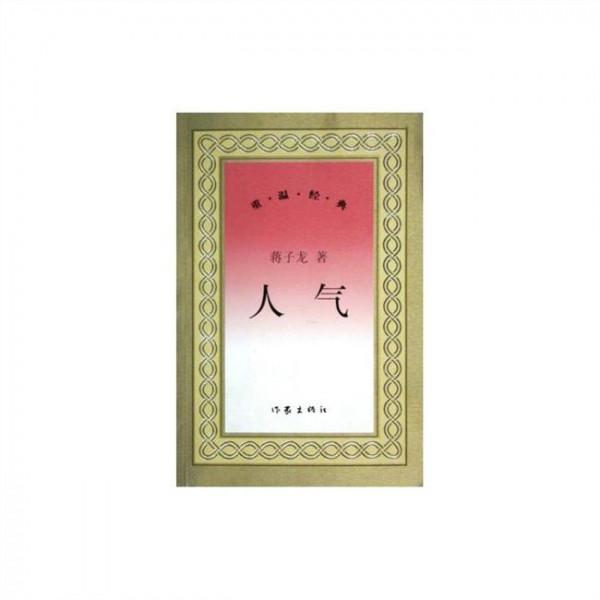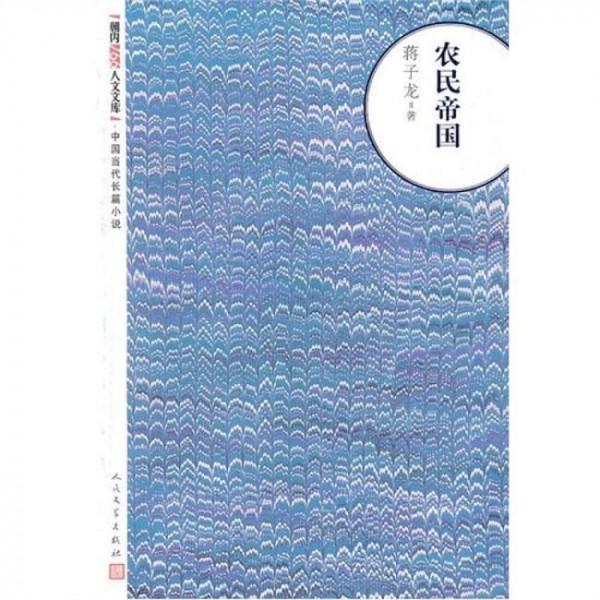蒋子龙收审记 灵魂安处是吾乡——记沧州籍著名作家蒋子龙
灵魂安处是吾乡——记沧州籍著名作家蒋子龙
沧州
人物档案:蒋子龙,沧县姚官屯乡窦店村人。做过工人、海军制图员、厂长秘书、车间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农民帝国》等,出版了十四卷《蒋子龙文集》,作品多次获奖,并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版本。
外表冷峻孤傲,内心古道热肠。4月1日,在沧州市图书馆负一楼报告厅,蒋子龙与家乡父老见面。75岁的老人魁梧高大,穿着朴素,头发斑白,精神矍铄。透过一副大框的金边眼镜,一双眼睛明亮犀利。说起话来,少有笑意,但时时幽默诙谐,言语洒脱,一口一个老乡们,很是亲切。
人们都说他有五种身份,丰富的阅历是他成功的基石。14岁之前,他生活在农村,是个地道的农民,运河边上有他金色的童年。14岁后,天津求学。之后当过兵,做过工人,最后却阴错阳差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身在城市几十年,他总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
他曾以工业题材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又在花甲之年以农民题材长篇轰动文坛。虽然作品中很少直接描绘家乡,但故乡就像梦一样永远跟随着他。他把那份深重的家乡情结,揉进了他的作品,用一串串的文字表达了对家乡的依恋。运河边长大的“调皮孩子”
从沧州走出去的人,心中总是离不开这条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蒋子龙也不例外,他记忆中的运河,银河盈盈,白帆点点,舟楫相济。沿岸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茂密树林,与这一脉碧波相约而行。蒋老说起的记忆,就是梦中的那片绿色。那是自然的绿,是满眼满心的绿,是赋予他生命的绿。
说起童年趣事,蒋子龙笑得像个孩子。他一边比画着,一边说起了和小伙伴们的“爬瓜记”。沧县窦店村位于运河东岸,夏日炎炎,大人们正在睡午觉,这正是小孩子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幼小的蒋子龙伙同几个小玩伴,从河东凫水到河西,因为那里有一片西瓜地。几个孩子见着大的西瓜就往怀里抱,没摘几个,就被看瓜的大爷发现,撒腿就跑。“大爷并没有追我们,只是吆喝了几嗓子,结果我们就跑掉了。”蒋老笑着说。
蒋子龙是沧州人,与武术也有不解之缘。家乡窦店以前有两个武场,孩子大人都去练武术,蒋子龙也喜欢。只是父亲一直认为他应该学文,不让他练武。“有一次,我偷偷溜出去,去了武场。被父亲发现后,用皮鞭打得我在地上打滚。
”蒋老摸着自己的胳膊,似乎现在还能感觉到当时的疼痛。他的同学们个个都练武,那时候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打架是必备的游戏,他就是在跟同学们的交手中学得了一招半式。就是这一招半式,让他曾经在天津上学时威震全班。
他说,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很少做城市梦,做了也记不住。进入梦境的几乎全是老家的景象。走上作家路“纯属巧合”
当时,蒋子龙的哥哥在天津工作。小学毕业后,蒋子龙被父亲送到了天津四十中学上初中。后来,他考上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上学期间,1960年他参军,并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毕业后任制图员。在这期间,他经常为部队文艺宣传队编写节目,锻炼了写作能力。1965年复员后,他到天津锻铸件厂,任厂长秘书。本来想一辈子当工人,阴错阳差成了作家。
走上写作这条路,蒋子龙笑称“纯属巧合”。他从初中开始对写东西感兴趣,不断往各处投稿。后来上了技术学校,学的是理工科,一直没专门学过中文。说起投稿,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初二时,蒋子龙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受到警告处分。
此后,他投给《天津日报》的稿子被退了回来。一位同学恶作剧地把退稿钉在墙上,还讽刺说:“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个作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这件事对蒋子龙刺激很大,挫败感转化成了写作的动力:“有点儿赌气似的,偏要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
写作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能写出一篇在当时社会上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不容易。蒋子龙感慨道,工厂环境很复杂,人事复杂,工作环境让人压抑。每天值班,只有听着巨大的机器轰鸣声才能入睡,否则心乱如麻。正是这样的环境,给了他无限的压力,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动力。
1979年,一篇《乔厂长上任记》轰动文坛。他用独特的笔法,揭露了现实,表达了心声。这样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不同声音,就像一道闪电,在中国文坛炸开了锅。伴随着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茅盾、冯牧等人的赞誉,各种批评文章也呼啸而来。
不服输的执拗性格却让他愈挫愈勇。“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我就在下班路上买一瓶啤酒,再买五角钱的火腿肠,当晚必创作一个短篇。”之后,他写出了《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大批优秀作品,蒋子龙,成了业界公认的工业题材作家。作品中的“沧州味儿”
为什么蒋子龙的作品中,没有专门书写沧州呢?这可能是每一个家乡人都有的疑惑。面对这个问题,蒋子龙说他不愿意回答,但必须要回答。
作家是带着犀利的眼神去审视和批判社会的,他的作品力求有时代的厚重感和幽默性,家乡是灵魂的归属地,他直言伤不起。但是仔细阅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几乎每部作品中都有沧州的影子。“比如《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电视机就是沧州牌的。哪有沧州牌电视啊,那是我想起了儿时农村一个村仅有的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大家围坐在村委会大院的老槐树下,看得不亦乐乎,其乐融融。”蒋子龙非常幽默地说。
2008年,蒋子龙出人意料地以一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再次冲击文坛。该书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以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钱、欲望、权力对人性的冲击。
这部作品的整个大背景即为沧州农村,字里行间,有批判更有依恋。他说,以前回老家就常常会感到陌生,童年时候的那个乡村,哪儿有个大水坑,哪儿有棵大树,全对不上号了。庄稼地,菜园子,围着菜园子有条小河,他在里面捉过蛤蟆,打过蛇,河边有几棵老枣树……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美好。而这一切都成了记忆。只有在写作的时候,这些记忆才又活了起来……
“《农民帝国》的写作,是我对家乡的感情太深了,几次在梦中遇见老乡们,坐在炕头上讲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所以这部作品是对社会的反思,更是情感的归宿。”蒋子龙说。作家的“灵魂”应一直行走
蒋子龙是一个厚重而幽默的人,他说作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写出的作品就容易缺筋骨,缺思想,缺行动。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的灵魂、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为了写《农民帝国》,他去农村很长时间,广东、河南、山东,还有天津周边的农村都去过。
到农村去,都是走单帮式的,最长的几个月。村里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就知道来了个老头,或者来了个亲戚,他要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他从来没拿过公家的介绍信,下农村是尽量将自己变成一个农村人,这就跟他童年的经历联系起来了。
蒋子龙讲《文学的精变》也是如此,引经据典,充满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一口的时尚词儿,从他口里说出来,是讽刺和幽默。他总是走在社会潮流的前列,从未落后过。30多年前,他就用电脑写文章,早早地开了邮箱、博客。现在他又玩起了微信,有些好的文章也会收藏通读。
当然他也有“守旧”的一面,他说家中的书房到现在还是木头窗户,儿子说给他换个断桥铝的,他说什么也不肯。“何为断桥?寓意不好。”现场大笑,细想起来,这是对文化的敏感性,对生活的执着,更是一种个性执拗的人生。
说起自己的书房,他笑道:“那是一个定期清理的书城。”他认为书有强大的征服和侵略性。他最怕搬家,因为搬家主要就是搬书。面对越搬越沉的一大堆书,搬家的人难免有些抱怨,蒋子龙就安慰他们:“俗话说‘字字千钧’,可见世界上最重的东西是文字。”新书、准备要看的书、看了一半的书、写作正用得着的书、有保存价值的书,占据了他房子的绝大部分空间,而且还不断扩展。
蒋子龙还喜欢扔书。他说书房里书最多的时候,从地板堆到了屋顶。人走路顺着中间劈开的羊肠小路,一步步转。每逢年终岁尾,清理书可
是个大工程。到那时候,他总是搬一个小板凳,往书堆里一坐,平时没有时间读的书,只有现在才真正塌下心来阅读,有时候一看就是一天,废寝忘食,完全沉迷于书中。
当然,生活中不只是书。他爱好广泛,最爱游泳。“游泳是我从小就学会的,运河水那么清凉,至今我还记得那种天然雨水的感觉。”蒋子龙说,从1989年他开始游泳直到现在已27年。如今还身手矫健、思维敏捷,游泳功不可没。
同样让蒋子龙感到惬意的还有集邮。当年写长篇小说《空洞》时曾遇到一个问题:国际防治肺结核病的标志为什么是一个双十字?请教医学专家,到网络上搜索,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均不得要领,最终还是在集邮册上找到了答案。
采访即将结束,蒋子龙重拾话题,说起了家乡和这条有着千年文化的大运河。他期待能为家乡作点贡献,能看到梦中那条绿色的长河。他说,他这辈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在百年之后,埋在父母身边,埋在生他养他的这片黄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