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海子的诗歌帝国
陈嘉映 中国大陆最具哲学思维的学者。1990年以《论名称》一文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喜欢诗歌的人都知道海子是谁。海子,1964年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查湾,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海子高蹈他的理想走了,留下我们在歌舞升平中消费一切,挥霍无度。可是仍然有一群怀念和追忆海子的人,他们每年3月26日都要在北大举行诗歌朗诵会来纪念海子。他们是社会上的诗人,校园中的诗人,他们曾经与海子并肩吟咏,或是受过海子诗风的影响,他们大多数仍然在坚持不懈地写诗。
我所见到的两次海子纪念诗会,全都门庭若市、座无虚席,可见喜欢诗歌、喜欢海子的普通同学相当之多。诗会是不要门票的,有节目主持人,首先朗诵的是海子的诗篇,然后诗人们纷纷上台宣读自己的近作,这些诗作中不乏优秀之作,不过整个的风格和氛围已经和海子那个时代相去甚远。80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时代,是海子的时代,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不用多说,你们就会知道,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
今年3月,除了开诗会纪念海子,北大戏剧社和北大五四文学社还联手推出了根据海子长诗《太阳?七部书》之《太阳?弑》改编的诗剧《太阳》。老实说,这出戏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显得比较晦涩,对于我们时代轻松的气氛来说显得有些凝重和做作,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演出。
《弑》的背景选在古巴比伦王国,一个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的王国。巴比伦国王是在一次革命或曰起义中登上王位的,他日益专横独断,不惜耗费半数巴比伦人的生命去修建太阳神庙,他原先的弟兄们(十二法王)重新揭竿而起,可是全部被巴比伦王擒获,处以极刑。
从沙漠上来了三个青年,有两个来刺杀国王并篡夺王位,有一个回故乡来寻找心爱的妻子。巴比伦王用诡计使两兄弟自相残杀,幸存的兄弟在皇宫中误杀了假扮成国王的公主,而这个公主正是两兄弟的心上人,因此杀人者自杀了。
另一个青年闯入宫殿,为死去的朋友和故乡的人民复仇,老巴比伦王告诉他,他其实是王子,而他的妻子,也就是公主,其实是他的亲妹妹。老国王已经服了毒药,他把权杖传给了这个青年,立他为国王。
青年(名叫宝剑)象古希腊悲剧人物俄狄浦斯一样挖瞎了自己的双眼,然后永远离开了巴比伦城。这时,农民们登场,他们歌颂粮食和丰收,他们问宝剑是为谁而牺牲的,一个农民回答说,宝剑是为我们而牺牲的,他接着说,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杀戮和鲜血,我们需要的是粮食与生活。在农民歌队的问答中,悲剧骤然结束。
就情节而论,《太阳》与传统的古希腊悲剧没多大区别,但是其表现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也就是说,戏剧并不按照自然时间组织情节,而是由一系列暧昧而神秘的片段暗示情节,在这些片段中,海子的诗句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整个戏剧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简单地说,它的风格是原始主义的。原始主义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追求和崇拜近乎迷狂的原始的力量。在哲学上与之对应的,是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以及一些流行的神话学理论,在音乐上,以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为典型,斯氏的《春之祭》表现了一个少女被选中做牺牲的祭品、最后狂舞至死的过程。
有人认为,在政治上,与之对应的是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张扬的“血和土地”。不幸的是,《太阳?弑》的核心理念就是“血和土地”;不过令我们快慰的是,海子在政治理念上与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海子在中后期创作中迷恋神话、迷恋原始主义,这一倾向也是80年代流行的倾向之一。《太阳》一剧动用了三个神话原型,其一是:大地生养儿女却又吃掉他(她)们,生(春)与死(冬)是土地的两种原始力量;其二是:要用少男少女的鲜血来祭神(如太阳神)才能换来种族生存的权利;其三是:杀父娶母或兄弟姊妹乱伦。
在《太阳》剧中,这三种神话结构象不详的命运一样笼罩着整个巴比伦。海子似乎是想通过这种宿命来影射中国以及诗人们的命运。
中国是农耕社会,土地是中国人的根,土地给人们粮食,也给人们造成灾难;中国的历史总是由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杀戮与流血充斥着整个古代史(在《太阳》中,造反的十二反王之一叫“闯王”,这无疑影射着中国的历史)。
杀戮和流血在海子诗歌中的对位意象是太阳、红、花朵等等,海子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值得谴责和否定的东西,相反,他用酒神般的迷狂热切地歌颂太阳、红、花朵、鲜血和杀戮,可能在他看来,这正是生命力之所在,是大地上劳作的人的宿命。太阳,作为热与力以及生命的中心,承载着海子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诗人”,在海子眼中,无疑是“英雄”、“精英”的同义词,所谓英雄,通俗地说,就是那些能领导大众改变历史的人。英雄与大众这对二元概念无疑是整个80年代启蒙话语中最张扬的东西。诗人们在80年代的任务不是消遣,而是启蒙与革命。
当然,这是80年代的诗人们一厢情愿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在《太阳》一剧的节目单上印着海子的这么一段话:“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个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观啊?!象所有冲动的浪漫主义者那样,放眼民族和人类的海子也把过多的任务加在诗歌和自己的头上。
18世纪的启蒙本来是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随后的革命却和非理性越走越近。从五四运动到80年代的启蒙运动,其实既不“科学”也不“理性”,象黄河那样泛滥在学术界、文艺界的不过是“非理性”而已。
革命固然是群众的节日,是满腹怨气的人舒心畅气的日子,可是革命运用的手段和革命允诺的千年王国却是值得怀疑的。诗人们在革命的狂想曲中显得格外冲动,他们最容易把自己幻想成全民族的救主。诗人和所有文人一样,又是极端虚弱无力的,于是在他们革命的头脑中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呼声:我注定要牺牲自己,成为时代的祭品。
这一呼声与其给他们带来了狂喜与希望,不如说给他们带来了无边的痛苦与绝望。在“我注定要牺牲自己”的呼声下隐藏着他们对自身命运的预感:原来,一切行动全是无意义的,是没有结果的。
但是浪漫主义诗人们固执地象春天里的花朵那样开放。他们绽放的方式是把诗歌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宏大、越来越气势磅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作为虔诚的诗人,他们的革命行动只能是诗歌创作,他们想创造出具有魔法力量的“原诗”。
他们认为诗歌在本质上属于原始力量,于是他们走向原始社会、走向神话,企图从神话那里借来圣水与圣杯。T.S.艾略特无疑是他们的榜样之一,然而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留下来的神话屈指可数,而且缺乏鸿篇巨制。
不过,没关系,他们从异乡借来了神话原型,他们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幽暗的巴比伦王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出神话来。诗歌本来就适合创造任何可能世界,诗歌就象上帝,能够从无创造出有。于是有了海子象阿房宫一样的《太阳》。
其实,海子早在抒情年代就有了预谋。村庄、土地、庄稼、太阳等意象反复出现,逐渐构造出一套完整的象征体系,或者说诗歌帝国。海子是端坐在帝国中央孤独的国王,他象老巴比伦国王一样寂寞、孤独、“不被人理解”。“不被人理解”是英雄的浪漫主义者生而有之的想法,连反对感伤浪漫主义的尼采也是因此而加重了病症。
虚无主义其实不是世纪的、人类的疾病,而是尼采之类浪漫主义诗人的疾病。他们在想象的牺牲中发出了象基督耶稣一样的呼喊:“上帝啊,你为什么抛弃我?!
”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耶稣对待暴力、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们对“力量”高唱起赞歌来。雄性激素在诗歌里大量泌于是在80年代,诗人成了最繁忙的情书阅读者,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有少女们充满爱情的眼睛。
不过,诗人在歌颂永恒女性的同时,似乎也被女人们的善良天性感动了,于是在《太阳》中,王子“宝剑”(也即诗人自己)首先不是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而是以一个寻找亲人、寻找生命的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无知的”、总是关注鸡毛蒜皮的女性总是在拯救浪漫诗人。浪漫诗人总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女性身上找到“永恒女性的美”,然后又总是假装失望,弃她而去,另觅新欢。最后,在一次仪式性的自杀中(原始主义最为关注的是神秘的仪式),诗人逃避了所有可能的道德谴责,在永恒女性的引领下升入天国。
在《太阳》一剧中,宝剑寻找的亲人、妻子,由一位身穿洁白衣服、跳着优雅舞蹈的美丽女性扮演,是她使全剧阴沉的、血腥的气味稍微减轻。
在此,我无意于影射海子。关于海子的生活和海子的自杀,我了解得很少。我只是在描绘一幅浪漫主义诗人的画像,这幅画像有可能象很多人,但又不象任何人。不管怎样,这幅画像中的那个“人”,随着海子的自杀,也就病入膏肓,在一次不动声色的消费热潮中悄然死去。
留下的,是没有帝王的“诗歌帝国”(这个词在《太阳》一剧中多次出现);就象秦始皇死后留下万里长城――甚而,并没有一块秦砖留在今天的长城上。作品完成,作者退隐,这就象海螺死去留下贝壳一样自然而然。人的精神永远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人的肉体却永远是渺小的,如同在《太阳》一剧中歌唱的那样,他注定象谷子的壳被大石头碾去。
《太阳》或许隐藏着某种政治冲动,但占上峰的却是艺术冲动;在诗剧结尾农夫们的合唱中,诗人对自身的怀疑连同“理性”一起唯一一次微弱地闪耀了一下,随即退身隐入诗歌帝国。《太阳》就象巴比伦的太阳神庙一样,精巧、牢固、充满了魔力。
诗歌帝国建造起来了,在帝国的宫殿中,巨大的魔力使一切的人与物都沉睡在宫殿的里面,使他们永远无法走出暗红色的宫门;巨大的魔力圈同时拒斥了现实世界(包括政治)耀眼的阳光,在魔法的保佑下,幽暗的宫殿里的陈设依然如旧,就象皇帝还在的时候那样。一个人能在时光无情的流逝中修建起这样一座宫殿,无论如何是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全文共有3925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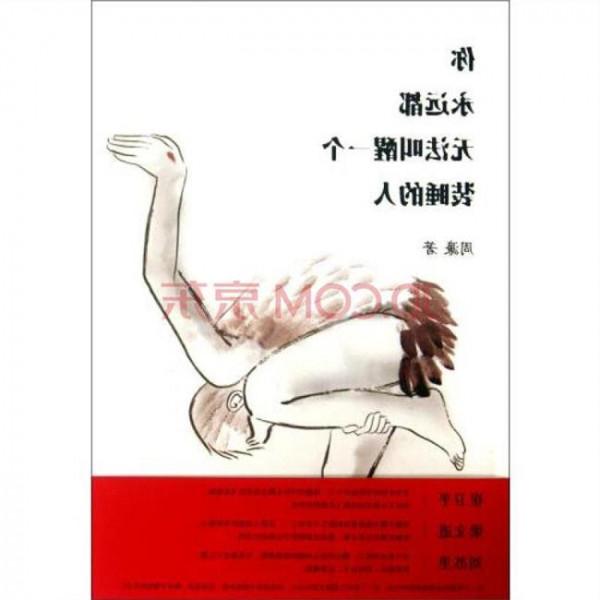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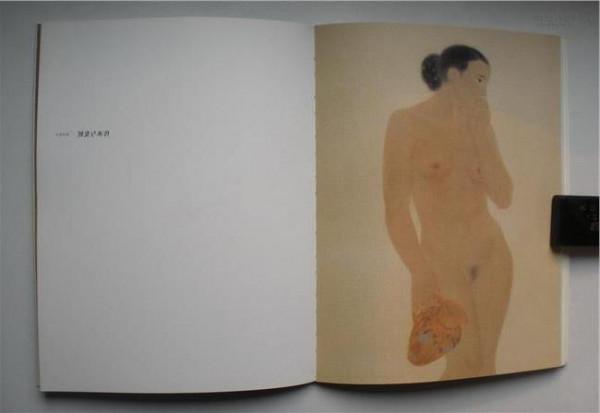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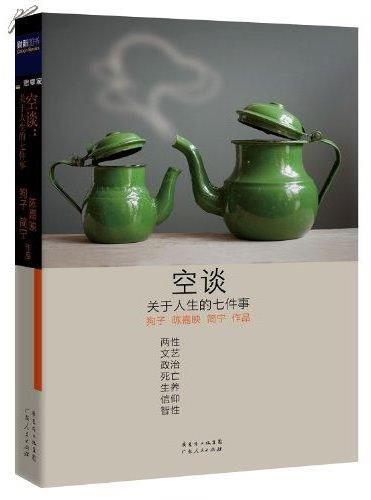

![>陈嘉映]陈嘉映 周国平](https://pic.bilezu.com/upload/0/72/0725457507eb935c5e97395ded42714c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