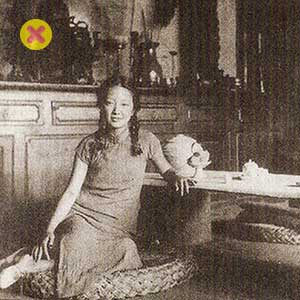张充和《一曲微茫》 Vol 969《一曲微茫度此生 致张充和》
生命,这点微尘,一如音乐的织体一样,在急管繁弦中透现生机生意,在山重水复间见出天地豁朗,又在空疏素淡中,味尽恒常的坚韧,寂默的丰富,以及沉潜慎独的绵远悠长啊。她用诗词、书法、绘画、昆曲和旗袍抒写了她多姿多彩的一生,绝非虚言。按她自己的诗,即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了。她是张充和。
编辑:汪汪
主播:陈树
后期:贝勒爷
提到民国闺秀,一般人会想到宋氏三姐妹,颜值高,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深远。如果说政治是百年国史的一根明线,文化则是一根影响更大却不彰显的暗线,其中合肥四姐妹的影响,当远不止于八卦,颜值亦毫不逊色。
叶圣陶说过这么一句,“九如巷张家的四个女孩,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生世显赫,曾祖辈为淮军名将张树声,但四姐妹一生远离政治,全部嫁给了文艺界大咖:大姐张元和,与小生名角顾传玠恋爱而结为伉俪,后旅居美国;二姐张允和,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夫人,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三姐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沈从文的名句“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四姐张充和(小妹),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傅汉思教授的夫人。
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擅昆曲,能作诗,善书法,会丹青,“琴棋书画”皆精。
1914年闰五月二十日,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别墅里,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 母亲陆英见是女儿,颇为失望,在这之前,她已有了三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她谨切地盼着能为丈夫张冀牗生一个儿子。可惜,她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
父亲张冀牗是极开明的人,他深受新风潮的影响,对待女儿和儿子远没有时人那么泾渭分明。他为这刚出生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充和。同她的三个姐姐一样,充和的名字里也有“两条腿”,他希望女儿们不要再困守在闺房里,都能走得更高更远。不过那时候他没想到,这个最小的女儿会走到地球另一边。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充和的学问根基更扎实,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在出生11个月后,充和被过继给了叔祖母识修,她是李鸿章的四弟之女,但识修并不是有福的人,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悉数早亡,大悲大恸之后,她开始向佛祖寻求慰藉。充和的到来,像一道阳光照亮了叔祖母识修寂寞的晚年。识修祖母对小充和关爱有加,自任启蒙老师,言传身教大家闺秀的风范,一心一意想把她培养成名门淑女。
她严格地为充和挑选老师,花重金延请吴昌硕的高足、考古学家朱谟钦为塾师,悉心栽培她,还另请前清举人左先生专教她吟诗填词。张充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4岁会背诗,6岁识字,能诵《三字经》、《千字文》。
从六岁到十六岁,充和每天都在书房呆足八个钟点,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只有一个钟头的午餐时间,每隔十天,她才有半天休息。她的课本有《汉书》《史记》《左传》,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跟着博学的先生,充和熟读了中国的经典。 如是10年,闭门苦读。充和晚年一直铭感这两位恩师为她奠定了国学的功底。
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合肥张家的深宅大院里静静地长大,没有同龄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耍,没有母亲的娇宠疼爱,她跟着庄严肃穆的祖母,养成了清冷的性情。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
这些情形让她形成了她自己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形成了她宁静的气质,养成了她学者的习气,她成长的十年间,一战,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整个中国都在急剧地变化,而她的世界却始终如一,一册古书,一支毛笔,遗世而独立。
1930年养祖母告别人世后,16岁的充和“归宗”回到苏州,承欢在父亲的膝下,与姐妹们共同生活。在父亲创办的乐益女校上学,乐益女校由父亲张冀牗独资创办,张闻天,柳亚子和叶圣陶都任教于此。
重回家人身边后,充和很快便发现了,她远没有三个姐姐“摩登”,她不懂“科学”与“民主”,加入不了她们高谈阔论的圈,姐弟几个一起踢球的时候,她不懂规则,只能做守门员,她的姐姐们都是西式教育下的民国小姐,而她却像晚清的闺秀,不喜嬉闹,不愿出头,静默地读书,习字,写文。
下了课,她总喜欢呆在藏书楼里,那儿很静,有数以千计的书卷,她在那些故纸堆里翻到过《桃花扇》《紫钗记》还有《牡丹亭》。她很爱读这些,尤其是《牡丹亭》,她独自坐在藏书楼里,孤零零读着“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似这般都付于断壁残垣”,窗外高高的院墙上有一道深黑的裂缝,她似乎懂得杜丽娘深闺的寂寥。
父亲是位昆曲迷,常请曲家到家中教女儿们拍曲,在父亲的影响下,四姐妹成立了幔亭曲社。她与长姐元和同演一出《惊梦》,她饰杜丽娘,而长姊是柳梦梅。当杜丽娘在台上徐徐甩开一抹水袖,柳梦梅一个折身一个回眸,悠悠唱开“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藏书楼里的《牡丹亭》仿佛活转过来,在她面前徐徐展开一个绮丽的世界。
幼年时对昆曲萌生的一点兴趣,至此蓬勃生发,她说“我总是能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从此,昆曲雅正的“水磨腔”悠悠伴随了她一生。
从少女时代起,她便在情感上显出清洁的理性,她不喜一个人时,她是冷漠的,而她喜欢一个人时,便极为温和亲善,她的喜与不喜,泾渭分明。
十九岁那年,她去北平参加三姐兆和和沈从文的婚礼。张充和小时候是与弟弟们一道听沈二哥讲故事长大的。沈从文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呵护着她。她很钦佩这个只有小学文凭却能写一笔好文章的姐夫,亲切地叫他“沈二哥”。在沈从文访美的时候,她用西洋式的礼节吻他的头,沈从文去世的时候,她写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她隽永的书法与这段话相得益彰,被公认为对沈从文一生最好的概括。
家人劝她报考北大。她想不妨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北大的入学考试需要考四科,国文,历史,数学,英文。她没学过数学,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学英文也刚刚两年。用了“张旋”的化名报考,沈从文那时在北大任教,她不想沾光,避嫌。
沈从文和张兆和都劝她补习一年再考。可她淡淡一笑,不改初衷。成绩出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斐然,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充和后来说,作文是她面壁虚构的)。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看到她的作文,便说:“这学生我要了!”,当时北大有规定“任何一科是零分,都不能录取”,可她因为国文成绩优异,最终被破格录取。
但她只呆了三年便患病休学,朋友们都很惋惜,胡适还专门找到她,劝她不要放弃。 可她自己似乎不在乎,考入北大时,她也只说是“糊里糊涂便进了”,出了北大,她也不觉得多遗憾。尽管当时有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可她却觉得北大的气氛并不适合她,不是一个能叫人静下心来读书的地方。
她对激烈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更乐意将时间花在她喜欢的昆曲上。小她一岁的弟弟宗和在清华读书,她常去清华,与弟弟一道去聆听一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的讲座,期期不落,还不时参加曲友们的演出活动。
在苏州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之后,她去了南京《中央日报》,担任副刊《贡献》的编辑,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初露才华。 1937年,抗战爆发,她随三姐兆和一家流寓西南,在昆明,沈从文帮她在教育部属下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
战乱中条件艰难,充和寄居在姐姐家中,房间极小,她并不挑剔物质的匮乏,唯一挑剔的是笔墨纸砚,她说:“我不爱金银珠宝,但纸和笔都要最好的。”
张充和端庄、大方又热情,很有人缘,在人才云集的西南科教界,她广结师友、见贤思齐。流亡生活并没有湮没她的艺术光华,她的昆曲唱得愈发好了,当时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汪曾琪听过她的演唱,“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一年后教科书编选单位解散,她在重庆教育部下属礼乐馆工作。她将整理出来的24篇礼乐用毛笔书写,首次展示了她的书法艺术,隽永书法惊艳众人,也就是在那时,她结识了书法家沈尹默,沈先生头一次见她写字,便说她的字是“明人学晋人书”,将她收入门下。
她很用功,搭运煤的车子去歌乐山求教,不去老师家时,她也会把诗词书画作业邮寄老师审批圈改,沈先生教她写字要“掌竖腕平”,于是她每天花三个小时临帖,雷打不动,练到后来,她的臂力足够她双手撑起身体悬空而走,到老了,“她的手臂还和少女时代一样有力。”
她的书法为她赢得过很多赞誉,后来,她被称为“当世小楷第一人”,文学家董桥称她的“毛笔小楷漂亮得可下酒,难得极了”,他不仅多次写文赞誉她,还四处收藏她的字,说:“张充和的工楷小字秀慧的笔势孕育温存的学养,集字成篇,流露的又是乌衣巷口三分寂寥的芳菲。
” 书法家欧阳中石曾点评她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家,而是一位学者。无论字、画、诗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难得。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格调极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没有改动过的。书法上的行书、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极雅,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
梁实秋赞她:“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多才多艺,由我出面邀请,会同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合演一出《刺虎》,唱做之佳,至今令人不能忘。”在重庆,她主演的一曲《游园惊梦》轰动了整个文化界,她应邀去张大千家聚会,一曲《思凡》让张大千大加赞赏,画了两幅小品为赠。 一为仕女持扇立芭蕉下背影,暗寓她演戏时之神态。一为水仙花,象征她演《思凡》时之身段。均题上款曰“充和大家”。
可她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淡淡笑道:“我一辈子都是玩儿”,她对别人的赞誉一直抱着一种淡漠的态度,在她身上,始终有着童年时代熏陶出的闺秀气质,把琴棋书画视为必要的修养,不会恃才自傲,在铺天盖地的赞赏面前态度端然。
她根本无意成为书法家,文学家或是昆曲名角,书法,诗文,昆曲……只是与生俱来,她走到哪都带一本字帖,即使空袭警报拉响,她仍在不停书写,“防空洞就在我桌子旁边,空袭警报拉响后,人随时可以下去。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就练习小楷。”艺术让她内心平静,她不在乎那些艺术家的虚名。
她的诗词“词旨清新,无纤毫俗尘”,流亡时期,她写过一首词叫《桃花鱼》,写的是重庆嘉陵江中的一种状如桃花的水母,她这么写:
《桃花鱼一》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桃花鱼二》散尽悬珠千点泪,恍如梦印平沙。轻裾不碍夕阳斜。相逢仍薄影,灿灿映飞霞。海上风光输海底,此心浩荡无涯。肯将雾谷拽萍芽,最难沧海意,递与路旁花。
她借这微小生灵写她对爱情的态度,抗战时期,她的词句并没有因烽烟战火而变得粗粝,仍然雅致空灵,这两首词被公认为她最好的诗。
章士钊很欣赏充和,他在赠充和的诗中写道: “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他虽把她比作旷世才女蔡文姬,可是她极为不悦,认为“拟于不伦”,她说,蔡文姬被掳至胡地,不得不倚仗异族过活,而她虽因战乱背井离乡,却始终自食其力,竭尽所能。
她是世家的女儿,不是那经得起富贵挨不得穷的浅薄女子,幽兰生于空谷,亦有清芬,再艰难的环境里,她也自有她的优雅。不过多年后,她不禁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那是1947年战争结束后,她回到北平,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结识了一个叫傅汉斯的男子,次年,她嫁给了他——一个西方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与她的热爱毫不相关的地方。
傅汉斯是德裔美国人,出身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来到中国学习汉学。在北大,他结识了沈从文,常来沈家和沈从文的两个孩子玩,而充和那时也居住在姐姐姐夫家中,他们渐渐熟悉起来,在充和的建议下,他把他的名字里面的“斯”文的斯改为了相思的“思”,孩子们留意到了他们关系的转变,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淘气地喊“四姨傅伯伯”,故意把句断得让人听不明白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她淡淡地笑,没有介意。
充和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言谈举止都是国学的底子,从姑苏烟雨中着一袭旗袍娉婷走出,而他却是在美国加州的阳光下长大刚刚开始涉猎中国文化的西方男子。她对他能产生好感,让人不由不好奇。
在重庆岁月,才貌双全的张充和尚待字闺中,石榴裙下尾着一批追求者。用情最专最深的当数诗人卞之琳。这个新派诗人给张充和写了不少诗歌,包括那首最著名的《断章》。可张充和无意于他,她感到卞氏人是好人,但“不够深沉”,故对其总是冷淡、疏远。别人撮合他们时,她生气得离家出走。“情到深处天尤怨”,诗人太钟情了,一生都对她不能忘情,却终归只是“装饰了她的窗子”,而她却“装饰了别人的梦”。
还有一位姓方的男子也喜欢她,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总给她写信,全用甲骨文写,一写好几页纸,她看不懂,也无意去弄懂。她回忆起他时,说“每次他来,总是带着本书,我请他坐,他不坐,请他喝茶,他也不要,就在我房里站着读书,然后告别,结果我俩各据一方,他埋头苦读,我练习书法,几乎不交一语。”
她把这些追求者都拒了,在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着类似的特点,沉默,木讷,有着中国文人惯有的腼腆,可是她却全然不喜欢那样拖泥带水的爱情,她长大的过程中母亲是缺席的,使得她无法适应阴柔的“欲说还休”的情感表达方式,而傅汉思那种西方式的直接与热情,最终打动了她的心。
1948年11月19日,他们举行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婚礼,有美国基督教的牧师和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副领事到场证婚,沈从文、金隄担任介绍人,由于傅汉思的父母远在美国,杨振声教授代表男方傅汉思的家属参加,而女方那边来了三姐兆和,沈家的孩子小龙小虎,两个堂兄弟和几个好友,连牧师夫妇,宾客一共14人。
仪式虽是基督教的,可两个人也依照中国惯例,在结婚证书上郑重其事盖了章。
三天后,他在给父母的家书里写:“我们前天结婚了,非常快乐。”
两个月后,她随他赴美,永久地离开了中国。 他们先定居在加州的伯克利,后来又移居到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傅汉斯入了耶鲁大家教授中国诗词,而她去了耶鲁大学讲授中国书法和昆曲。
她决意要在耶鲁将中国文化传扬开来,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美国学生把中国书法当成画画,对昆曲唱的什么故事都弄不清楚,但她并不灰心。 没有笛师,她便先将笛音录好,备唱时放送,没有搭档,她培养自己的小小女儿,用陈皮梅“引诱”她跟自己学昆曲。母女二人身着旗袍登台演出,母亲清丽雅致,混血儿的女儿可爱如洋娃娃,悠悠的笛声和唱词一起,就算再不懂中国文化的学生亦为之陶醉。
她的努力,渐渐积水成河,许多年后,她播下的昆曲种子终于发芽,她的四位高徒,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1年的时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的“明轩”落成,邀请她前往参加《金瓶梅》雅集。她欣然前往,在那仿苏州园林式的亭台楼阁中,以笛子伴奏的南曲方式,演唱《金瓶梅》各回里的曲辞。
那日她穿了一袭暗色旗袍,“素雅玲珑,并无半点浓妆,说笑自如”,一直唱到《罗江怨》的“四梦八空”,最后以一曲《孽海记》中的《山坡羊》收篇,她的声音婉转低回间又有几分苍凉清冷,映着明轩的亭台水榭,翠竹松石,叫人心神皆醉。
如雷的掌声,她让西方人认识到了东方的美。
娶了她这样的妻子,傅汉思也在中国文化研究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参加了中国《二十四史》的英译工作,为德国版的《世界历史》撰写了中国中古史,他还和她合作完成了《书谱》,大院里学北平话的西方年轻男子,成长为了有名的汉学家,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
再回国已是许多年后,1986年,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年的纪念活动上,她和大姐元和合唱演了一曲《游园惊梦》, 她已是古稀老人,可她的剧照被俞平伯称为“最蕴藉的一张”。
二十年后,她回苏州,穿一袭绛红丝绒旗袍,披一条黑色丝巾出来唱曲,往雕花栏杆边一倚,仍是仪态万千,那种端方秀雅,在现在年轻的女孩子身上再难寻觅。
2004年她的书画展和一系列关于她的书的出版,让“张充和”这名字突然被大众熟知,琴棋书画,随意天涯,这样的人已经在这个时代消贻殆尽,无数人感慨她身上大家闺秀的气质,连带着怀念她所代表的那些女子,已经离开的宋氏姐妹,林徽因,冰心……。
她在大洋彼岸看到那些扑天盖地的赞誉,只是淡淡一笑。那时,她正静静坐在自家的竹林里,教一个叫薄英的美国人如何沏茶,高冲,低泡,分茶,敬茶,她熟练地演示着沏茶的每一道工序,她喜欢喝茶,一直沿用在苏州老宅时的泡法,滚水冲泡,方能品到天然本真的原味。
这个叫薄英的男子帮她出版诗集的人,他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星期,她和傅汉思选目,一共有十八首,她用小楷重新抄写了一遍,傅汉思和薄英一起逐字逐句地翻译了出来,诗集起名为《桃花鱼》,每一本都是薄英手印并亲手装订成书,一百四十部书耗时整整三年。书的封面是木制的,分别用了印度紫檀、阿拉斯加雪杉和产自非洲的沙比利木,即使不看文字和书法,每一本书也能单看作艺术品。
她总是固执的,隔了这么多年,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她还保留着骨子里的中国情调,穿旗袍,每日临帖三个小时,在她那西式的花园里,一侧种着北美人家最常见的玫瑰花,一侧却种着牡丹和竹——两种中国画家笔下最常见的植物。
即使远在异国,她也不曾改过她大家闺秀的气派。
在汉民去世后,年逾九旬的充和在全心整理汉思遗著的同时,坚持在砚田边耕耘。她的另一门功课是经营她寓所门前的小院。院内花木扶疏,除育观赏的牡丹玫瑰外,还植一些食用的葱蒜时蔬。侍弄花草,栽瓜种豆。劳作之余,依在竹林旁的长木椅上吟诗或听曲,颐养天年。充和以一首园牧歌式的清雅小诗,抒发她时下的心境:
当年还胜到天涯,随缘遣岁华。雅俗但求生意足,邻翁来赏隔篱瓜。
丁亥清明时节
24岁时,她为自己编一本《曲人鸿爪》,收集各方昆曲名家、学士才人的即兴书画。张充和的继母韦均一工书画,擅昆曲,年长充和十五岁,两人常在一起练习唱曲、绘画。
1956年秋天,胡适先生在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客座,也在《曲人鸿爪》册页里写下元代曲家贯酸斋所著《清江引》: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张大千早年也曾在《曲人鸿爪》中赠她画作两幅,以形状张充和《思凡》身段。
可以想象,上个世纪中叶,张充和的生活风花雪月,海棠结社,多么繁华。
她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活里,没有大的波澜和惊险,也没有被改造和异化。她的天性——艺术感,本身就是人性中最本真的部分——保存完好,而常人的艺术知觉早在粗糙生活或者自我修整中磨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昆曲和书法,是她的一生知己。她似乎一直活在忠孝节烈、才子佳人的故事里,活在虚构与韵美里。她在新的世纪,还延续着少年时代读诗、习字、吹笛、唱曲的苏州岁月。她家中衣橱里,挂满风姿妖娆、长短各异的旗袍。
她果然“独在异乡为异客”了。她是一棵临渊的静树,旁边是深潭的水,深不见底。她走了以后,她的《曲人鸿爪》中的主角们,正在渊里挣扎和沉落。
她为什么要远走他乡?如果她选择留下她会怎样?如果那时候她没有嫁给傅汉思,如果那时候她没有离开中国,她还能完整的保留她自己么?她的亲人和朋友都没有逃过文革,三姐夫沈从文濒临精神崩溃,老师沈尹默销毁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和多年收藏的书法珍品后还是没有逃脱被迫害致死的命运。在“革命”的中国,是否能容下她的琴棋书画,容下她对政治的清冷疏离?
1948年,她还没有预见这些事情。她只是觉得自己喜欢的那个世界风韵犹存。但是新世界对她来说是黯淡的、陌生的,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甚至连梦想那些东西的空间都没有。她觉得,应该让那些“弹性大,适应性强”的人留下,她只是从祖母那里学到了慈悲,也知道了一切为善之道。
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她离开得正是时候,她的丈夫,这来自美国加州的男子把加州的阳光也带给她,她可以在阳光下自由地生活,保留她生命中的美好与诗意。 即使在西方,她也不曾改变过,而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努力溶入她雅致清冷的东方世界。
2011年04月,在中国昆曲博物馆举行的张充和昆曲珍藏捐赠仪式上,来自纽约的海外昆曲社社长陈安娜转交张充和的捐赠物品时表示:“充和老师说,要把最好的珍藏留给故土,留给懂得珍惜的人。”
当时99岁高龄的张充和虽远在美国,却一直心系故土。她所捐赠的昆曲珍藏中,既有早年她演唱昆曲《游园》所用过的一领斗篷,也有她在1991年手抄的昆曲曲谱,此外还有一副珍贵的点翠昆曲头面。这三样珍藏品在捐赠仪式上一经亮相,让台下坐着的昆曲曲友们赞叹不已。
其实早在2003年昆博开馆之初,旅居美国的张氏姐妹就曾对昆博馆藏品的征集工作给予鼎力支持。张充和已先后两次向昆博捐赠所藏昆曲资料,进一步丰富了昆博的馆藏。
她是一位时光的代言者,她的故事就是这乐音乐言的本身。也许,对于她,弹奏华彩乐段的右手,已经换成了左手——记忆成了生活的主体,现实反而成了记忆的衬托?其实,人生,在不同的阶段,记忆和现实,黑键和白键,就是这样互相引领着,互相交替、互为因果的叠写着,滚动着,流淌着——有高潮,有低回,有快板中板,也有慢板和停顿……所以,生命,这点微尘,才会一如音乐的织体一样,在急管繁弦中透现生机生意,在山重水复间见出天地豁朗,又在空疏素淡中,味尽恒常的坚韧,寂默的丰富,以及沉潜慎独的绵远悠长啊。
她用诗词、书法、绘画、昆曲和旗袍抒写了她多姿多彩的一生,绝非虚言。
按她自己的诗,即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了。(2015年6月18日凌晨一点,张充和以102岁高龄辞世,谨以此文缅怀张充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