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普世宗教与特殊宗教——财新文化
作者: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普世宗教与特殊宗教——一个教外人读汉斯·昆的《什么是真正的宗教》
本文选自财新图书《价值的理由》(中信出版社,2012)
程颢说王安石谈道是在塔外“说十三级上相轮”,不能“直入塔中,上寻相轮”。吾侪教外人说宗教,难免被这样批评。
但我是教外人吗?有时碰到人问,你是基督教徒吗?我说不是;不觉得别扭。他接着问,你是无神论者?我说是;却有点儿别扭。倒不是这个回答的真值不够确定,而是这个回答好像有一层否认神的存在的意思。A-theism,即“无神论者”,无论从构词上说还是从历史上说,都带有点儿积极否定,甚至挑战、挑衅的味道,“战斗的无神论者”的味道。
我是个男人,而不是个非女人,更不是个misogynist(厌恶女人的人)。在“头上三尺有神明”的意义上,在“叫它幸福!心!爱!神!我对此却无名可名!”(歌德,《浮士德》)的意义上,我并不是“无神论者”。
我的确不是基督徒。基督教只是宗教中的一种,此外还有伊斯兰教、佛教、萨满教、罗马国教、青阳教,数不胜数。它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你有宗教信仰吗?我若回答,有,我信青阳教,那会是一个蛮奇怪的回答。基督教历时两千年,上有教皇,凌驾于君王之上,下有遍布世界的教徒,中有神学博士,神学著作汗牛充栋;青阳教屈居民间,信众(我顺口就说“信众”而没说“教徒”)只有少数“愚夫愚妇”,没有百十年就湮灭了。
虽然辞典不得不为“宗教”一词提供一个统一的释义,但似乎不如说各种宗教之间最多只有家族相似。
除了字典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少有谁从宗教的共同本质想到宗教说到宗教,总是从一两种典型的宗教想起说起。我猜想,即使字典学家和社会学家谈论宗教的本质,通常也是从一种或几种典型的宗教着眼,然后逐步扩展开来,而不是把所有宗教摆到眼前,从中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点——尚未确定何为宗教的本质,又怎么决定该把什么摆到眼前,例如,是否该把儒教摆到眼前?
所谓典型或原型,多半是那些世界宗教;那些限于一个小部落、一小群人的宗教,历时不久的宗教,别人不知道,很难起到典型的作用。各宗教的神祇本来都是民族性、地方性的,只有几种宗教转变为世界宗教,数其大者,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已。
(印度教信众虽多,但差不多只有印度人信。)今天关于宗教的界定,像其他多数关键词的界定一样,来自西方;就连“宗教”这个汉语词,虽然已有千年历史,但一旦用来翻译religion,它的意思就跟着religion走了。于是,基督教自然而然便是宗教概念的原型。儒教是不是宗教?我们多半会参照基督教来考虑答案,而不是参照青阳教。
以基督教为原型的宗教概念,扩展到如今笼统称为宗教的例如佛教上,很难严丝合缝。别的不说,佛陀并不是个人格神,他没有开天辟地之功,也不是处女生的;佛陀是个凡人,是凡人中的彻底觉悟者,就此而言,我们不知道他更近于上帝、基督还是更近于孔子。
说佛教是无神论,虽不中肯,却不算错。从历史—社会角度来看,近代以来涉及宗教的最根本的问题,宗教宽容,差不多也只是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问题,佛教徒无需宗教宽容的观念,他本来就没有异教徒的观念。(外道与异教徒是两个观念。)
欧洲经过了惨烈的宗教战争之后,逐渐生长起宗教宽容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莱辛的《智者纳坦》中获得了广富影响的表达。宽容或tolerance是种好品质,但这类词比较适合用来赞誉别人,用来形容自己则有点儿高人一等屈尊俯就的意思。
但反过来说,一种宗教是否真的应该或能够把自己视为与其他宗教平等?我阅读不多,却也读到过不少以此问题为中心的文著。这里谈谈汉斯·昆的《什么是真正的宗教——论普世宗教的标准》。(刘小枫,《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1。注,以下引文都出自该书)
汉斯·昆以基督教教内人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依照现代开明观念,我们不应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宗教视做高人一等,不应把身在基督教视做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但另一方面,“如果在教会和基督教之外已经存在着拯救,那教会和基督教还有什么必要存在?”(第9~10页)汉斯·昆分三步或曰依三层标准来回答这个疑难。
首先,存在着基于人性的普遍伦理标准,任何真正的宗教都不能违背这些总体的伦理标准。其次,每一种伟大的宗教都有自己的圣典,它们提供了一种宗教特有的规范。
最后,是特殊的基督教标准,“一种宗教如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让人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精神,那么,这种宗教就是真的和善的。我把这一标准仅仅直接用于基督教:使用自我批评式的方法提问:基督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合乎基督教精神的?不揣冒昧地说,这个标准自然也间接地适用于其他宗教”(第24页)。
总体上说,讨论这个问题,有外部角度与内部角度,从外部观察,我们会发现许多真正的宗教,然而,“我面对的不单是需要思考的哲学和神学论证,而是一种宗教的激励”,“只有在某种宗教成为我的宗教之时,对于真理的讨论才能达到激动人心的深度”
(第25页)。
汉斯·昆
汉斯·昆的论述,颇多内容深得吾心。尤其是他以基督徒的身份,常首先“使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基督教本身提问,直面十字军、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的迫害(第15页),直面极为排他、不宽容和气势汹汹,几乎是病态地夸大罪恶和负疚的意识(第14页),他的坦诚体现出大器的自信。
不过,在总体立论路线上,我觉得似未尽善。这条总路线,简要说,是把普遍性完全理解为共同性,以这种作为共同性的普遍性来解答思想上的困惑: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特殊性实现普遍性,“真正的人性是真正的宗教的前提……真正的宗教是真正人道的实现”(第30页)。
他的三层标准,第一层便是普遍人性的伦理标准,而下面两层标准能否确立,归根到底以是否合乎第一层标准为准:“基督教的特殊标准不仅仅符合宗教一般本源标准,而且最终地也符合人性的总体伦理标准。
”(第28页)这条总路线总的说来似乎是绕过而不是切入普遍性/特殊性关系的真正难点——如果确有普适的伦理标准,这些标准确实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发生分歧和冲突的时候,人们确实愿意从自己的特殊性上升到这些普遍标准(最后这一点其实是“确有普适标准”的主要内涵,因为,如果在发生分歧和冲突的时候,人们不愿上升到“普遍标准”,“普遍标准”就成了空话),分歧和冲突当然会迎刃而解,我甚至要说,特殊性就只是一些摆设而已。
然而麻烦在于,特殊性附属于普遍性只是一种积非成是的形而上学幻象,并不是对事情的真实描述。事实上,特殊性并不附属于普遍性,特殊的人之间、特殊的宗教之间发生冲突,没有什么原理迫使他们上升到普遍性,他们仍将作为特殊的人和特殊的宗教来寻求解决冲突之方。
解决之方也许包括营建某些普遍的标准,但它们并不是一些已有的现成的标准。“保障人权、解放妇女、理解社会正义和战争非正义”(第19页)并非一开始就是所有宗教和所有文化共有的普遍者,它们由宗教—文化的冲突和对话营建而成。
汉斯·昆笔下的上帝也是这样的普遍者。他说“基督徒信仰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上帝”(第27页),这个上帝,不只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所有宗教的上帝。例如,“在末日不会再有任何宗教,而只有上帝本身”(第32页)。
然而,作为共同者的普遍上帝并不能真正公平地对待众生;他是不是多神教的上帝乃至无神论的上帝呢?作为真正的普遍者,应该是的。一个基督徒如是说,足够宽容了,但对多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似乎仍有武断之嫌——“只有宗教才能确立一种无条件的和普遍的伦理,同时把它具体化”(第18页),似乎有点儿强加于不信任何宗教的人。
汉斯·昆批判“匿名基督教徒论”时说:“那些不是基督徒也不想成为基督徒的人的意志没有受到尊重……我们不会发现一个严肃的犹太教徒或者穆斯林、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不觉得把自己当做‘匿名’、‘匿名的基督徒’的做法是一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手段……似乎这些人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人!
”(第12页)根据同样的理路,我们似乎也不能把不信任何宗教的人视做匿名的信教者。也许,即使无神论者也信从“无名可名”的高于他自身的存在,但因此他一定信仰上帝吗——哪怕不把上帝理解为单属于基督教的上帝?
人们常说,语词总是抽象的;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也不妨说,语词总是具体的,称Jehovah(耶和华),称God(上帝),称Allah(安拉),称天,称Sakyamuni(释迦牟尼),总已经把某种特殊的文化—历史一道说出了。
那么,在这些语词之上,是不是有一个更高的“无名可名者”呢?在我看来,“无名可名者”不属于任何一种特殊的语言,但它也并不属于一种高于各种语言的语言,或属于作为一切语言基础的语言;倒不如说,“无名可名者”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中间地带,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同一与分殊。我希望我们不再迷恋凌驾于一切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更不用说把自己的特殊存在直接提升为普适原理。
那么,任何一种宗教,例如基督教,仅仅是种种宗教之中的一种吗?上面说到,汉斯·昆引入了从外部的观察与内部的观点这组概念(第24页),在一名“中立的”观察者眼里,基督教只是种种宗教中的一种,然而,从内部看待基督教,基督教就不只是与其他宗教并列的一种宗教,它是“我的宗教”,在这种宗教里,“我相信我找到了说明我的生与死的真理”(第25~26页)。
从外部看与从内部看是一组广泛采用的概念,本文开头处提到程颢对王安石的批评,采用的就是这组概念。
这组概念有种种亲缘概念,例如经验与观察,体验之知和观望之知。依体验之知和观望之知这组较为宽泛的概念,宗教间的对话与文化间的对话就没有什么不同。我虽是教外人,对爱和信却并不陌生,就此而言,与信教人的心智也许并不远隔,就像开明的信教人,与我们交往并未格格不入。
我们也许可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文化的爱与信都称做the religious或religiosity,即宗教情怀。
我生在华夏文化之中,我因生于斯成长于斯而爱我的文化;我并不是把我的文化与别的文化比较一番发现它最为美好才爱它。爱和信不是研究和选择的结果。我不必向人证明要人相信,华夏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我生在父母怀中,我因生长于亲人之间而爱他们。
我并不是因为把我的亲人与别人比较一番,发现他们最出色最美好才爱他们。我不必向人证明要人相信,我的亲人是最出色最美好的。)科学结论若不能证明其普遍为真就不足信,爱的信却不是如此。
我的信既不依赖于别人也该信,也不导致别人也该信。体验之知之为真与观望之知之为真有着不同的标准,更确切地说,事涉体验之知,只有在类比的意义上才谈得上“标准”,因为我们主要从外部谈论标准,而体验之知的真,体验之真切,主要是从内部说的,牵连着爱和信赖。
我们很难为体验之真切列出评判标准,并非因为体验是隐藏在内部的心理活动之类,而是因为体验之知既与爱和信赖纠结在一起,其为知的形态就千变万化,难用一致的标准来界定。
在这里,如果硬要说到标准,不妨用汉斯·昆的话来说:真理标准“首先只和自我而不是和他人相关,首先只对自己有约束力”(第15页)。我无须别人爱我之所爱,信我之所信,我只在自己的所爱受到轻慢和危害时才奋起捍卫她。
爱和信不是站在外部加以权衡之后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爱与信闭目塞听。爱自己的亲人并不意味着看不见他们的缺点,或看不见别人的优点,甚至相反,爱之深而责之切。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也一样。就基督教而言,“甚至在基督之后也还经常需要预言性的补正,需要教会内部的预言者……也需要教会以外的预言者和受到启示者;预言者穆罕默德和佛可以突出地列入其中”(第28页)。
与他者的对话是对话的典型形式,同时,以比较不那么彰明的方式,始终存在着一种内部的对话,或汉斯·昆所说的“内部的批判”(第22页)。
华夏文明内部始终存在着对这种文明的具体内容的质疑和批判。其实,就我们有所信有所爱才责之切而言,宗教间对话、文化间对话倒可以视做内部对话的一种形式。
上文所引“只有在某种宗教成为我的宗教之时,对于真理的讨论才能达到激动人心的深度”一语,似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关心人权概念的异同,关心民主制有没有普适性,研究罗尔斯理论的得失,唯当这些转变成我们文明的内部问题时,它们才“激动人心”。
生活的真理从来都是在这个传统或那个传统之中展现自身的,无人怀疑,宗教传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最重要的传统。正因为只有身在一个传统的内部才能对真理爱得深切、信得真切,在我们这个不断营建普遍价值的时代,宗教信仰绝未失去意义,对自身文明所怀的“宗教情怀”绝未失去意义。
这些仍有意义,在于它们生长在特殊的传统之内。特殊性是相通的基础或前提。我们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救赎。有人或由基督教的上帝救赎,有人由华夏文明救赎。有谁竟由普世宗教或普适伦理救赎,那仍然是一种特定的救赎,而不是更高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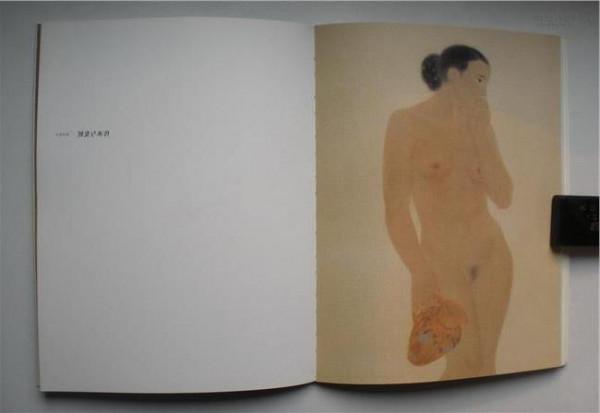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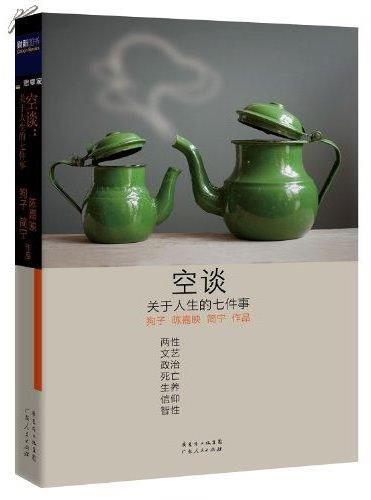

![>陈嘉映]陈嘉映 周国平](https://pic.bilezu.com/upload/0/72/0725457507eb935c5e97395ded42714c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