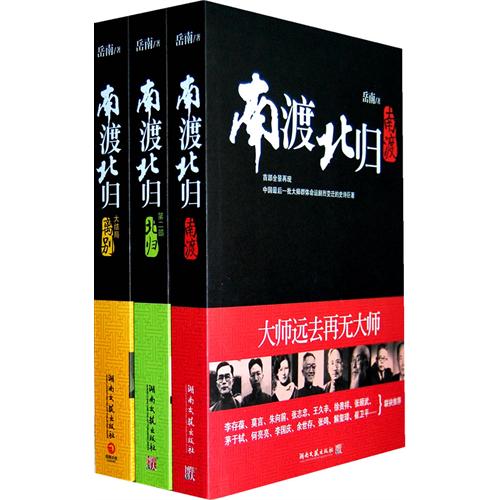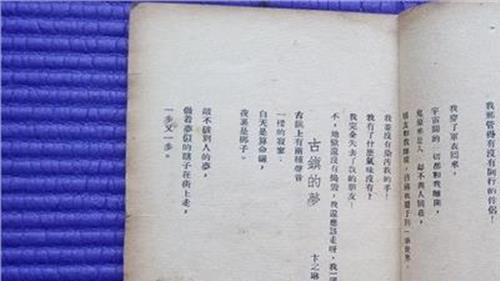闻一多学生陈梦家之死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连续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除中科院系统的大小头目与喽啰,包括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翦伯赞等辈也应邀参加,翦在会上宣读了讨伐“三大”右派分子特别是北大同事向达的战斗檄文。
向、荣、陈“三大”在一顿棍棒夹击和满口仁义道德掺杂着马列学说的大义凛然的唾骂指斥声中,立即变成了蝼蚁一样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三小”,被迫在会上弯下因几天没吃没喝而饿得宛如杨柳飞絮的细腰,低下高贵的头颅,做悔恨交加状,对着镜子狂喊王八——自骂自地高声“深刻检讨”起来。
为了把中科院系统包括陈梦家在内由“三大”变为“三小”的右派分子彻底批倒批臭,并作为反面典型警示那些大瞪着眼、懵懵懂懂、迷迷糊糊正在向“右”边沟里滑去的书呆子,中科院领导再度号召下属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继续组织强有力的革命中坚,对其给予致命一击。
各单位和研究机构得令,争先恐后响应,急速排兵布阵,并以外战的外行,内战的内行的革命大纛为向导,车辚辚、马萧萧开入阵前。在一片纷乱杂芜、旌旗猎猎、人喊马嘶的战阵中,随着郭沫若帅旗摆动,只见三员将领顶盔贯甲,跃马横刀杀奔而来。
居于中间为首的是一代名宿唐兰,左右两名小字号偏将乃潘山、秦华。三员将领到得阵前,勒住马头,先由二位青年小将分别叫号骂阵,潘、秦二人抓住一个叫关锡的青年曾给陈梦家写信大谈文字改革弊端,而陈氏积极响应并在媒体上为之公开呼应的往事,分别以《评关锡和陈梦家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态度》《继续追击右派——驳斥陈梦家、关锡》为纲领,对陈氏进行了一番痛骂与鞭挞。
二人骂过,回归本队,头号战将唐兰接着豪气干云地杀奔而出。
唐兰乃陈梦家的师辈人物,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任北大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始,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
就其资历与学问而言,称得上是著名的古文字学与古器物学家,完全可与陈梦家有一比拼。当年在甲骨学界兴行的“罗王董郭”之“四堂”学术定位,就出自唐兰之手并受到学界认可,这个定论曾在香港大学古文字研究生考试中作为试题被考过,可见其影响之大。
据闻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吴其昌(子馨)当面对唐兰放出豪言:“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14]吴氏的大言能否被学界公认是另一会事,但足以见出唐兰在对方眼中属于重量级选手的事实。
作为如此重量级战将,如今披挂上阵大战陈梦家,自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唐氏以《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根据平时对陈梦家强势与弱点的深入了解,结合前几日在中科院批判“四大右派”分子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草成了一篇名为《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雄文中,唐兰以先声夺人的凌厉气势,一开口便指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经此致命一击,陈梦家确是一败涂地,躺在地上如同一只被踩扁了的癞蛤蟆,只是干瞪着眼珠,鼓鼓嘎嘎地喘着气息而动歪不得了。
蓝的星,腾起又落下
为扩大战果,整个社会教育文化科学界也很快被发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殴运动。波澜所及,连西北大学师生也卷了进来。
据这所大学的一群师生揭发,陈梦家在受邀到该校讲古文字学期间,曾胆大妄为地说:“郭院长搞考证,引经据典,你们不要认为真的读了这样多的书,其实所讲的什么字通什么字等,是从‘说文通训定声’来的。
”这本来讲的是善于使用基本工具书的客观事实,西北大学师生却发文愤然批驳道:“郭院长是我国著名学者,我们向陈梦家抗议,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们敬爱的郭院长。”棒喝之后,又揭发道:“他又大肆污蔑革命先烈闻一多先生。
他在介绍闻先生的时候说:‘闻一多穿一件烂长袍,为了学习连尿也不到外面去,房里臭得很。”[16]面对全国学术、教育界掀起的批判声浪,“一败涂地”的陈梦家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忍受肉体与精神的极大创痛,低头认罪并甘愿遭受千刀万剐的惩处。
未久,陈梦家的工资被降三级,后曾一度随考古所下放锻练干部到河南洛阳白马寺植棉场劳动。此时,赵罗蕤面对自己、父亲赵紫宸和丈夫陈梦家受到批判和遭遇群殴的事实打击,身患精神分裂症,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治疗。
就在“反右”风潮波滚浪涌之际,远离风暴中心的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先后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三十七座汉代古墓,并在磨咀子六号墓发现了四百六十九枚《仪礼》木简和日忌杂占简十一枚,另有一些零星汉简出土。
时在考古所主持业务工作的副所长夏鼐,考虑到这批汉简的生要学术价值,征得尹达的同意,于1960年6月将陈梦家悄悄派往兰州,协助当地考古人员进行整理研究——这是夏鼐冒着政治风险为陈梦家寻找的一条避免肉体和精神折磨的通道,也是陈梦家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次转机。
于是,陈氏心怀感激悄无声息地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在一间形似仓库工房里蛰伏下来。因是戴罪而来,组织上规定陈梦家不能对外联系,不能与馆外的人接触,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讲,就是“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陈梦家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也为了不给把自己从五指山下搭救出来的夏鼐增添麻烦,坚守规定,足不出户(院),整日蹲在小屋里,全部身心投入到汉简整理研究中。
时值盛夏,陈氏冒着酷暑,昼夜苦干,博物馆值班人员深夜巡逻,经常看到陈梦家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趴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察看简上模糊文字的身影。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陈梦家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对出土的汉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包括六号墓出土的四百八十简,十八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以及四号、十五号、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墓出土的“柩铭四条”),撰写叙论、释文和校记三篇,随后完成了《武威汉简》一书,于1962年经考古研究所同意,由本所与甘肃博物馆共同署名,交由文物出版社作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于两年后出版。
出土的武威汉简文字
1962年年底,经过5个寒冬冰窟煎熬的陈梦家,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和政治生活,开始按考古所的计划要求,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铜器断代》和《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
随着“文革”狂潮巨风兴起,整日埋头于考古所研究室内一堆乌龟壳与破铜烂铁中的他又大难来临。1966年8月,所内的造反派以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三罪”,将陈梦家揪出来批斗。
所谓“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用稿酬在钱粮胡同购置的那个四合院;“作风问题”,则指陈氏早年是地道的新月派诗人,并有生活不端的绯闻,如当年在南京和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生、曾一度与徐悲鸿有过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后跑去台湾的孙多慈有一段纠结不清的关系等。
而进入新社会后又拒不改造。而“学术问题”,则是罄竹难书,有抄袭、剽窃、编造、欺骗、假充内行、纂改历史、欺世盗名等,无法计算。一时间,陈梦家的人格、学问成了毛主席所说的地地道道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随着“文革”武斗升级,成了“狗屎一堆”的陈梦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接受群众监督与批斗,令其反省交代“三罪”。紧接着,陈氏住处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和工厂造反派,开始游走于大街小巷抄家,陈梦家耗大半生精力,不惜破费万贯钱财苦心搜集收藏的明式家具、古玩器具,外加丰富的藏书、拓片、字画被一扫而空。
钱粮胡同的房屋成了外来人员的暖巢,赵萝蕤的卧床也被陈梦家一位同事强行占用,陈氏夫妇被赶到一间原本是汽车库的小黑屋存身。其间赵罗蕤精神分裂症两次复发,但送不进医院救治,整日在亲属的看护下摔盆砸碗地大喊大叫。
这年8月23日,考古所的造反派成立红卫兵组织,已关入牛棚的各类“牛鬼蛇神”26人被拖出来,分别戴上纸糊的高帽在所内游斗。24日上午,考古所的“牛鬼蛇神”被监视劳动,约11点半左右,一个头目突发善心,下令收工,各自回家吃饭,饭后再回所参加批斗会和劳动改造。
连日来被折磨得如同霜打的干瘪茄子状的陈梦家,突闻“大赦”,心中自是欢喜异常,在简单清洗之后,经由与考古所相通的近代史研究所大门,去往东厂胡同东口路南一个蔡姓妇女家。
所内看守的红卫兵一见陈梦家进入仅一墙之隔且有小门相通的近代史所,马上意识到什么,立即召集一干人马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待陈梦家到了蔡姓妇女家,刚要喝口对方端过来的水,忽闻大门“咣”的一声响动,随之冲进来一伙手持棍棒的红卫兵。
进得堂屋,红卫兵们二话不说,当场扇了陈梦家几个耳光,又将其踹翻在地,那位蔡姓妇女吓得全身打哆嗦。只听一个红卫兵头目说:“把这个乱搞破鞋的东西带走!
”众人蜂拥而上,将陈梦家从地上拉起,连拖加拽地向外弄。就在翻过门槛的时候,陈梦家回过头来,满面凄楚哀婉地对蔡姓妇女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言毕,被拖出了院内,随之在考古所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两单位相邻食堂的路口,遭到罚跪与棍棒敲头的毒打与辱骂。
烈日炙烤下,红卫兵弄来一个木凳子让陈梦家站在上面,进行围观式群殴。陈梦家头上的汗水和着脸上屈辱的泪水哗哗而下,未出半小时,就从凳了上摔下来瘫倒在地。
当日下午,缓过气来的陈梦家仍被勒令在牛棚参加学习。据当时亦在牛棚学习的王世民后来说,这个时候,陈氏的情绪显然与往常不同,时而走来走去,心情焦躁不安。傍晚的时候,陈梦家特别向牛棚中的学习组组长牛兆勋请假,说是夫人的癔病又犯了,在家大喊大叫,自己要回家照顾一下,晚间的学习就不参加了。
同时,留下一封敞口的信,请牛兆勋转交“文革”小组,说明蔡姓妇女与自己并无谣传的不正当关系,只是不时请她帮助料理家务和照看一下有病的赵萝蕤。
当天中午去她家,就是因为爱人癔病复发,急需有人前去照顾……怀着对陈氏遭遇的同情,经牛兆勋向“文革”小组汇报和力争,陈梦家被特许当晚不到考古所参加学习和写检查,但也不许单独外出,以免危害党和国家。陈梦家答应后回到家中。
那天夜里,被勒令不能走出家门,蹲在钱粮胡同一间小黑屋里令其“反省”。这一天,正是红卫兵野蛮的暴力行动达到极至的日子。考古研究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首,再向北穿过一条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国美术馆。
据“文革”史家王友琴调查考证,那一天,在考古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深夜,在用棍棒皮鞭打个半死之后,将人绑于葡萄架或小树上,再用烧得滚沸的开水往被扒光衣服的人身上浇,其中有两位妇女于沸水浇灌中“像杀猪一样”哀嚎不止。
邻居们说,被折磨的人那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久久不散。有的邻居不忍听闻又感到救助无力,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以减少精神刺激。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将横七竖八,一具具呈血蛋状的尸体运走。
那天夜里,被关在考古所一间黑屋子的陈梦家,一定也听到了外面受刑者那“杀猪一样”惊天动地的声声哀嚎,他无法容忍如此的残酷与野蛮,遂决定以死明志,以古老的“尸谏”方式,向所遭际的政治制度与考古所哪些昔日的同事、今日的敌人作无言的抗争。他吞下了此前藏在衣兜里安眠药,斜倚墙壁,面向窗外,等待着死神的召换。
35年前的1931年,20岁的陈梦家编辑出版了那部著名的《新月诗集》,除了收集闻一多、徐志摩的诗外,另有自己的诗作位列其内,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欣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正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時候。不知身陷囹圄的陈梦家这一夜是否看到了新月,更不知他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思考了什么,是否想到了“新月張開一片風帆”那美丽的意景和隐喻:新月形如風帆,送自己走向理想的彼岸,这彼岸不是天国而是人间。
让我合上我的眼睛,
听,我摇起两支轻浆——
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
在黑暗里轻轻的响;
吩咐你:天亮飞的乌鸦,
别打我的船头掠过;
蓝的星,腾起了又落下,
等我唱摇船的夜歌。
——陈梦家吞下的安眠药因药力不足而没有致于死地,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他与死神擦肩而过,没有合上“我的眼睛”。
据陈梦家的弟弟、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梦熊回忆说:听到哥哥出事了,我就急匆匆地赶到离陈家较近的北京隆福医院,只见哥哥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医生正在抢救。
我看了哥哥又回到钱粮胡同,去看嫂子怎么样。红卫兵小将正在院子里,对嫂子赵萝蕤又打又骂。赵不能前去丈夫的病床前照料,遭受着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红卫兵们突然见到一个前来探望的陌生人,当即把我抓起来审问。
当得知是陈梦家的弟弟时,如获至宝,把我押到院子中间,与嫂子并排跪着,一同接受皮带的抽打,两人被打得伤痕累累。领头的红卫兵似乎还不过瘾,下令用皮带的铜头抽砸——这是“文革”中红卫兵使用的最凶狠的一招,只要铜头砸下去,受害者必皮开肉绽,头颅开花。未砸几下,我与嫂子赵萝蕤的头皮已是鲜血四溅,四处开花,我那天穿的白色衬衣被血水浸泡成黑红色。未久,我与嫂子都相继昏死过去了……。
几天之后,陈梦熊成为地质部造反派的批斗对象,而赵萝蕤则被北大的造反派拉往北京大学校园批斗,而向她脸上狂搧第一个耳光的竟是燕大留校的一个助教、赵氏当年的得意女弟子。
十天后的9月3日夜,已回到家中的陳夢家再次遭到了考古所昔日同事、今日暴徒们的狂殴与侮辱,他决意不再被这些已完全陌生的暴徒“当猴耍”,去意已决,于当天晚上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赵罗蕤那惊恐的眼神与阵阵笑声中自縊身亡,那双看够了世事烟云的眼睛终于合上了。这一年,陈梦家55岁(文/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