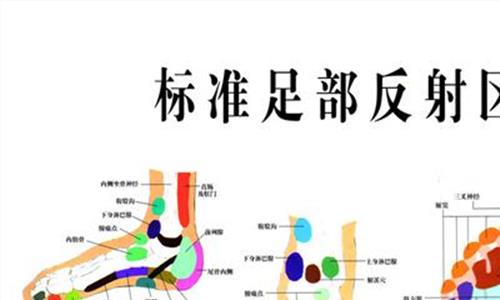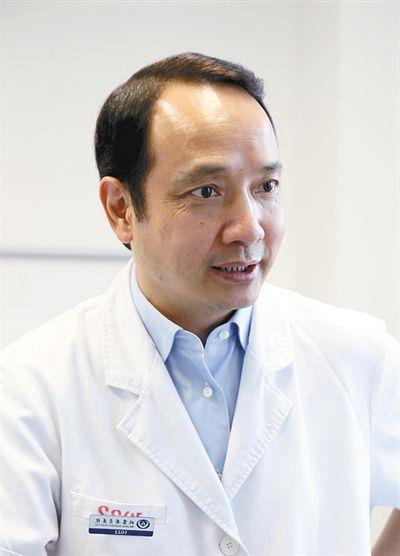叶子龙医生 保健医生忆毛泽东怎样对待自己的四位子女
我见到过毛主席的四个儿女,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毛主席和夫人贺子珍还生过五个子女,有的夭折了,有的已无下落……
毛岸英(1922-1950)是毛主席长子,也是他们兄弟中造诣最深的一个,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已经是红军中尉了。他从苏联回到延安,毛主席把他送到农民那里学习务农。我第一次见毛岸英,是在1946年初夏。中央门诊部组织医护人员到王家坪体检,走到村口,我看到两个穿西装戴礼帽的青年坐在村旁的石头上。那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白一点是哥哥毛岸英,黑一点的是弟弟毛岸青,他们刚从苏联回来。
一个月后,傅连暲叫我给毛岸青检查眼睛,我告诉他患有近视,需要配眼镜。他仔细看了处方,微笑着用夸奖的口吻说:“你这样年轻,就是医生啦,真难想象。在苏联给我看病的都是大胡子老头。”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稍带点口吃,可能跟很久不说母语有关系,他在讲话中没有带出一句俄语,这也很不容易了。我询问他年龄,知道他比我大一岁多一点。
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时,毛岸英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一带时,我没有见到他。
在东柏坡,我和毛岸英在同一个中灶,他在学古文,言谈中常带出“之乎者也”,看大家笑,他停止进餐,逐个向几位发笑的同事审视了一遍,问:“难道我的话说错乎?”引起更大的笑声,于光远说:“你说的话并没有错,不过古文是书本上的语言,你把它用来和生活中的语言放在一起说,才引起我们发笑的。”毛岸英微红着脸,自己也笑了。
进城后,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不久,投入抗美援朝战场,在彭德怀麾下作一名翻译。1950年底,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传来,是叶子龙最先告诉我的:“鹤滨同志,毛岸英同志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了,毛主席尚未知道,还瞒着他呢!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叶子龙的话我明白了,他是怕我有意无意地泄漏给毛主席。
我问:“岸英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司令部的同志们正在用饭,突然发起警报,敌机飞临上空,其他同志都迅速地躲进了防空洞,他不想离开,没去躲避,结果一颗炸弹下来,正落在了他在的建筑物上……”
时间过了不久,叶子龙刚刚从主席办公室里送文件出来,碰到我。“没有办法,岸英牺牲的事,主席知道了。”他沉痛地、无可奈何地说。
“主席怎么知道的?”我急忙关心地问。是谁透露给主席了?我想知道,也是向叶子龙表示自己没向任何人说过此事。叶子龙用低沉的语调说:“我送文件给主席看,我还没有离开,主席就带着怒气发话了,‘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主席发了脾气,他不知道岸英调不回来了。我只好向他讲了,岸英同志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写的……我接着讲了岸英牺牲的经过,毛主席听后沉痛地惊呆了。”叶子龙说罢,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开了。
毛岸青(1923-2007)是毛主席次子。我到中南海工作不久,一次走进主席的寝室了解他老人家的健康情况,主席带着愁闷的心情,把一个大信封递到我的手中时,用低沉的语调说:“王医生,你研究分析去罢。”我把信封恭敬地接到手中,只见信封上毛主席用铅笔横批着几个字:“河(鹤)滨同志阅,毛泽东。
”里面是一叠信纸,毛岸青写给父亲的,叙述他的思维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的情形。看信纸的样子,毛主席好像是反复地看过了。
岸青幼年,生活极其悲苦,流浪在上海街头,遭人白眼受人欺侮,甚至被毒打,幼小的心灵遭受了很深的摧残,以至精神有些不正常了。后来毛岸青弟兄被送去苏联,与他们的妹妹李敏及母亲贺子珍生活在一起。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食物短缺,毛岸青还常常丢失配给证,只好从母亲和妹妹那挤食一点。
回国后,毛岸青在中宣部工作,给一位在延安就颇有名气的俄文翻译家当助手,报上常有他们共同署名翻译的文章,但以后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这位翻译家欺他患病,有时少给他稿酬,甚至把翻译的文章据为己有。这样一来,毛岸青的病情加重了,以至不能坚持工作,于是他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生活。
我为此非常痛惜。岸青是位很有才干的年轻翻译家,当时我曾数次看到单独署名毛岸青的大块翻译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版面上。
一次,在卫士值班室,岸青正与几个卫士们说笑。“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伟大不伟大?”这种病态的语言成了卫士们逗笑的话题。我作为医生听到这些语言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心情是很沉重的。他见我走过来,高兴地说:“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都不对我说真心话?”我问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他尚能清楚地回答上来。
但是不久,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只好请专人特别护理。他到中南海岸边的马路上散步时,必须跟上两个强有力的小伙子在两侧保护,不然他就往水里跳……
我问他:“岸青同志,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自己才好!”
“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到水里去!跳到水里去!’我没办法摆脱掉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好,对我有说有笑的,我又不离开他……”
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见了我也不愿理睬了,完全被他“脑子里的小家伙”控制了。他看我的目光是那样的淡漠,好像我是个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一样。
毛主席问我:“岸青的病情怎么样?”
我说:“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我沉重地回答。
“那怎么办?”主席又问。
“那需要送去医院治疗。”我果断地回答。
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对我说,又好像自言自语地和自己商量:“岸青需要住院治疗,去哪里好呢?”他思考了一下说:“我本来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孩子有病去麻烦苏联政府。”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考虑一下……”他吸着一支烟沉思起来,我退出了毛主席的寝室。最后,毛主席不得已决定送岸青到苏联治疗,派了两名卫士护送,以防出现意外。此时岸青已无能力控制自己了。
1954年11月,我去苏联留学,到达莫斯科时,我请了一位大使馆的同志带我去医院看望毛岸青。值班医生简略地向我介绍了岸青的病情,之后将我带到了一间病室,这里只有毛岸青一个病人,病房很普通,一张病床紧靠着山墙,室内有两把椅子。医生向毛岸青说:“郭良(岸青在苏联的名字),你的中国朋友来看你来了。”说完,值班医生转向我说:“你们谈谈吧,他近来的病情还算稳定。”说完便走了。
此时,毛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笔画着什么,经医生说后,他向我看了一眼,仍旧画他的画。我走到他的面前温和地问:“岸青同志你好!你还认识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