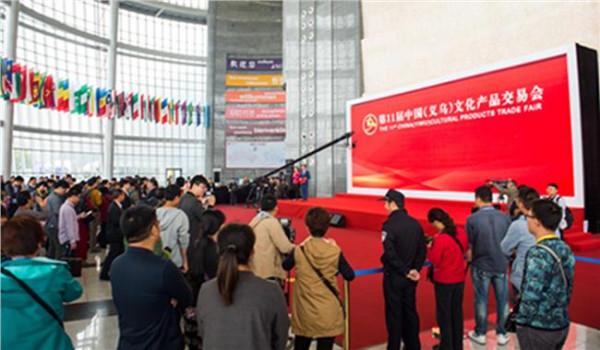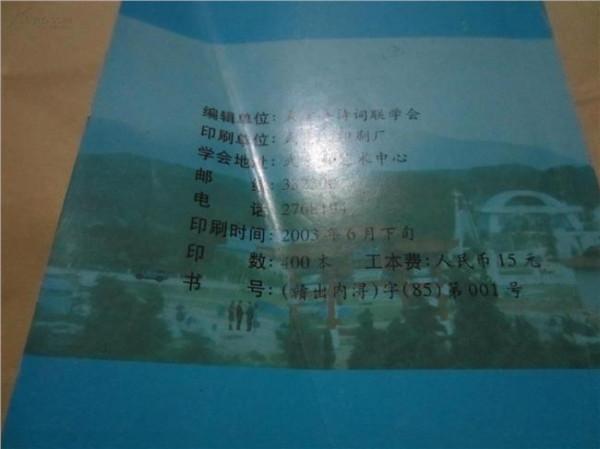雷平阳的人生 雷平阳:那个与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诗人
雷平阳,诗人。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现居昆明。2010年鲁迅文学奖及多个诗歌大奖得主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云南诗人雷平阳曾这样描述自己:“石头的模样,泥巴的心肠,庄稼的品质。笑起来,厚厚的嘴唇像石头开裂;不笑的时候,嘴巴荒芜,鼻梁落满白霜,小眼大雾茫茫。我从来不用额头思考问题,但皱纹一层叠一层,头发悄悄变黄。我知道我皮肤的漆黑,像有一片不变的夜色把我与世界隔开,所以我怕太强的光,所以我一直身体向内收缩,像个患了自闭症的诗人,默默地生活在故乡。”
默默在云南生活了48年的雷平阳,最近又推出诗集《基诺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2010年以来《云南记》之后的大部分诗作,这是他又一部让诗歌“在场”的结晶。
这些年,雷平阳的诗越来越受到关注,他也拿下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文学奖。在某一次的获奖词中,他说:“生死有艰险,乡愁无穷尽。这些我身边的生活画卷足够我写作一生。为此,我深知,作为云南这片土地上,像一棵树一样的生长者,我的写作,永远没有高高在上的时候。如果诗歌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一座殿堂,它应该修在山水的旁边,村庄的大树下,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雷平阳也不是。他温和、敦厚,远离各种流派、是非之争。对于文坛上的很多事,他只是淡然一句:“人都自有因果,我不关心。”
他是个老派人,至今不用电脑,在儿子的帮助下才学会了用微信,平日习惯用钢笔写诗,用毛笔写信。除了写诗、写散文,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贾平凹说雷平阳的字,“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有拙正、庄重的味道,所以在他的笔端,常见方笔,他的笔是定得住的,意到,笔才到,入了一种境界。”
前不久,雷平阳的书法展“山水课”在大理展出,策展人是客居云南的诗人潘洗尘,但展览并不针对市场,更像是朋友间的雅集。他和诗人李亚伟、树才、赵野等人齐聚一堂,饮酒论诗。“我拜山水为师,听命于山水,认为山水间有不朽的教堂与课堂”。
若干年前,雷平阳曾说:“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连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若干年后,雷平阳继续在写,“雨林中的基诺山。人、神、鬼共存的基诺山。”
对于雷平阳来说,诗歌写作的难度,是如何将“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在他看来:在“现实”中,我是那个与鬼谈恋爱的人,在“诗歌中的现实”里,我则是那个与神山之上的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诗人。
对 谈
我一直不认可
“地域性”这个概念
羊城晚报:无论是《基诺山》还是《云南记》、《出云南记》,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写云南,能否谈谈您对云南的感情?
雷平阳:故乡或者他乡,对于诗人来说其宽度和重量是一样的。我不是一个只为某片土地而写作的诗人,“云南”在我的诗歌中,它是语言、情怀和时空的背景,不是写作的标的,更不是审美的终点。从《云南记》到《基诺山》,有着对情感根系的寻找与持守,但主要还是为了让诗歌及物、在场。
我们曾经长时间地受制于观念,却一直缺少从内心生出的有感而发,仿佛诗歌真的必须虚无缥缈。在“云南”生活了四十多年,故乡、亲人、山水以及多元的文化,我受其恩,感其德,视其为地平线背后的天国,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即使老死在那儿,你一定要相信,对它而言我仍然是一个过客。
羊城晚报:人们喜欢说您的诗歌具有某种“地域性”,但换个角度,如果将诗歌里的地理坐标换成别的地方,诗歌也完全是成立的。从这个角度说,您的诗似乎又并不是地域性的?
雷平阳:我一直不认可地域性这个概念,尤其不认可用来对应“全球一体化”的所谓地域性。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诗歌界,有的自认为具有“世界性”的诗人,他们总不遗余力地把另一些生活在“小地方”或写“小地方”的诗人划入“地域性”,借以说明他们才是诗神的特选子民。
以前我也认为诗歌领域是一片净土,渐渐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大超巿和名利场。我认可这现实,但我不认为贩卖舶来“奢侈品”的人就有权力贬损销售大米的人,当然,销售大米的人也无权去挑衅任何人。
人人都看见了灾难
却装着没看见
羊城晚报:您在《基诺山》的序言中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偷渡客。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我所奉行的往往就是我内心反对的,而我真正以文字竭力捍卫的东西,却连说出声的勇气都早已丧失,我的身份缺少合法性、公共性和透明度,总是被质疑、被调侃、被放逐”。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特别触动,这似乎不仅是诗人在当下的某种困境,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巨大难题。您能否再详细谈谈?
雷平阳:首先要说明,在诗人的眼中,诸如黑暗、暴力之类的概念,它针对的是人类共有的文明,不指向具体的国家与政权,惟其如此,诗歌也才会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永久性。
《基诺山》这本诗集里,我的愿望是将基诺山作为我写作的可以坐实的场域,彰显生存困境。我们所经历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放到一座人鬼神共生的山上,不是为了缩小世界之悲,也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找出它们之间的秘密通道和神秘关系,继而发现颠覆、衍生、毁灭的反人性的一面,同时又挖掘出人们内心隐藏的、不便直接表达的悲心与忏悔。
“偷渡客”,我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思想与身体,都已经离开,却又发现自己被留存在了现实的哈哈镜里。我们的现状,越是恶心的东西越可以大行其道,摆到桌面上,而那些圣洁的、我们共同向往的东西,却被抛弃和埋没。人人都看见了灾难,却装着没看见。人人都参与了对美的追捕,却又谁都不站出来承认。拷问,审判、反思,是应该的,更多时候,诗歌可以魂不守舍,但现在则应该主动加入。
类似的困境,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存在,反对它,以前的诗人在做,我也不想置身事外。我不喜欢象牙塔,我就喜欢荒野和现场。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当代汉语诗歌,观念流派太多了,缺少的是质地坚硬的真诚的书写,没了血性与生命力。
羊城晚报:很多1980年代写诗的人中途就停笔干别的去了,但您一直在写,没动过别的念头吗?
雷平阳:去了来了,风流云散,一切都自然而然。有人离开,有人死守,诗歌写作的人群一如其他人群,“变”乃是唯一不变的东西。我有过离开的念头,这念头不强烈,也不持久,便留了下来。留下来的时间久了,人事也就荒芜了,也就不想离开了。
再寂静、再破落的寺庙也得有人守着,否则庙寺也会成荒山,无庙了。相信很多诗人也如我想,所以诗歌界仍然香火袅袅,不因谁走而荒凉,也不因谁加入而鼎兴,常态、常形。
读者少了?
这是个滑稽的问题
羊城晚报:经常有人说,诗歌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但是“作家们其实还是在为文学忙得不可开交,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麦家语)。文学活动似乎越来越多,但真正静下心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您怎么看?
雷平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是会死的,文学却肯定不会死,谁给文学送过终、当过守灵人?没听说过。在写作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文学的生与死问题却持乐观态度,我不认为这个时代是文学万劫不复的年代,人类历史上比现在更不堪的年代太多了,文学不也存活下来了?
至于读者少了,更是个滑稽的问题。我的书卖不出去我就说读者少,怎么没听金庸说读者越来越少?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怎么也不说读者少?读博尔赫斯、托尔斯泰的人肯定是少数,干吗一定要强求?如果我让自己十一岁的儿子读卡夫卡、普鲁斯特、萨特,读屈原、杜甫,读残雪、马原、顾城,我认为是家庭暴力,他就该读安徒生。
我们别犯酸了,也别自以为是了。上个月我去法国,见到的法国作家都说,法国人都在抢读萨科齐老婆写的畅销书,莫迪亚诺得了诺奖,书的发行顶多也就几千册。
羊城晚报:我有个感受是,诗人之间的交往似乎比小说家们显得更为紧密,关系也更亲近,各种诗歌活动很多,民间诗刊、民间诗歌奖也不少。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雷平阳:由古及今,诗人的交往都是诗歌史中最温暖的章节,都是些相对透明又怀揣火焰的人,在一起自然就会产生激情与光芒。互联网时代的确方便了诗歌的传播,对此我是持肯定态度的。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是不用电脑写东西,只享受写在纸上的触感?
雷平阳:我不讨厌电脑及互联网,但我讨厌用电脑写汉诗。汉字会意象形,是活的,我迷恋手写。
羊城晚报:不仅写诗,您的书法也颇为人称道,其实诗歌创作和书法之间,是否在本质上存在某种共通之处?
雷平阳:诗歌和书法在汉语传统中都是古老的技艺,两者都是为了让汉字活过来、美轮美奂。一些诗歌和一些书法之所以像模像样却又不忍卒读,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汉字是死掉的,作者没有让它们借尸还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