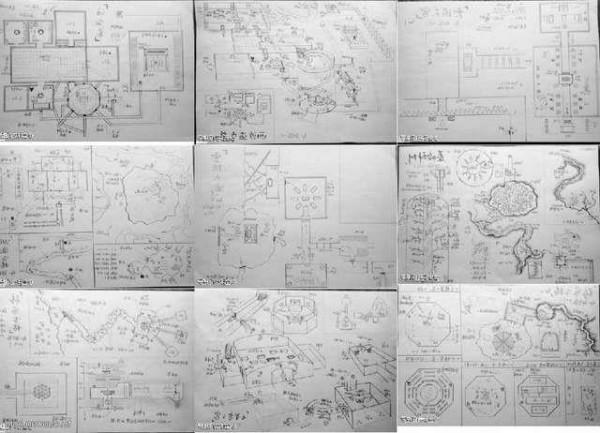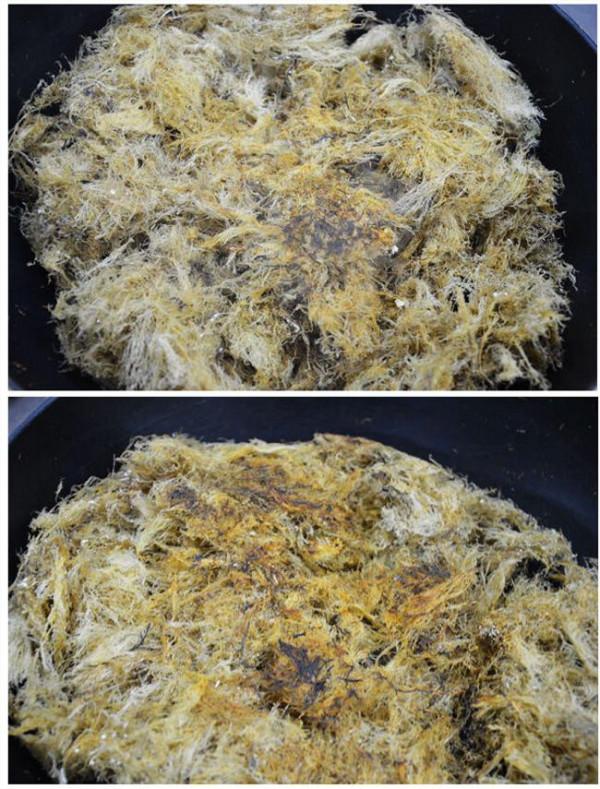陈晓卿至味在人间 陈晓卿谈《至味在人间》:最好吃的是“人”
因《舌尖上的中国》而被人熟知的总导演陈晓卿,十年写吃的文字集结成《至味在人间》一书,在出版方“理想国”的规划下走了全国十几个城市进行“巡演”签名售书,而最后一站,他放在了广州。
因为,广州的吃,选择实在太多,每次来广州,朋友们在推荐他去什么餐厅吃的时候,都要屡犯选择困难症,这还不包括潮汕地区的吃,“生在那里更是个‘悲剧’,一辈子别想离开,好吃的太多”。
这心得也是8月14日下午陈晓卿在太古汇方所,与广州人民分享关于吃的时候感慨的。
我有一个故乡
对于吃,陈晓卿是不忌口的,“啥都吃”,他曾吃过比较惊悚的食物是云南傣族人的“撒biang”(音),就是牛反刍的胃液,撒上蚂蚁跟白糖同吃……同时为表对尊贵朋友的热情,要喂到嘴里,而对于北京来的尊贵朋友陈晓卿,人家的热情再升一级,先搁自己嘴里咬一半,把另一半从嘴里掏出来送进他嘴里。陈晓卿说他一口就吞下去了,旁边一位云南本地女性同行瞬间就吐了……
如果非要说哪一样食物是他的最爱,“那就是醉酒后妈妈煮的粥”。
食物的记忆是很私人的事情,它往往与个人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陈晓卿说他在北京,去得次数最多的是一家朝鲜冷面馆,保守估计也去过不下两千次,而且最难得的是,每次他将这个冷面馆推荐给朋友,得回来的反馈基本上都仨字——真!难!吃!
可对他,这冷面馆,无论环境还是味道,都带着对往事的印记,每次去,就有点儿“往事就面条”的亲切感,很多事、很多人,都在这里发生、经历,就像另一种调味料,一靠近就滋滋往外冒。
陈晓卿从安徽老家到北京读大学,专业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婚纱摄影,他说这学校连月票都管,唯一缺点是不管饭,穷学生,没钱,被同学带着来这冷面馆吃冷面,当年的价格是一毛三分钱一大盆,吃一盆管一天不饿。第一次吃他也吃不惯,后来迫于环境,还是总选择到这里吃,直到把这家的冷面活生生吃成自己心目中的“正宗”。
在陈晓卿看来,关于吃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三个终极命题——吃什么?去哪儿吃?跟谁吃?而这个“跟谁吃”,又是终极中的终极,跟自己喜欢的人、恋人或有趣的人,吃什么和去哪儿吃都可以忽略,哪怕是坐路边摊、哪怕是轻易不会去的馆子,都行,只要有这样的人一起吃。
所以他的文字,更多的不是写这个菜怎么做,关注点更多着落于食物与人的故事、情感,他说这本集子,最开始起的书名是《最好吃的是“人”》,这个灵感来源于鲁迅的《狂人日记》,“满篇都是吃人”,但有关部门觉得不雅,后改为现在的书名,其实就陈晓卿那些文字而言,《最好吃的是“人”》似乎还更切题一些。
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的乡土情结,沈宏非评价他是“对城市充满了敌意”,虽然从小物质基础并不算十分丰富,但京城也确实没有那么多密集的、好吃的可供选择,此外,“人要有个故乡”,是陈晓卿的另一观点。
故乡情结,是当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发生转换之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情意结,每一个离开家乡在外漂泊的人都有这种情意结,它,代表着一种乡愁,也代表着对新的空间、新的现实生活的不认同和疏离感,哪怕这是自己的选择,也不影响你持有这种故乡情结。
与此同时,这也是成为一名美食家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必须在离开自己的出生地、经历过异乡的味道、颠覆自己曾经的认知体系之后,才更深刻体会故乡的滋味。“像梁实秋、像汪曾祺,他们要是不曾离开北京,哪里能写出那样诱人的北京的吃的文字?”
“地沟油”美食家
陈晓卿的朋友曾说他是“地沟油”美食家,他一点也没有反驳,因为他确实喜欢那些带着鲜活的人间烟火气的路边小店。美食,并不仅局限于食物本身,他更看重由美食而来的人文的东西,那些普通人的生活,让他觉得安稳,他特别喜欢。
他常去的一个小馆,春节前,店里几位忙着择菜准备,陈晓卿喜欢跟人搭话,就随口问人家,“过完年还回不回来呀?”
“回,我还要赚钱呢,我还有一个目标没实现,我还没喝过茅台,我想试试。”另一个就说:“我老公喝过,好不好喝不知道,但这酒不上头。”再一个又接:“酒还是少喝点,你看你好好的在这上班,要是你喝了酒,说了不该说的话,就回不来啦。”……
他活灵活现地复述着这些——人间烟火气的餐厅、普通人的生活、人之间的交流、在这个浮躁社会中已属难得的真性情,都是吸引他的。
所以他的镜头也总对着普通人,有人说《舌尖》里出现的大多数是普通人,面对镜头是那么自然,如常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如同面前没有镜头一样,陈晓卿说这是因为《舌尖》的拍摄,更多的功夫和精力花在了调研上,这个时间很长,拍的和被拍的早已混熟成了朋友,所以一般人望之神秘可怖的摄像机也就像空气一样自然存在了,“你得比你的拍摄对象更能坚持,他干他的,你拍你的,你别比他先放弃,就是这效果。”
去菜市场 才是“滚床单”
这么多年吃下来,除了智商、情商,还吃出来了“食商”,即饭桌上的急智,经常被要求评价菜好不好吃,好吃的还好办,不好吃的又不能直接说不好吃,那怎么办?陈晓卿便借用蔡澜先生的说法:“嗯,相当有趣。”
他形容自己对吃,是一个欲求不特别强烈、容易满足的人,能欣赏得了特好特贵的菜,也能享受各种奇葩惊悚的食物,可以是挑剔的美食家,也同样忠实于自己的味蕾,“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通道,”他说:“为自己的价值而生,餐饮就是社会,不一定是同一标准,再难吃的餐厅也有自己的忠粉,有挑剔的食客才会有好的餐厅,而我们的现状是,大多数人其实还不懂得吃,跟风的性质更普遍。”
菜市场被他推崇为“一个城市的灵魂”,“如果说去餐厅吃饭好比是穿戴整齐了面对面相亲,那去菜市场才是‘滚床单’。”
作为美食爱好者,同时又是美食专栏作家,陈晓卿很享受写作的状态,“既受虐又幸福”,受虐的是对自己的文字,有洁癖和强迫症,对写作环境和写作时间的完整性也比较讲究,写完自己删删改改好几遍,过程就带点自虐性质。但写作又是他的独属天地、自主王国,长期混迹于充满各种妥协、不能极致表现自己想法的电视行当,当可以随心所欲撰写自己想写、有兴趣写的东西时,那感觉不啻于大热天从室外进到空调房喝下一碗冰镇酸梅汤一般畅快。
虽然他说这些零星的念想文字其实是被报纸杂志的编辑们用“午夜凶铃”给逼出来的,但他非常感谢这些编辑们,他们不但逼出了这些记录,甚至《舌尖》也带着与这些文字相关联的气质,还集结成册,有了《至味在人间》一书。
人,每天都会饿,饿了就要吃,不过,好(此处请读四声)吃好多年,陈晓卿也言若有憾地摸着肚皮说:“体重从120斤吃到了160斤,这是工伤啊,单位也不给报。”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