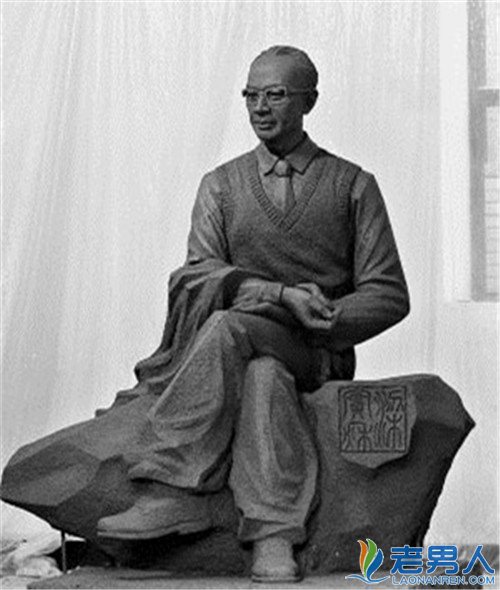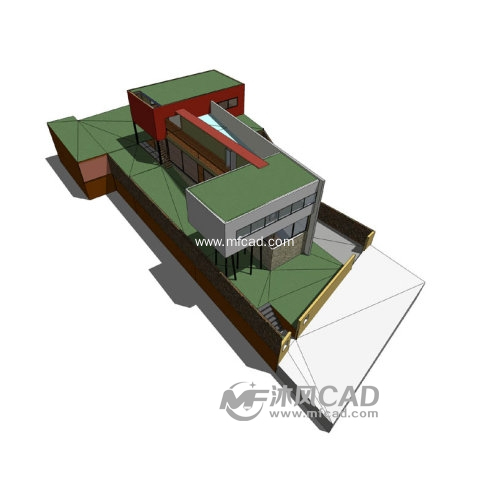库哈斯作品 库哈斯|央视新楼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库哈斯:你知道,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它是绕不开的。一说起60年代,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嬉皮士、摇滚乐、流行文化一类的事物,似乎只有这些才是那个年代的象征。但实际上有两个60年代,美国的和欧洲的。美国那时候,战后“婴儿潮”一代正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刚好是我的同龄人。
在冷战的余波里,年轻人眼中的世界失去了方向,甚至不可理喻,他们敞开心扉,寻找一切途径宣泄自己旺盛的精力,管它是合理的还是荒诞的。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个强大的旋涡,需要抓住一种能够证明自己存在感的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本身是虚无的。
这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无法避免的。嬉皮士、摇滚歌手、反社会者,他们追求性解放,追求自我放逐,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一种极致的、眩晕的反思,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抵制还是在享受这眩晕的感觉。
欧洲却是另外一番景象。60年代的欧洲,革命浪潮席卷整个大陆,年轻人呈现出另一种精神状态,与其沉溺在旋涡中不能自拔,不如努力反抗,寻找秩序。
况且在欧洲,革命是有优秀传统的,从荷兰到法国,再到中东欧,几乎可以说历史是在革命的推动下不断演进的。60年代欧洲的革命,根源都在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反思,虽然未来的方向仍然不清晰,但这个过程对年轻人头脑的历练胜过了对身体的释放。
E:那么您更喜欢哪一个60年代?
库哈斯:坦白地说,我更喜欢欧洲的60年代。它的美好之处在于,那时候从事建筑并不需要文凭、执照一类的东西,那真的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蓬勃自由的状态,无论你对什么事物感到好奇,都可以依着自己的兴趣去挖掘。
你的创作构想,经常会得到正面的鼓励和支持,建筑是大家共同参与的领域,每个人都怀着社会责任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把社会推向良性发展的道路。现在的情况是,要想成为建筑师,必须经过一套成规训练,看上去学这学那,热闹得很,可实际上对学生们的思考有太多限制。
所以我很感激我经历了那样一个思想开放的60年代。至于在《海牙时报》做记者,你懂的,记者这一职业的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客观,所以这段经历对青年时代的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锻炼,让我逐渐学会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观察社会,感受事物变化的脉搏,再以客观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出来。
E:您描述的60年代很令人向往,您对它可曾有过怀旧之情?
库哈斯:这个倒没有。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可重复的,这一点我很早就想明白了。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它的魅力,所以不必一味怀念已经逝去的岁月。
E:您的建筑作品向来以“去类型化”著称,那么您的政治立场呢?
库哈斯:我基本上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当初决定从事建筑,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要通过它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那些以资本为导向的价值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除了理论和主张,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去做一件件具体的事。这需要社会性的参与、合作,需要建立真正的公民意识。
E:您为自己的事务所取名“大都会建筑”,其用意何在?
E:在200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奖演说中,您将自己形容作“未来主义者”,15年过去了,您仍这么认为吗?
库哈斯:是的,我一直关注未来,从最开始选择职业时就是这样,我需要了解这个行业自身的发展前景,并思考从事这个行业对未来的意义。不管我从事哪一种工作,我都尽可能地利用它提供的契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社会的动向,琢磨事物发展的规律。具体到建筑,我会关注它在往哪个方向走,这趋势中哪些是内在的意志,哪些又是来自外部的驱动力,它是不是最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方向,如果不是,我们建筑师能做些什么来改变它,等等。
E:同样是在那次颁奖典礼上,您提到当年在纽约与建筑师彼得·艾森曼初逢的一段趣事,他认为您代表着“哥特元素”,言下不乏对历史的隐喻。那么身为一名荷兰裔建筑师,您可曾感到自己身上肩负着某种传统?
库哈斯:哈哈,这段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第一次到纽约,当时彼得·艾森曼正担任建筑与城市研究院的院长,我到研究院的第一天,他上来就抓住我的大衣袖子,直截了当地问:“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库哈斯?”我说不知道啊,然后就被告知,我来这儿就是要代表“哥特元素”。
艾森曼真是眼力过人,一下子击中了要害。要知道,在那之前,我可从来没想过自己“代表”什么传统元素这事儿。在我的青春时代,在我的国家,标示某人的宗教或种族背景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比如犹太性,我们对此都绝口不提。
但在那次与艾森曼的戏剧性初逢之后,事情彻底改变了,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身份问题。这实际上关系到责任,如同你问到的那样,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传统,也就感到了责任的分量。
我来自荷兰,而荷兰又是欧洲的一部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代表欧洲的,承担着一个欧洲人应尽的义务。我努力为欧洲一体化做些事情,包括在比利时协助欧盟委员会推进建立欧洲首都的工作。
这里面有我的政治理想,但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遭遇挫折和反对。欧盟各成员国的政府规模和能力参差不齐,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做事风格也出入很大,意见经常有分歧,很难统一,导致决策力大幅减弱,要花很多耐心跟他们沟通。我在设计欧盟旗帜的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这是历史形成的,欧洲自古以来在结盟这个问题的争执上就没有消停过。
E:说起历史,90年代您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曾指导学生做过一项关于古罗马城市的研究,它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库哈斯:我们都喜欢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过去似乎有一种特别迷人的意味,但是我们远没有了解这魅力背后真正的东西。罗马之美,在于它的秩序,从军事、法律,到建筑和城市,是秩序赋予它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在研究中也特别关注这个特质。古罗马的城市,包括罗马人在地中海其他领地建立的城市,都是在不同地形、建筑和公共空间的组合中建立秩序,并竭尽全力去维持它。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很多大都市都缺乏的。
库哈斯:每个大城市都有它的问题,这是肯定的。但北京、上海与70年代的纽约最大的区别在于,当年的纽约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它就像一条下滑的螺旋线,无法逆转。资本主义掌控下的社会已病入膏肓,城市看上去五光十色,但处处潜伏着没落的迹象。
而今天的北京是一条上升的螺旋线,前途是光明的,对此我充满信心。我真的很喜欢北京,人们或许会批评它混乱无序,但恰恰是在这“混乱”中,隐藏着关于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和我们全部的期待。我相信政府和决策者的眼光,当下的问题和困难在所难免,但从长远来看,会越来越好。
我也非常喜欢深圳,这座城市真的很有意思,它在短时期内建成,又带着与生俱来的性格,可以说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奇迹,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感到未来是有希望的。
E:北京中央电视台总部新楼是个极富争议的作品,它是否对您此后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库哈斯:当然影响啊,争议是正常的,一件作品问世之后的反响,我们建筑师无法控制。CCTV这个项目说来还有一段故事,那年我的事务所还被邀请参加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竞标,也就是纽约世贸大厦的重建项目。美国那时候几乎是全民反恐,复杂的意识形态背后还有一种对旧日辉煌的留恋,很难说这样的心态是积极进取的。
而中国的城市发展则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印象,我更看好这样的前景,也真心想为中国做点什么。我设计CCTV新楼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为北京、为现代媒体建立一种新的身份,我预料到会有反对的声音,但实际引发的论战还是令我吃惊。
你能想象吗,当时真的是骂声一片,空气中充满敌意,就在清华大学,200多人一起声讨我们,用了非常激烈的言辞,其中不乏恶意的批评。
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这个项目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令人深思的是,两种批评的声音非常不同,西方质疑我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初衷,到最后都变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现在回头看,其实所有这些争议都很有启发性,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争议背后有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因素,这是不以建筑师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不管我们的初衷有多真挚。“因地制宜”听着简单,但真正执行起来绝非易事,我仍在不断领会。
E:如果您作为一个评论者来看待这个设计,会如何评价呢?
库哈斯:我至今仍觉得,这是我建筑职业生涯里最好的作品之一,我很珍爱它,而且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北京的人们会渐渐喜欢上它的,那时候,我为其倾注的心血就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E: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重新设计CCTV新楼,您会怎么做?
库哈斯:我很少对过去做出假设,一件事发生之后,便不可能逆转,你只有继续往前走。
库哈斯:其实,我并不是“先知”,尽管普利兹克奖的评委是这样形容我的,他们可真是抬举我了。我所能做的是细心观察,思考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欧洲的国家历史上也发生过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也经历过成功和失败,如今都已成过往。
中国的城镇化的确有让人困惑的一面,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理想的发展状态,有崭新的方向,难得的机遇。欧洲在老去,美国在衰落,这个趋势难以改变,我们迟早要接受。世界越来越多元,其他文化的崛起本该是令人振奋的事,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的希望又何尝不是世界的希望?所以,身处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都要把握好时机,把握好方向。
E: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建筑文化遗产几乎已消失殆尽,您对此作何感想?
库哈斯:遗产保护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在中国想做的事情。但保护的概念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而且不同文化有不同理解,据我的观察,在中国,更多的是围绕着“保护”这个概念做文章,对“保护”的阐释不止一种,经常是随机应变,所以就会看到,老的建筑拆了,再模仿它建个新的,修旧如旧或者修旧如新,甚至把几处老房子的遗迹全部搬走,移到另一个地方重新搭建起来,都叫保护。
但在欧洲,保护指的就是东西本身,就是这个房子,要把它留下来,小心翼翼地修缮它,修好了就不许碰它。
在中国,需要保护的建筑遗产还有很多,比如说胡同,这个我非常着迷,随着对它了解程度的加深,我越来越感到,我们要保护的根本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最珍贵的东西,是文化的一部分,建筑与文化不可分割。
E:中国的先哲孔夫子曾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意是指人所能抵达的自由境界;您已年过七旬,可曾感到这种“从心所欲”的自由?
库哈斯:我一直都有这种自由,这是建筑师跟政治决策者最大的不同,关键是看你如何驾驭这种自由。我之前提到过,建筑与其他认知和实践领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触角可以伸得很远,它其实是灵活的,有弹性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在具体操作时它会受到各种限制,不妨把这些限制当成创作的推动力,带着这样的心态工作,最终的作品自然会挣脱束缚,抵达自由。
E:近年来您开始关注乡村问题,而迄今为止您在中国的实践都集中在大城市,您是否想过到中国的农村看看,并参加乡村改造?
库哈斯:当然啊,我一直盼望有这样的机会,我必须承认自己对中国的认知是很有限的。中国还有那么多值得我去学习和了解的地方,城市只代表中国的一面,而乡村与城市一样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每一天都会不同。
乡村的改造也不是哪个建筑师说了算的,最有发言权的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我们不能傲慢而武断地告诉他们,这里应该变成什么样,你们应该怎么过,去哪里建设美好生活,等等。所以亲自去跟乡民交谈,观察并体验他们的生存境况太重要了!
E:身为“明星建筑师”,您自己又是如何看待“明星建筑师”这一现象的呢?
库哈斯:你提的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所谓“明星建筑师”,真是不由自主的,这都是媒体和宣传运作机制造出来的,它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我们就这样被推进了“名流”之流。可仔细想一下,“明星”和“建筑师”本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族群,各有各的营生,怎么能硬往一块儿拉呢?我在实践的时候就是要有意识地消解这个叫法。
比如现在这个Prada项目,我在设计中尽量去保持场地100年前原汁原味的工业遗迹,把这个区域固有的潜力挖掘出来,再想办法自然而然地呈现它,让它跟周围的城市环境发生对话。
所有这些都是在“平常”的态度中完成的,带着一颗平常心,不需要矫揉造作,更没必要故弄玄虚,它有它该去的方向、想成为的样子,我们应该做的是拿出耐心和诚意来了解它,而不是人为地给它贴上什么形式标签,一旦带上“明星建筑师”个人风格的烙印,它自身的生命就开始枯萎了。
所以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明星”与“建筑师”这两个本来不相干的物种重新区分开来。
E:建筑这一职业是否已失去生命力?
库哈斯:我曾经对建筑的前途感到怀疑,深重的怀疑,尤其是当我把建筑置于城市大背景下来看待的时候,就像蒙了一层黯淡无光的天幕,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那种幻灭感仍会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造访。但是你知道,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任何走过青年时代的人来说,怀疑主义是一段必经之路,你不怀疑这个,也会去找别的事物来怀疑。但现在我反倒看到更多的希望,建筑生长在文化里,同时也在塑造文化,同呼吸,共命运。
E:如果建筑能一直走下去,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库哈斯:让它成为一面镜子,映照我们真实的社会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