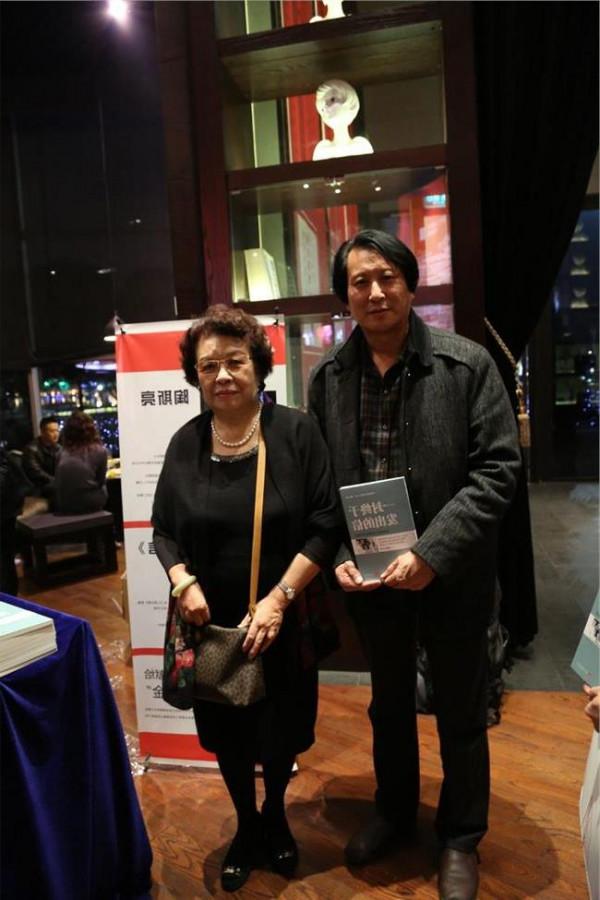无耻的曾希圣 关于陶铸 曾希圣的一些史实和感想
陶铸,在我心目中,是老一代党领导人中值得敬佩的一位。
武汉解放后不久,举行过一次地下党员和进城的党员会师大会,陶铸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陶铸本人,一口湖南乡音使我感到亲切,讲话爽快明确,给人一种为人正直的感觉,符合我对革命老干部的想像。当然,这只是一个刚从地下冒出来的青年党员的最初印象,不足为凭的。
后来,读了《松树的风格》这样一些短而隽永的文章,又发现了此人不仅是政治家,还富于文学情趣,所写的思想也是我当时所信服的,亲切感就更深了。
再后来,知道了1962年广州话剧歌剧会议上陶铸所起的作用。那次会议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虽然短暂,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给毛泽东否定了,却仍然确确实实是喜事。那次,陈毅、周总理都到会,陶铸是东道主。据说,当时传颂一时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之说是在会议之前就由陶铸向广东的知识分子们说过的。为此,我对陶铸的敬佩达到了顶点。
近几年来从书刊上读到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有关材料,却使我的感觉复杂起来。
下面就录下这些材料,对每件事的具体感想就不说了,因为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看到了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著名人物如陈毅、郭沫若、康生、杜国庠等人与陈寅恪的有关交往和陈氏对待他们的态度,读之对这些大人物,有的感到可敬,有的感到可笑,此处不多赘。
只谈作为当时地区最高领导人,书中涉及之处最多的陶铸。从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出,陶铸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例如,他知道陈寅恪爱听戏,就专为他买了一个高级的收录两用机;知道陈眼盲,就叫在陈的门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方便他散步;后来陈摔断了腿,为护理陈又派出了三个护士。
这件事有人不满,陶铸说:“陈先生虽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
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陶铸还指着那位表示不满的马副书记说:“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也一定给你三个护士。”快人快语,使人又感动又解气。
第二件事,是关于陶铸在文革中的沉浮之谜。陶铸在文革中一度曾被提升为第四号人物,不久又突然变成了第三号被打倒者,列位仅在刘、邓之下。这个谜该如何解?近读一篇文章是这样解释的:因陶铸在文革前曾对刘少奇不满,估计他会是一位打刘的干将,就被提升了,但提升以后,陶认为刘虽有错误,却还不够当作赫鲁晓夫打倒的资格,不肯落井下石。
因此,他本人就在转眼之间成了最大的保皇派,也进入被打倒之列。可惜我已忘记此文的出处,如果属实,当然是高风亮节。
第三件事,来自李锐《庐山会议纪要》上的记载,这件事却使我惊异,并产生了一种“不敬”的想法。庐山会上,彭德怀得罪了毛泽东,开始还不识相,一味辩解,许多人都来劝他检讨,当然都是善意,想让彭老总好好过关,陶铸也是劝者之一。
大家说的无非是尊重领袖、照顾团结之类的话,也有说得更多的。但陶铸说的一个道理却有些特别,他说:“我们入了党就和旧社会女人嫁了人一样,嫁了就定了终身,不能改嫁的了。
”我真不明白我所尊敬的陶铸怎么能说出这样荒谬的话来。当然,事实可能也正是如此,党章虽然规定有退党的自由,其实是不行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你虽然并不想退党,上级却来劝退,不开除,是一种优待的处理,如对吴祖光;二是你申请退党,却不许,因申请,开除以示处罚,如对戴晴、杨宪益。但从道理上讲,入共产党即如旧社会女人嫁人,对吗?
从李锐的书中看,庐山会议上的批评大多水平不高,而这些人大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可见没有道理,水平就不可能高。说话者有些本来就是浑人,有些却是有思想水平的,不得不作违心之论时,水平也自然难高了。
第四件事,来自牧惠的《<思忆文丛>引起的思忆》(《读书周报》,98年11月7 日),其中所引的陶铸的一些讲话,又引起我的惊异。文章写的是广东反右旧事,其中提到一个干部林鹏的冤案。
林鹏以一张《陶书记主观主义,干部受灾!》的大字报打成右派。大字报中引了陶铸1952年六七月间在华南分局对党员讲的一段话∶“我到广东后看出,广东地近港澳,封建实力浓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
因此我们估计广东地以上的干部全部是我们的,县一级的干部大部分是我们、小部分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则小部分是我们大部分是人家的。”林鹏认为这种估计前一半对,后一半大半不对。
这张大字报引自作者牧惠保存的1957年机关发给的《广东历史问题材料汇集》。此书所载另一份材料《关于地方主义问题》中还栽有陶铸同年7月6 日的讲话中有“地方武装不纯,更需大加改造”等说法,并指名批评“方方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剑英同志决心不大”。
作者牧惠也是当时广东较上层干部。他说∶“事实证明陶铸对广东地方干部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当时的南下干部曾把地方干部(土八路)称为‘旧基层’。建国初期‘清理中内层’时把一批地方干部以种种理由关押审查,虽查不出问题来仍逐出革命队伍。土改中更搞了不少冤假错案。……”
第五件,最近又读到曾在陶铸办公室工作过的马恩成的一篇文章(《百年潮》99年11期),说到陶铸在动员文革的报告(66年5月19日)中曾突然检讨自己的“右倾”。
陶铸检讨说:“在1962年之前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工作问题上,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61年到62年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会上我的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马恩成说:“陶铸指出的这两点,即他曾经搞过田间管理的责任制和那次创作会上的讲话,当时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因此提高了陶铸的威望。62年毛泽东提出反‘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后,陶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现在却否定了,还给自己扣了‘右’的帽子,这不能不引起干部们的震动。陶铸的讲话中还提出‘要保持晚节’,说‘我个人没有旁的要求,只求死后骨灰罐上能写上共产党员陶铸这几个字。’为什么讲这些?是否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干部们纷纷议论。”
显然,陶铸这时已经感到了深深的压力和矛盾,确实有了“不祥的预感”。
关于曾希圣
曾希圣是怎样一个人?老党员,老革命,这是无疑的。但他是“左派”还是“右派”?
最先使我对曾希圣产生比较深刻印象的,是58年《红旗》创刊号上关于河网化的文章。以我当时“衷心拥护三面红旗”的水平,读后当然极为鼓舞,感到安徽规模宏伟,形势一片大好。风头如此之健,曾希圣显系“左派”无疑了。但后来又听说他竟支持“包产到户”,而且因此挨批,吃的苦头不小。“左派‘何致于此呢?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一直未能解决。
直到读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人物》97年5 期),才大体知道了他一生业绩的梗概。
曾希圣是黄埔出身,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危难时期入党。全国解放前主要作军事情报工作,被称为我军情报部门的创业人。开国后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安徽是个多灾的省份,经常闹水灾。大水一来,老百姓纷纷出外乞讨为生,人称安徽是“乞丐之乡”。曾希圣到任后力求改变这种局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避灾保收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成绩非常显著。
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间,全省工农业产值从29·72亿元增加到43·19亿元,农民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曾希圣抑制不住高兴,说:我这个“乞丐头子”的帽子快甩掉了。
工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都到安徽视察过。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
但是,在成绩面前,曾希圣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于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了,不切实际的高要求产生了,强迫命令出现了,再加上全国也是那么一种热烘烘的的形势,很快,成绩转化为灾难。
这里只举两件事:其一,1956年安徽省党代会上有些代表对省委在改革中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提出批评,人民日报作了报导,省委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更正,结果,原报导只有六百字,刊出的“安徽来电更正”却有一千六百字。
由此可见曾希圣当时的得意和跋扈。其二,所谓“河网化”。本来可说是个好计划,目的在使涝灾得到根治,旱年也有水利灌溉的保证,但是工程浩大,需挖四十亿土方。
曾希圣最初提出时还比较客观,说是按实际能力计算,每年只能完成四亿土方,准备用十年时间完成。可是在当年冬天省委就制定了一个只用一冬春就完成八亿土方的任务,而且,一发动“高潮”,这个任务四个月就完成了,再战一个月,第二个八亿土方又完成了,次年2月,省委又提出了第三个八亿土方的任务,《安徽日报》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评论。
于是,一件好事完全办坏,工程粗糙,进度虚假,劳民伤财。农民从收秋后就不能回家,住在工棚,精疲力尽。
“整人”方面的“左”,安徽在全国也不落后。反右派时,安徽除在全省轰轰烈烈之外,还整出了一个特大的“右派反党集团”,其成员为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检察院长、副检察长等,打成右派的原因就是对曾希圣的那些做法提了不同看法,“反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庆祝“巨大胜利”的社论。反右倾时,又整出了一个副省长和省宣传部长的“反党联盟”,两次斗争都株连极广。
曾希圣从积极改革取得成绩而转为极左,他给安徽人民闯的祸比他办的好事更多。但是他在这段时期却一直走着红运。尽管毛泽东后来对他的河网化有些怀疑,说过“搞经济建设和作诗是两回事”的话,还嘲笑过《安徽日报》“端起巢湖当水瓢”的标题,但对曾希圣还是喜爱信任的。
当时在三面红旗招展下天下大难,曾希圣还被调去兼任问题也很严重的山东的省委第一书记,希望他能解决山东的问题,可见圣眷之隆。
但是曾希圣毕竟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那种安心以人民的苦难为基础向上爬猎取高位的人。他骄傲了,瞎干了,造成了祸害,在现实面前,终于还是睁开眼,醒悟了。
据说,使他清醒的有两件事。一是他曾回过一次湖南故乡。虽然当地干部早已做了封锁的布置,警告老百姓不许向曾书记胡说实情,但曾希圣这次的身份毕竟只是还乡的游子而不是统帅当地的大官,故乡总还有一些“老叔”们憋不住时会发出心中的愤懑,再说人们生活的疾苦也是掩盖不住的,曾希圣触目惊心,非常难过。再一件就是他在兼任山东职务时所见的实际情况。
湖南和山东的情况使他联想到安徽,他坐不住了,打报告请求辞去山东职务回安徽。
一个人如果是真心想了解真实情况,其实也是容易的。当时安徽人民的生活可用“饿、病、逃、荒、死”五个字来概括。曾希圣没有文过饰非,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了罪”,声言要“戴罪立功”。
这就是安徽实行“包产到户”的由来,当时按曾希圣的说法叫做“农业生产责任制”。
这次实行这个“农业生产责任制”,曾希圣是认真谨慎的,向上请示,向下调查,和干部群众商量,打消顾虑,事先表示如有错误由自己承担担子,等等。在层层向上请示时毛泽东也答复说可行,当时曾希圣高兴地说:“通天了!”
在向下调查中,曾希圣觉得拿不稳要仔细研究的是三个问题:1,责任制是不是单干?2,会不会造成两极分化?3,会不会加重农民的私心?这些问题,在调查研究后得到的都是正面的回答。
在和农民讨论责任制会不会加重农民私心的问题时,农民回答得特别干脆:“私心是有的,现在有,过去也有。不过过去是暗的,混工,争工分,不顾农活质量,不关心庄稼生产好坏,这种私心危害最大。现在的私心是明的,种好责任田,争取多得超产粮,这种私心和责任心分不开,对生产有好处。”
虽然这个责任制对生产有利,农民也欢迎,曾希圣仍不敢掉以轻心,他向干部提出了十四条防止重犯过去错误的事项,主要是不能蛮干,不能急于求成怕落后。看来,过去的教训曾希圣确已铭刻在心了。
安徽省做这件事当时是惊动了许多人心的。陶铸当时就曾说:“曾希圣在做一副大牌。可能赢个满贯,也可能输个精光。”
这副牌最初确实是赢了的,当年就立杆见影。粮食丰收,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非正常死亡现象基本消灭,群众说责任田是“救命田”。河南、山东、江苏等邻省群众纷纷来安徽买粮食。61、62年冬春河南从安徽买的山芋干达五亿多斤,陶铸和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专程到安徽表示对支援的感谢。
这副牌可不是赢了吗?但是,且慢欢喜。
1961年12月,全国困难稍稍缓和,毛泽东就把曾希圣找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露不同意的意思,安徽省委决定62年继续搞下去。
没想到,就在次年,在那个让大家“出气”、“看戏”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却被指名检讨他所犯的“方向性错误”,在曾希圣还没有回过味儿来不知错在哪里的时候,就被免去职务,叫他从北京直接移居上海,他请求去安徽告别,不被允许,而且,“任何材料都不要带去,片纸只字都不能拿。
”家属是由有关部门安排,在蚌埠上火车同行的。据他夫人余叔说,自结婚后,只见曾希圣痛哭过两次,一次是在听陈赓讲他哥哥被张国涛迫害至死的经过时,另一次就是在蚌埠火车上相见,曾希圣抱头痛哭。
曾希圣所犯的“方向性错误”究竟是什么?后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明确说明:说他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到上海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当然实际上是赋闲。文革中多次批斗,遭受皮肉之苦,不久便病魔缠身,66岁即去世。
也有人为曾希圣辩护,是邓子恢。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他公然说曾希圣搞的责任田不但不是方向性错误,而且是搞好集体生产的一条路子。但辩护的结果不妙,没过多久,邓子恢就给戴上十几年一贯右倾的帽子被批判,八届十中全会上更把他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干脆撤消。
也有人为邓子恢辩护,是邓小平,“黄猫黑猫论”就是在为邓子恢的辩护中说的,后来邓小平成为第二号赫鲁晓夫,这件事也不知是否因素之一。
胡耀邦当时对责任田曾持否定态度。八十年代初他任总书记时来皖,曾对当地干部说到这件事,他说:“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又说:“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后半生的经历。在他“极左”给一省人民造成了大害的时候,曾红极一时;在他醒悟认错决心“戴罪立功”,并已初见成效,为人民办了大好事的时候,却倒了霉,应了陶铸那句话的后半,“输个精光”了!
一些思考
上面这些材料,关于陶铸部分,是我在阅读的多种书刊中东鳞西爪集中起来的,关于曾希圣部分,则是一篇文章的概述。 这些偶然读到的材料,使我深深感到,人是复杂的。
当然,从道德品质看,人在根本上有好坏之分。但真要找到一个“全好”或“全坏”的人却也不易。陶铸、曾希圣应当说都是好人,但他们也都有错误和缺点。从他们,我还想想到其他许多党内的革命老同志。比如周恩来曾是公认的大好人,现在已在许多人中不无道理地被讥为“愚忠”,这样一个有能力、有知识而又搏闻强记的人怎么竟会“愚”呢?令人很难理解,其中或许还有更微妙的因由。
又如彭德怀,是对革命立过大功,后来又受过大委屈的人,人们对他都怀有敬意。
但是在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批了刘伯承,揪出一个以萧克为首的“反党集团”,直到八十年代才平反,萧克“反党”,就是因为给中央写信不同意彭德怀认为“军队教条主义严重”的判断。当时彭德怀并不以把萧打成“反党”为非,公然视自己为军队中的“党”,也应说是蛮不讲理的。据说他后来曾表示过歉意,大概是接受教训后醒悟的表现吧。
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他们人品中的“好”和“好中之坏”,他们的认识和行为中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无不带有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痕迹。有些问题,说是品德也可以,说是囿于某种在长期的“党的教育”和中国传统思想习俗熏染下所形成的“共识”也可以。
例如“愚忠”,就不止周恩来一人有,陶铸劝彭德怀时所用的那个“女人嫁人”的比喻也是一例。忠臣事主,贤妻事夫,都是以他人为“纲”——不管这人对不对——的封建思想。
在他们这样做和这样说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联想起什么是忠,什么是党,什么是领袖和人民,它们的关系又是什么的问题。是忠于党,还是忠于真理和人民?是党应忠于人民,还是人民应忠于党?党的领袖是否可如过去那样“朕即国家”、“朕即党”?曾希圣在“左”的时候是很专横的,但在“右”的时候却小心谨慎,打招呼,谈情况,讲道理,直到“通天了”才放心。
但在处理曾希圣这个人的时候却用不着那么小心谨慎了,不但毛泽东,就连柯庆施也可以为所欲为,那个叫曾希圣不得在安徽停留,不得带片纸只字的决定就是华东局作出的,不劳毛亲自吩咐。这又是为什么?和“朕即党”有没有关系?
又例如,对阶级、对知识分子、对地下党的看法,当时在党内实际上也是有着一种“共识”的。这三者有相联系之处,但也有区别,矛盾或悖论。陶铸曾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对陈寅恪优礼有加,但对“土八路”却如此严厉无情,“左”得可怕。同一个人的两种行为是否矛盾,为什么?和上述“共识”是否有关?
那个令人迷惘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那许多令人迷惘和忧心的问题更没有过去,因此,在读史的时候,在了解了更多的前人,特别是那些好的或“好中有坏”的前驱者的作为和遭遇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尊敬,同情,遗憾。
谴责,兼而有之,相互夹杂。对每一人,各种因素的程度也不一。所以我想,对于前人,与其急于作绝对的结论式的品评,还不如更多地思考,从他们的作为和遭遇中分析、研究和吸取经验教训。这一点才是十分重要的。
“八路”却如此严厉无情,“左”得可怕。同一个人的两种行为是否矛盾,为什么?和上述“共识”是否有关?
那个令人迷惘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那许多令人迷惘和忧心的问题更没有过去,因此,在读史的时候,在了解了更多的前人,特别是那些好的或“好中有坏”的前驱者的作为和遭遇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尊敬,同情,遗憾。谴责,兼而有之,相互夹杂(应全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