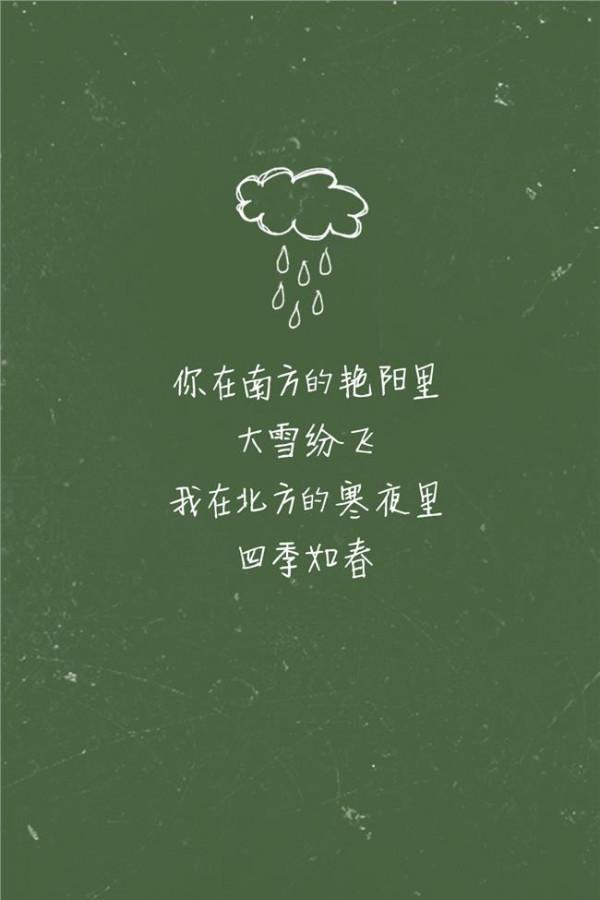马原牛鬼蛇神 读马原《牛鬼蛇神》:为一代人的青春和命运画像
“革命方知北京近”,这是“大串联”时人们爱说的“切口”,放在来自天南地北的两个少年身上正合适。
10年前,我曾骑自行车驮着陆星儿穿过巨鹿路老弄堂,去路另一边。陆星儿瘦瘦的,文静,平和,见面时微笑,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去年散步穿过,墙壁上贴写了一些名句,曾住在这弄堂的名人名录。我又记起沉静的陆星儿,很难想象十几岁的她,曾随几百万人流在那个大广场心潮澎湃,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曾握过伟大领袖的手,是那个时代的偶像之一。但,也在人流中的13岁沈阳少年大元,到底分不清哪一个才是老人家真正的身影。天安门太远了,迷蒙中,他们匆匆而过。40年来,大元一口咬定,中间那个就是。不为什么,他对自己有信心,坚信自己来到了,看见了……
无论什么故事,从天安门开始,从“零公里处”开始,总是一种神奇。
马原曾写过一篇自己长期都为之得意的《零公里处》,但后来人们沉迷于谈论他的先锋小说,把这篇作品遗忘了。过了30年,他在第二部长篇《牛鬼神蛇》里,把这个故事又说了一段。一个少年对道路的迷恋,对数字的执著,对广阔世界的好奇,是很多作家叙事的起点之一。
大元和在大串联中结识的朋友李德胜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寻找想象中的“零公里碑”。他坚信,每条道路都应该有个开始,这个开始就是广场中间的某一块石碑。但两个少年没有找到——道路的开始在某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隐秘历史,却开始在这里。
1966年9月,13岁的沈阳红小兵大元小学刚毕业,听二姐描述在北京串联受到伟大领袖接见的场景后,他瞒着家人搭上一列南去列车,倒吊在行李架上,目睹窗外“老铁路”母亲气急败坏地追跑着喊:“来信!啊!”红卫兵们大声哄笑,他刚发芽的青春,也紊乱地激荡。
在北京,大元碰上趁大串联一切免费的时机在全国各地游荡的17岁海南山民李德胜——几百万人浩荡,两人小概率地成了伙伴,继而结成莫逆之交——后来他们一直通信,持续40多年,从沈阳、西藏和海南这三个极端的地理位置出发,相互倾诉,彼此探望。这种大跨度的时空设计,在小说里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张力。
《牛鬼神蛇》不是一部关于少年和青春期的小说,那仅仅是一个开头。每个小说都有个开头,就像大元认定每条道路都开始于天安门广场一样。然后,无数的道路就出现在无数人的脚底下,在广袤的时空中,蜘蛛网一样交错纵横。
希腊神话里,把人生表达为命运女神的纺丝,是极为精妙的。人开始时,总以为路在自己脚下。走过去之后,发现路在身后。两个少年中,大元一直不停地到处走;李德胜回到海南山里,稳稳地待着,任凭人生起起落落,风雨来来往往。
有句话——“常识离事实最近”——出没在小说的各个角落里。小说中,主人公大元把人生中积累起来的各种重要疑问,都放在常识的维度上思考。他的挚友、串联结束后回到海南深山里结婚生子,十几年不再出门的李德胜,却靠神秘直觉来解决难题。
17岁前,李德胜从没出过山上过岸,在大陆发生的各种事情他都极为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犯了大忌。一走出海岛,他就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在全国各地漫游。
13岁的大元听他自报姓名时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敢?”
那时,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名字之一,可海南山民李德胜却浑然不知个中利害。当大元耐心地解释后,他也紧张了:和伟大领袖名字冲突,一不小心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人一起琢磨了很多替换名字,但发现都不理想。一个名字附着在人身上,要改掉是很困难的。名字的魔力,在大元给李德胜的小女儿起名李小花的很多年后又一次浮出水面。但那是小说后话,得读到最后一章,读者才能恍然大悟。
那个牵动几千万人在960万平方公里大规模移动了半年之久的大串联运动,把这两个男孩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分享着喜悦和沮丧,交换着疑惑和信心:“……那天晚上回到住处,大家为到底哪个位置是毛主席争论不休……大元咬定,中间的那位才是毛主席。不然为什么站在中间呢?不然别人为什么与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呢?”
要问为什么的时候,在人的一生中还有很多次。
马原仍然一开始就想到了问:人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
马原小说里充满了各种生动细节,而细节在人生及小说中同样重要。
“李德胜”这个名字引起的震惊,也是细节——大元说:“你怎么敢?”
在中国新时期小说家中,马原是最早有意识地确立叙事者权威的先驱者——“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
在叙事上,马原对小说充满信心。小说中人物性格发展、命运走向、故事结局,他都有强烈控制欲,并且总能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独裁者叙事。在空气澄澈、阳光无限透明的高地上,马原以自己的叙事语言,把他对西藏的感悟和交缠着现实和梦幻的世界,一样样地呈现出来。
但来到平原后,马原产生了醉氧反应。在小说里建立起的叙事者权威,在平原地带神秘消解了,同样被消解的是语言方式。在平原,人生不再有多向性,马原可能被冗余语言缠绕得失去了表达信心。
小说家失去对现实的细节感知,失去了语言的控制,就可能失去叙事的信心。一个人的人生中失去了细节,同样也会失去表达的兴趣。
在他那一代作家中,马原对语言有一种类似洁癖的精炼。1997年3月作家出版社的四卷本《马原文集》,依次题为《虚构》、《旧死》、《爱物》、《百窘》——四本书共八个字。第四本《百窘》里,收入了马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这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被淹没在那个时代的喧嚣中,在浪花泡沫中沉浮,只成为少数读者记忆中的黄金。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马原可能面对着一个“百窘”的内心世界和外部难题。
《百窘》是一篇自问自答式散文。这篇问答是进入马原精神世界的一百条捷径——没有之一。在问答里,他思考了一名小说家所能想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小说历史、小说经典、小说评价、小说技法、小说秘密……这里的很多“窘迫”,都体现出一名卓越小说家对阅读、人生、世界、未来的深入思考。他不给出答案,甚至没有答案的路径。
马原似乎被这些疑问压迫得失去了表达的兴趣或能力。只有通过在大地上持续行走的方式,马原才能消解这种大山般的重压,并在行走中,把曾经思考过的所有问题,继续一条一条地思考下去。因此可以看到,在马原小说中干净的语言背后,有多么沉重的精神和哲思负担。
一个人可以思考任何问题,远与近,生与死。但对一名优秀小说家,最终仍会回到自己的内心。就像马原写了那么多小说之后,全都喧腾着冲着汇入《牛鬼蛇神》这一汪波光粼粼的巨湖中,湖中,有一条巨大的湖怪在出没。
《牛鬼蛇神》这部长篇小说,我读完之后,曾认为是:“新生命的赞歌。”很主旋律,但确实如此。又或者,是“对生命的感恩”。还是很文艺,很温馨。
在这部小说里,马原把他自己原来曾有过的种种思考,从头到尾又完整地重新梳理了一遍,并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再度罗列了一遍,好像八角街那些骄傲的康巴汉子一样,稳稳地端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珍宝,与你四目相对,脉脉暗流涌动。
他甚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写过的小说大段拷贝过来,镶嵌成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来自《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死亡的诗意》、《西海无帆船》、《冈底斯的诱惑》等小说里的段落,频繁闪现。这种做法可能会遭到一些读者的诘问,以为是滥充字数。
判断是不是凑字数,要看这些文字和整部小说叙事之间是否有排异现象——但在西藏,出现了海南山民李德胜,一切就产生了改变,包括叙事的语调。李德胜是这篇小说中的盐,他让这些貌似陈旧的材料,变得有滋有味。
仔细分析下来,我发现马原的小说语言经过20年的潜伏之后,竟没有明显的改变,他现在的文字和20年前的文字完全可以无缝衔接。可见,在20年前,马原对小说的思考就已经到达了他自己的尽头,从而出现了小说向何处去的困惑。
在《牛鬼蛇神》里,马原采用复踏的方式,再次把自己的原有经验重新梳理了一遍。13岁的大元和17岁的李德胜后来各自回到故乡,但一直保持着通信。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大元来到西藏,爱上了八角街,在拉萨的透明空气下行走,为西藏广袤的天空所激励。
这时,山民李德胜则一直住在海南深山里,和毒物为伍,与凄厉命运作伴——他结婚,育儿养女。一个女儿被汽车撞死,一个儿子生下来残疾被他自己亲手溺死。他的晦暗人生和大元的透明世界,形成尖锐的叙事对比。
大元对李德胜的森林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在通信十几年后,他终于设法来到海南,住进了李德胜专门为他搭建的树屋里,听见丛林的声音,目睹了壁虎的爬行,思考了人生。若干年后,李德胜来到西藏,在大元和他的朋友的陪同下,遍历西藏诸界。
李德胜有一种大元一直无法明白的直觉能力,他很简单地就把大元无法理解的《古兰经》句子解释清楚了。他的锋利理解力,能从命运的迷雾中,直接看到暧昧的真相。无论是黑猫、雪人,还是神树,与他都息息相通;无论是海南本地的神秘巫术,还是高原的生死迷藏,他都能轻松穿越。
一只奇诡的蜻蜓,飞越了浓云缠绕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来到李德胜的手上,被他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了那位只有深夜才在八角街出现的高大康巴汉子。
回到海南深山里,李德胜以给亡灵制作精美的礼品和给亡灵建造纸扎宫殿为生计。他的人生,在巨大的圆圈画过后,恢复静寂。
大元接着来到了平原,他的身体出现了不适和眩晕症。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变得散乱而模糊不清。
但这两个少年在40年前开始的深挚友情,注定要在海南的海天之下,以令人感恩的方式开花结果——几乎走投无路的大元,在人生的最晦暗阶段,遇到了自己的比德丽采——她引导但丁遍历炼狱——海南田径运动员李小花。她的生命之光,照亮了大元最幽暗的角落,使他重获新生。
而这个神秘的女子,是李德胜的小女儿。她的名字,是20多年前大元第一次来到海南时给她取的……
很难想象马原会以这样的方式,沿着过去走过的道路,写出了一部经验和细节似乎很多重复,但读完之后你会觉得截然不同的长篇小说。什么东西在这里产生持续的魔力,而使得这些貌似陈旧的细节,闪闪发光呢?什么样的金属,在叙事的河床中沉淀下来?
马原在《百窘》中评价安德烈·纪德的中篇小说《窄门》时说:这是一部你读完后钦佩不已的小说,却不知道为何如此钦佩。
我反复地阅读《牛鬼蛇神》,觉得一切都正常。但读完之后,只剩下钦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