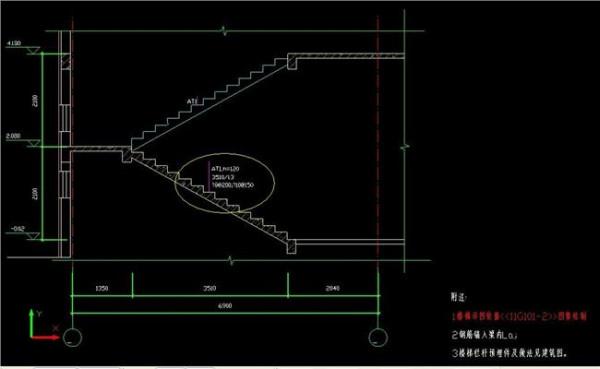傅国涌教育是什么 什么是更好的教育
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或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最美好的东西,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而不是在那里“跑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慢”,“慢”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 本报记者 梁慧
前不久,哈尔滨香坊区举办了“慢课堂、慢教育——生命化教育的区域行动”研讨活动。在这次活动中,知名学者傅国涌作了演讲,受到欢迎。本报记者近日从学校教育的现状,教师、学生为何不像先前那样快乐,当今教育面临的困惑以及到底该做什么样的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对傅国涌先生进行了专访。
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就是培养普通人《教育时报·管理周刊》:对于教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它是对一个人的培养;有人认为,它是教人怎么做人;等等。
结合我国的教育现状,您是如何理解教育这个概念的? 傅国涌: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了一个字:只有“教”,没有“育”。
如果我们把“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 自孔子以来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单一的经典教育。它有优越性,同时也包含了人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诗词歌赋,每个人从小就受到伦理、审美的熏陶。
但是直到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那一年,两千年来的中国只是在原地踏步,只有这种单一化的经典教育或者人文教育模式,跟不上世界的脚步。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
这套教育是从希腊发源出来的,它的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学、历史、哲学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又加上了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是3大板块: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近年来,速成教育有愈演愈烈之势,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在我们当代的教育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我们常常觉得教育在追求“快”,为什么?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
人文教育是讲究“慢”的,是注重生命的,但人文教育过于单一化,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可是,当我们把教育带到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上来的时候,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这就回到了我们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我们的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
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就是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是以普通人为本,尤其是基础教育。 没有教育家型的校长,学校就没有灵魂《教育时报·管理周刊》:在中小学,一些学校管理者为了提升学校的名气和升学率,不惜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来抓分数,甚至有些学校还设定目标。
您对此怎么看? 傅国涌: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学生的目标。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
所以,在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教师快乐的过程。然而某些地方却恰恰相反:学生不快乐,教师更不快乐。 过去,对教育的主体认识有很多分歧,我认为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
如果教师不快乐,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教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那么高,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生命尊严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失败了。
何为师道尊严?就是教师在这个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学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失败的。
很多时候,那些衡量指标都是不可量化的。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能否举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 傅国涌:民国时期的教育,虽然那时有战乱、动荡,但是它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教师得到了尊重,学校得到了尊重。
那个时代的学校大部分是由教育家来办的。那时,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和教育部部长之间是可以来回互换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部长,也多次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京大学校长。
他们并不觉得校长和部长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京大学校长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行政职务,而是一个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我想到几个人:张伯苓,南开大学的校长,但我更愿意说他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事实上,张伯苓办得最成功的学校可能还不是天津的南开学校,而是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南开中学;林砺儒,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后来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49年以后做了教育部的副部长。
我倒觉得他不应该去做副部长,他最适合的岗位是校长,而不是部长……这样的人,在民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批。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办出了一批很有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
所以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是由中小学所决定的,而这些教育家就是这些学校后面的灵魂人物,他们是掌舵人,没有他们,学校就没有灵魂。 求“慢”是一种理想《教育时报·管理周刊》:您刚刚提到了民国时期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与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何区别? 傅国涌:我在看民国教育的史料时,特别感到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
一个人可以以终身做小学教师来作为他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
所以,中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们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决定一个教师、一个校长、一所学校地位的是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自成体系。
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独立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这也就把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消解掉了。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或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最美好的东西,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而不是在那里“跑步”。
所以,我们要说“慢”,“慢”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这也就回到了我们的主题:“慢课堂、慢教育”。
傅国涌:我想起一个故事。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家美籍华人办的企业。这个企业的食堂门口有一片草坪,要进入这个食堂,必须要绕一圈才可以。但是,员工都不愿意,他们就在草坪当中走出了一条路,一条最短、最快的路。
这个老板后来在草坪中间种了一棵树,恰好挡住了这条捷径。然后他告诉员工,在这个公司,倡导不走捷径,用一棵树作为标志。他倡导的正是一种“慢”的观念。在一个人人都求“快”、走捷径的时代,求“慢”就是一种理想。
做把人当人的教育《教育时报·管理周刊》:民国教育是否还有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地方? 傅国涌:今天看民国的教育会有很多看点。上面阐述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看点:教育的独立性。另一个看点就是:它是人的教育,它把人当人。
在台湾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知识分子,叫殷海光。我到台湾参观他的故居时,进去看到的第一条便是他笔书的格言,当时印象特别深。由于他是研究逻辑学、伦理学的,因此就更加关注基本性的问题。
他说:“自由的伦理基础是把人当人。”我想把这句话借过来说: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把人当人。 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当所有人都往同一个方向上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 《教育时报·管理周刊》:这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些教师找不到职业幸福感,甚至对职业产生倦怠的深层原因吧? 傅国涌:当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本能设计的,但教育是与本能为敌的,教育是要提升人的,而不是按人的本能来行事,不是按人的本能来思考,而是要把人变成一个有能力驾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级族类。
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有高于本能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按照本能去做,动物也有本能,甚至强过人类百倍。
所以,人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本能,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通过教育提升人,通过教育让人超越本能、实现自我。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都是与这样的本能化趋向为敌的,是为了抗衡人类堕落的趋势而存在的。
如果只是为了迎合本能的需要,那就根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进学校。所以,自孔子以来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类一代一代积累的最好的文明成果告诉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己,让我们更加靠近文明。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多地往这个方向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