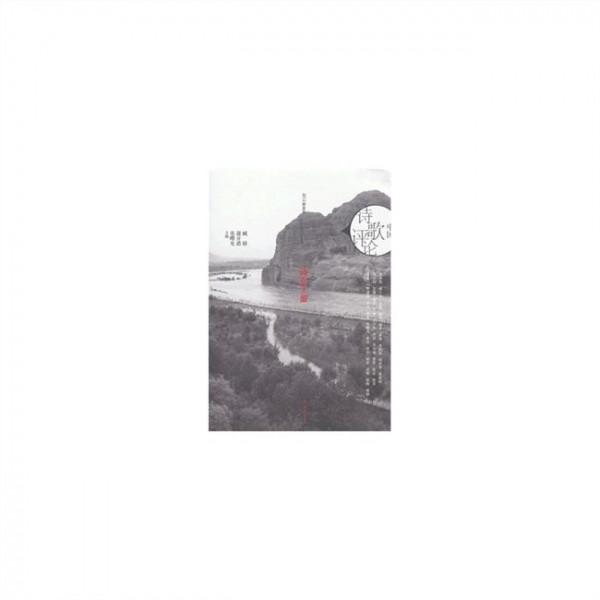臧棣臧克家 儿子眼中的臧克家
“不管我的创作上有成功, 还是有失败,我始终是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上是很短的,对一个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一生都献给了诗,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他经历了中华民族苦难与变迁的全程、经历了国家百年沧桑巨变。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如今写诗的老人终也走完生命的全程,安详宁静。
2月5日,一代文学大师臧克家走完了百年人生,带着没能在这位诗人生前走访他的遗憾,我们走进了臧克家的灵堂。对于安排在灵堂里的采访,我们的心中有着更大的不安与缅怀。臧老的儿子臧乐安第一次以亲人的身份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臧乐安先生说父亲生前就喜欢吃花生米、大葱大蒜,而在灵前,正摆放着这些东西。
臧老写诗凝神的表情、永远和蔼慈祥的笑容又一次浮现在我们眼前。 亲人眼中,告白的是一个故去的人,这比起任何的苦难还要惊心动魄。
但回忆本身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痛彻心扉的酸涩,更包含着对即将远走的旧梦的牵挂与不舍。无论是亲人眼中,还是常人所感受到的,都将穿越时空,带给故人深深的慰藉。因为不论时光如何飞逝,诗人的呐喊声永不消退。
岁月带走身影,却留下永恒的笑容…… 父亲写诗,有着家庭和环境的因素 父亲写诗,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当时的历史情况。最重要的是参与了当时中国社会动乱一百年的沧桑变化。他出生在1905年,当时是清朝的末尾了,他15岁以前生活在山东农村,天天和农民的孩子泥里、水里滚在一起,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
原来我们家是个封建地主家庭,老爷爷和爷爷都很懂古诗,而且经常给他念诗。七八岁的时候他就能背诵许多古文古诗。
我老爷爷一朗诵起诗歌来,人就变了个样,像敞开了心灵的闸门一样。父亲说,当年听爷爷朗诵白居易的《长恨歌》时,听了虽然不完全懂,但是莫名其妙的非常感动。他在农村头一次产生朦朦胧胧的爱情的时候,老爷爷就给他写了首诗,用诗来劝戒他:“青蚕栖绿叶,起眠总相宜。
一任情丝吐,却忘自缚时。”也没有当面指出他这样怎么不好,就写了这样一首诗交给了他。所以这就是家庭影响。 我父亲的爷爷对长工特别严厉,大家都很怕他,我父亲常常为家里的长工求情,因为他从小跟农民的孩子玩在一起,对农民有着深刻的感情。
他后来写《老哥哥》时,“一文三洒痛苦泪”。老哥哥就是家里的一个长工,“祖父是在他背上长大,父亲是在他背上长大的,我呢,还是。
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他是祖父和父亲的老哥哥,他是我的老哥哥。”最后老哥哥老了,“祖父最会打算,日子太累,废物是得铲除的,于是寻了一点小事便把五十年来跑里跑外的老哥哥赶走了。
我当时的心比老哥哥的还不好过,真想给老哥哥讲讲情,可是望一下祖父的脸,心又冷了。”他对老哥哥寄予了无限的同情,文章所讲的话都是双关语,这就可以看得出他背叛地主阶级,完全转向了农民这一边。 1926年他约了同伴背着家人去武汉投奔革命,走前,他给爷爷写了封信:“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
”就这样,一个“心潮澎湃正青年”的父亲就告别了家人,去了武汉,考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经历了讨伐叛军,被国民党追捕,之后上了山东大学。
受大革命的影响,他始终是向往光明。这些都影响了他以后的诗文道路。 那个时候受白色恐怖的压迫,父亲感受外界特别敏感,但又不能明着写,所以他就把形象压缩到极致,写得非常深沉,比如《老马》这首诗:“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有的人说,这首诗写的是中国的农民,有的说写的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还有人说写的是他自己。
他认为,都对。一首诗写出来,就是社会财富,压缩得越精细,内涵就越大。读诗的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领会出不同的境界。他的诗写得非常精练,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表面的感情张扬,实际上包含了多少的火热。
父亲最看重的还是诗文创作,他把写作当成生活的必须,因为身体不好,写作时间基本是早上起来天不亮就出去散步,回来开始写。他是走着路也想,吃饭也在想,睡觉也在想,想诗。
有时想起一句诗来,半夜起来拉开灯也要写,正所谓“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 有人说:臧克家浑身都是诗。诗对于父亲来说就是他的生命。“诗言志、诗表情”,他把所有的感情都通过诗表达出来。
他不主张诗写言不及义的内容。他认为,作为一个诗人,不能反映当下的时代,愧煞人了,还当什么诗人。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无为而治” 父亲在生活上非常朴素。他曾给我出过一个题目,让我写文章:《勤俭家风》。在我们这些子女的印象中父亲的袜子补了又补。
坐的藤椅,藤都断了,补上接着用。解放初期买的人字呢大衣,袖口都磨破了,还一直穿到住院前。我曾给他买过两件大衣,他也不穿。他说,能穿为什么不穿呢。穿得那么好有什么用,只要得体就行。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在朴素这点上,都是受父亲的影响,穿的衣服都很朴素。 父亲在教育我们的问题上,是“无为而治”,不强迫我们做什么,只是身体力行地做我们的榜样。他和我们说过,你们在外面不要以我的名义去搞这搞那。
我们都是非常自觉的,从来不用他的名义,我到了单位,从来不说我的父亲是臧克家,单位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臧克家的儿子。我的父亲自己是艰苦奋斗,干什么事都是执著追求,他说你们自己也要好好干。
父亲还有一点就是言必信,比如别人向他约稿,只要他答应了,就肯定写,你不用催。有一次,毛主席发表一个诗词,文汇报派记者来向他约稿,其实当时他已经答应了别人的约稿了,就告诉她说不行。这位记者就说,我们那个版面留着,我要是拿不到这篇稿子就完不成任务了。
急得就要哭。父亲一看说好吧,那我把稿子分成两半,给你一半给别人一半。他是非常守信用的。书协想让他加入成为会员,他说我是作家不是书法家,不能入,他对名利也看得很淡。
我过去上班的时候,我父亲多次住院,他从不要求我请假去看他,我经常上夜班,白天下班去看看他,很少请假。他说我知道你工作忙,做新闻工作,得争分夺秒,他非常理解我们。 父亲干什么都特别认真,要是认准一件事,非得破命的去追。
他叫我们办个事情,送个东西,立刻就得办,其实第二天办也没关系,他想的是这件事办完了,也就了了,否则他老挂在心上老想着。要是说下午开会,他准是一上午都躺着不起来了,要养精蓄锐。
有时候父亲和我说起来,觉得遗憾的是,没有教我们古文,我们的国学修养太差了。他晚年还和我研究诗的平仄。最简单的平仄常识我知道,但是和父亲讨论起来,差得太远了。他写了关于家乡山水的诗:“五岳看山归来后,还是对门马耳亲。
”他问我合乎平仄吗?我都说不出来。虽然父亲没有过多指导我们,但耳濡目染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父亲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老想着台湾统一的问题,我以前也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我去看父亲时他就和我聊国家大事,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他非常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一辈子忧国忧民,住院清醒的时候,见了我还问伊拉克问题怎么样了。 他曾说,朋友是我的半壁江山 “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这正是父亲做人的写照。
父亲好交朋友,他的朋友从老人到小孩,从高级领导到布衣百姓都有。他原来住在赵堂子胡同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出去散步,街坊邻居都认识他,不分老少,都愿意和他做朋友。孩子们看见他,就问他“臧爷爷好”,他兜里揣着糖块,就从兜里掏出糖来给他们吃。
我有个同学,她有个小女儿,五六岁就开始写诗,我父亲看了她写的诗,说哎呀,好极了。逢人就夸,他对待朋友真是掏心了。 我小妹妹曾写过文章:我父亲的亲情和友情天平上,友情的砝码更重。
他的身体长年不好,从50年代开始,每天卧床休息的时间多,有时身体不好,只能起来工作两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卧床休息,有朋友说我来看你,他躺下也睡不着,老想这个事。要是来了一个朋友,见了面,他热情得不得了,手舞足蹈,聊得滔滔不绝。
一个朋友走了,第二个朋友来,精力就差了一些,但依然聊得很高兴。第三个朋友来,他觉得精力不行了,便赶紧回到屋里躺着。有的时候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很小声的对我说,今天不能和我说话了。
我就知道肯定又接待了朋友。有的时候他就告诉妹妹和妈妈,让她们帮着挡挡驾。有人来了,我妹妹就在客厅里和来宾说,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出来见客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跑出来了。他就像是一团火,这是他的为人,也是他的性格,是诗人的气质。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锲的小女儿张苗,在小学六年级就采访过我父亲,现在上初三,那天来了。问她,臧老给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她先说“热情”,接着说“天真”。
有人问她什么叫天真?她回答说,和臧爷爷在一起很开心。 他曾说:“朋友是我支撑感情世界的半壁江山。只可惜随着年华的流逝,许多至诚至信的老友都相继离去。没有比朋友的故去更牵动我的情思了。”他也替朋友写过很多悼念的文章。
为了朋友,可以不惜一切。我们有时候说爱护自己一点儿,但一为了朋友,他就在所不惜。 他与季羡林是老朋友,都是山东人,1946年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相识,相交。以后每年过春节都要聚一次,不是初一就是初二,季先生必定要来家。
有一次季先生就说,以往我们都是一年见一次,但岁数都这么大了,还能见几次,一年改成见两次吧,国庆节再聚一次。说是说了,但实际上都做不到,我父亲身体一直不好,他很少出去拜访朋友,他也很抱歉,但也没办法。
老朋友都知道,他午间休息的时候从不来看他,有一次一个老朋友来看他,一看他在屋里躺着,就知道他身体不舒服,在休息,马上转身就走,他们朋友之间真是肝胆相照,一辈子都是互相关心。
父亲90岁前后的时候,有一次,他上街散步突然头晕就要倒下来了,过来个街坊给扶住了,后来检查说是脑血管硬化,有脑血栓的征兆,我们就不敢让他出去散步了。一次我跟父亲说我陪您散步吧,他说:“不要不要,我自己散步心情很轻松,想我愿意想的事,你陪着我我还得想着你,还得管你。
而且街坊邻居都认识我,不会出事的。” 往事如梦如歌 我和哥哥一生下来就送回老家了,让祖母和姑姑照顾着。因为父亲在临清中学教书,一年顶多回来一两次。
我们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诗人,对他的印象就是穿着一件长的大褂。他回来了我们还都挺害怕,一看到他,以为家里来客人了,就爬到树上躲起来。有人问我们怎么不回家,我们就说,家里来客人了。有一次,我父母回来以后,开始给我们小人儿书看,给我们画图画的彩色笔,但一说要带我哥哥出去上学,我们什么都不要了。
都要上车走了,我哥哥说什么也不去,我也吓得趴在床上。因为从小是姑姑带大的,对父亲不是特别亲。但后来长大了,父子之间的感情也很自然了。
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参加革命以后,父亲到济南开人代会,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我刚订了一个小本,他给我题了字:“你是英气奋发的一匹小野马,你所具有的正是我所缺乏的。
今天,你这匹小野马找到了一个可供驰骋的自由的原野,你必须为你的主人———人民俯首帖耳地服务,对你,我存着有一个大希望,千万不要叫我失望啊,我的,我们的小野马呀!”当时我刚参加革命意气风发,他的这个题词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这个本子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还让父亲给我把这几个字写成了一个条幅。
“文革”时父亲受到打击,临去干校的前一天,我给他收拾东西,我去给他买点菜,买了个小烧鸡、一条鱼,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我跟他说:我明早过来送你。第二天我们把父亲送到火车站,父亲上了火车后,我就跑到火车头前面的位置,这样我向他告别的时间就可以再长些。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他这一走是否还能见面,结果火车开过去,我没看见他。
他也没看见我。当时真是有说不出的那种心情,生离死别的感觉,很是辛酸。 我的记忆中,他总是鼓励我,肯定我,我到前苏联当记者之后,发回稿来。他便写信告诉我说,“经常听到你的广播,乐安活动能力还是很强的,到那儿一个月就发回稿了。
”2002年我去参加十六大的翻译班子,回来以后我把从大会上带回来的两枝笔送给了他,他很高兴,说:“你能参加这个翻译班子,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 现在回想起来,唯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小时跟父亲在一起的机会太少了,也没能像别的小孩子一样在童年时代享受到充分的父爱,而且再也不会有那个机会了。
这是永远的遗憾。那是时代的特点,也是时代的原因。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诗,献给了他自己热爱的事业,但是父子之间最浓的血缘关系并不能因此而淡化。
作为一个儿子,父亲虽然离去了,但现在我想说我最深切、真实的想法:无论如何,父亲在我们心中是个好父亲。我将永远牢记父亲的嘱咐:俯首帖耳地为人民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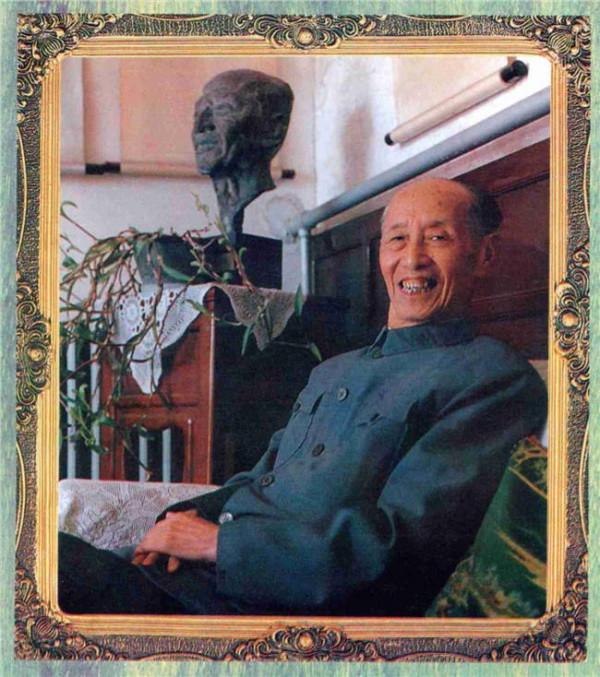









![臧棣骑手和豆浆 骑手和豆浆:臧棣集1991——2014[当当]](https://pic.bilezu.com/upload/9/70/970f22bd6b62395362180b81e012ec97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