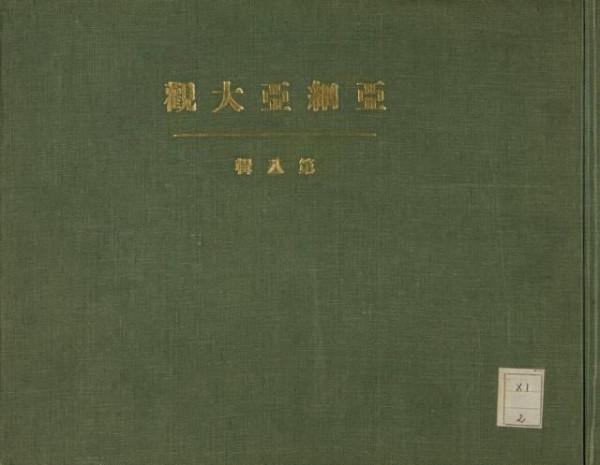杨宪胡惟庸 杨宪益与戴乃迭:惟爱永恒
戴乃迭晚年曾写过一篇英文自传(可惜没继续写下去),其中谈到了她与杨宪益的爱情与婚姻。我在写《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时,曾将之翻译引用于书中。这位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传教士的女儿,美貌惊人,她与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相爱,但遭到母亲反对。
“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 母亲这样严肃地警告她。 但她还是选择了杨宪益,并随他回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从此,她的命运、 她的事业永远与杨宪益合为一体。
只是她没有想到,母亲的警告成了谶言。“ 文革” 期间他们夫妇遭遇牢狱之灾,儿子也因此而患精神病,后来自焚身亡。可是,晚年戴乃迭仍不后悔选择了杨宪益,她在文章中这样说:“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这是两个人半个多世纪的情缘。它是真正属于个人的相知相爱,早已超越了国界,没有了丝毫世俗的、物质的气味。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戴乃迭患老年痴呆。几年时间里,杨先生谢绝了许多聚会,一次也不到外地去。他说,他要好好陪乃迭。
这两天,我找出一封杨先生一九九七年写给我的一封信,唤起我的记忆。信中写道:“我目前因老妻有病,整天坐着陪她。什么事也没做,除了家务事而外,也从未给朋友写信,也无法出门,电话倒是常打。但您的电话我也没有,有空欢迎来玩玩。……”
我去了。他们住在友谊宾馆的一套公寓里,此时戴乃迭衰老得完全变了一个人,不能交谈,坐在轮椅上,呆呆地看着我们。杨先生与我谈话时,他总要常常转过身看一眼她,还站起来去喂她一口水,再拿小手绢帮她擦擦嘴角。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中旬,戴乃迭因病去世。杨先生很难过,甚至说,他的生命也等于跟着走了。随后,他赋诗一首:“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一位朋友将这首诗书写后裱好送去,他挂在卧室里,与之整日相对。这首诗,一直挂到了今天。
戴乃迭去世后,亲友们都在想办法如何帮助杨先生散散心,尽快摆脱痛苦。当时,郑州有一个越秀学术讲座,由沈昌文先生与郑州越秀酒家合作创办。这个讲座一直由沈公主持,后来他忙,便邀我协助他,每个月请一两位文化界人士前去。我与杨先生商量,请他去讲一次,讲什么都行,顺便去开封转转。他迟疑后同意了。演讲题目定为《中国诗,外国诗与打油诗》。于是杨先生有了一次河南之行。这一年,他八十五岁。
这次河南之行,我与杨先生商量写写他与戴乃迭的故事,他很高兴。回到北京,将这次的谈话整理出来,起了这样一个标题《那些得意伤感悲哀的往事》。
其实,得意、 伤感、 悲哀,三个词汇远远不能概括杨先生一生。他的外表与内心,有着强烈的反差。何况,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文革”之后的杨宪益,他过去的性情如何,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推定,儿子杨烨的不幸结局,应是对他们夫妇的最大打击,这也是他们人生态度的转折点。
朋友们感觉到,从那时起他们仿佛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酒喝得更多了,更频繁了,但他们两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离。自那之后,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他们看得更淡,人从此也过得更为洒脱。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地,书架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更别说凑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判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
举行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晚上,吉林卫视“回家”栏目,为寄托他们的哀思,特地重播了四年前拍摄的专题片《杨宪益戴乃迭:惟爱永恒》。
面对镜头,杨先生沉着而从容,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讲述自己与戴乃迭的故事。他的话语不多,但却言简意赅,富有含蕴。
节目结尾部分,采访者问:戴乃迭的骨灰是如何安排的,有墓地吗?
杨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慢慢说:“都扔了。”
“为什么不留着?”
他指指烟灰缸,反问:“留着干什么?还不是和这烟灰一样。”
这是片子的最后一句话。
听说,杨先生的骨灰最终保留了下来。其实,对于他,物质的留或不留,没有区别,也不重要。他早就迫不及待地赶去与戴乃迭会合,如今,两个灵魂完全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