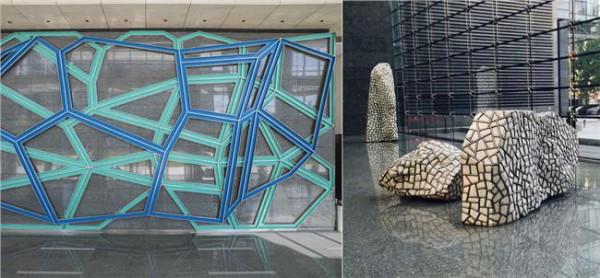隋建国老婆 隋建国:这个时代老中青年艺术家面对同样的困难
隋建国1956年出身于山东青岛,其成长是刚好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对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质的。作为特殊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群体,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在后来的艺术上都或多或少在其一生中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从川派的陈丛林、何多苓、罗中立,张晓刚,到北方艺术群里的王广义等等。
隋建国也是这一群中的一位,他的雕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和毛主席以及他的遗产“掰”关系,文革对这一群体艺术家的影响巨大也深远,让我们看到了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特别的故事:
隋建国口述:
我的青年时代与我自己的成长
在我青年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1972年我十六岁便进入青岛第一棉纺织厂,成为一名工人。当时的感觉是文革永远都不会结束了,因为毛主席说:这样的文化革命要不停地进行,这样才能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我当时想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做好了一辈子当工人的打算。
为了有点儿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我拜在了刘栋伦老师门下学习中国画,也算对自己这辈子有了个交代。刘栋伦可以说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学习画画的想法就是有点儿业余生活,在工厂里面,会写会画还能搞搞宣传,还能工作的比较轻松一些。
但我的老师告诉我:“你要是想搞宣传,就不用跟我学。”他是一位极具文人气质的先生,但是家庭成分不好,所以在那个时代不会有任何机会。
所以1977年他却鼓励我说:“你还有希望,将来大学恢复招生,而且不再讲家庭出生了,你应该去考大学。”这位启蒙老师不仅仅是我绘画技法上的启蒙老师,还教会我怎么去理解中国文化,怎么学习做一个中国式的知识分子,他为我将来走上艺术这条无穷尽的探索之路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他首先让我学会了如何去做人,去继承中国文化。
77年恢复招生的时候,我还不会画素描色彩,只会画水墨画。所以考大学是一切从头来过,重新学习素描、色彩,文化课。80年,我24岁的时候才考上山东艺术学院,那个时候考大学的年龄限制是25,再晚一年我就丧失资格了。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学生,而已经是一个青年艺术家了,就是去到学校就是去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
一个时代的精神导师:毛主席
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来说,最大的导师就是毛主席,他是所有人的精神领袖,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是毛主席的拥护者,也都是文革的参与者(不光是受害者)。
直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的倒塌。这种影响与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我的祖母一辈,像我的岳母,她们抗战的时候是军人,对她们来说是真正的倒塌。后来她们出国,看到了我们要建设的共产主义,在国外早就实现了,那种震惊与打击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的我也很悲痛,但随着文革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摆在眼前,看到一个那么完美、伟大的人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打垮了。文革结束后,我虽然上了大学,走上了艺术的道路,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条路,不会再像以前对待文革时那样的狂热了。
虽然文革结束了,但它的影响在我身上却一直持续,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与毛主席的遗产共同生存,对自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
“香港回归”前后,兴起了讨论中国一百年近现代史的热潮,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现《中山装》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真正反省我自己跟“社会主义”,跟“毛主席”的关系。这就和80年代的反思不一样了:以前是群体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在反省的是我自己,以及我自己和社会制度、精神领袖的关系。
选择什么表现对象来做作品,出自我的反省需要。但这件“衣钵”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穿在某人身上的,表达某种简单或复杂的艺术家个人情绪的物化体。
它是一个容器,将历史与现实装在其中。一直到2003年,我做完《睡觉的毛主席》,我跟毛主席的关系才算是撇清了,我意识到,毛主席也不过是个人,也会犯错,是个人犯了错就可以理解了。
现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自己的独立,而不是去折腾别人。05年以后,我的艺术与之前的反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告别了。我已经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而我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也搞清楚了,比起以前会习惯地将自己的命运归结为大的社会背景环境,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自己不够独立,开始学会面对自己,面对人的生命意义,有关人应该怎么活,怎么死?其实这也就是艺术要去探索的问题,能够在实践中去发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