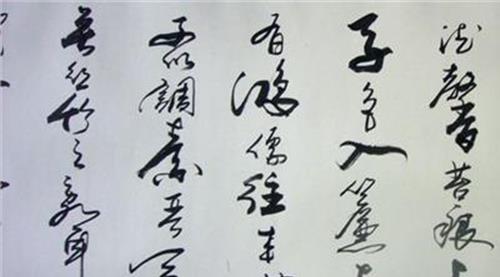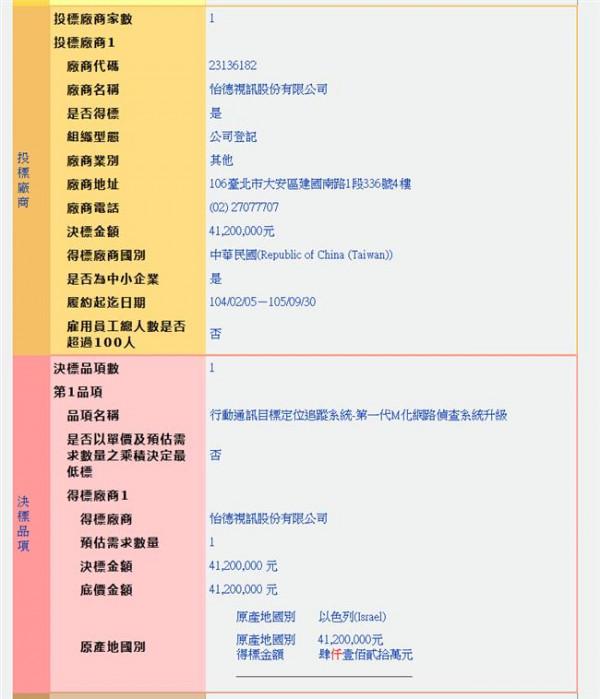王铭铭想象的 王铭铭:文化想象的力量——读E W 萨伊德著《东方学》
一般的学科是以希腊文的“logus”(学问、哲理)或英文的(o)logy(学)为后缀,而“东方学”(orientalism)却以“-ism”(主义)为后缀, 这难免给试图翻译这个名词的人带来一种困惑, 到底“orientalism”指“东方学”还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中世纪末期欧洲教会给为之研究和搜集非西方文化资料的学者所做的“学问”的称号,后来被知识分类法沿用,代指对中近东、东亚等地区的或甚至整个非西方世界的研究,所以它的确指“东方学”或“东方研究”[1](“orientalist”指“东方学者”或“东方研究者”),而不是“东方主义”。
对于东方学为什么要以“-ism”而不以“(o)logy”为后缀把“orientalism”改为“orientaology”这个问题,我们尚未有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解答。
不过,可以猜想,名词的发明者知道这种研究与别的学科不同,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任务。
1978 年,萨伊德(E.W.Said)发表《东方学》(Orientali-sm)[2]一书,对东方学的意识形态特点与结构作出深刻的评论。以往西方有关东方学的研究,多局限于把“东方”(theorient)视为研究对象,而萨伊德的《东方学》向东方学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它把东方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制度的存在加以阐述,给我们讲述了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和意识形态占重要位置的东方学的故事。
这个充满色彩和周折的故事告诉我们,东方学作为知识和言论的一个门类,其设计、发展和演化是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的兴起的内在力量之一。
在学术界,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界、区域研究界、宗教学界、比较文学界和政治学界,对《东方学》一书的评论成为许多论著的序论。
《东方学》一书之所以能成为社会人文科学界所注目的著作,原因在于它对“orientalism”的“-ism”的探讨,给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展示了知识与“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政治支配的密切关系。
萨伊德与《东方学》
《东方学》一书的作者萨伊德于1935 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他在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巴勒斯坦和埃及受基本教育,并在这门学科的“故乡”西方世界(美国马萨诸塞赫尔蒙德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受高等教育。1963 年之后,萨伊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青年教授。
之后,他又于1974 年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访问教授;于1974—1977 年间,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于1979 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科学教授。
目前,他身兼数职,在担任《阿拉伯研究季刊》主编之外,还担任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等职。萨氏的著述十分浩繁。主要包括:《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开端:目标与方法》、《巴勒斯坦问题》、《文学与社会》、《世界、文本与批判》及他的最具影响的力作《东方学》等。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兼国际政治评论家,萨伊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表述了他对文学和文化学及政治现实的联系的一种发现。这一发现,反映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与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厚修养。
从词义上看,所谓“东方学”即是对“东方”这个地域中的人民、文化与社会的研究。然而,对于什么是“东方”,却从未有过准确的定义。对于美国人来讲,“东方”可以指的是远东(亦即中国和日本)或“近东”。可是,历史上,对于法国人与英国人来讲,“东方”主要指近东或阿拉伯世界,或与欧洲接界的“非欧世界”(non-European world)。
而对于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以及瑞士人而言,“东方”指的又是另外一些地区。
即使有些人对“东方”的地域定义有统一的共识,他们对“东方”土地上的资源与文化也存在不同的观念。对西方小说家来说,“东方”这个词的使用往往可以与“东方少女”相类同。对文化学者来说,“东方”意味着与“西方”的宗教、哲学、民俗完全不同的文化实体。
而对于西方商人来讲,“东方”则意味着资源与市场。对“东方”的定义的歧异发展到十分深入的程度,以致于“东方”可以被视为“迷结”(syndrome)。
萨伊德从“东方”定义的相对性出发,探讨“东方学”研究本身的主观性。在萨伊德看来,“东方学”不仅指学术研究上的领域,它的存在受各种势力的限制:
“东方学作为一种表象(representation),在历史上不断地建构和更新自身,而且有对‘东方’这个广大的地区越来越发敏感的倾向。东方学专家所做的工作,是用他们对东方的印象、知识、和观察来表现西方社会的特色。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东方学者给他们自己的社会所提供的东方的形象有如下的几个特点:(a)这一形象有他们自己的引记,(b)它阐明了作者对东方可能和应该是什么的想法,(c)它与别人的东方形象形成反差,(d)它为东方学界提供了当时所需要的东西,(e)它是对一定时代的文化、职业、民族、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应对。”[3]
换言之,东方学者首先是一个“东方学者”(orientalist),然后才是一个人。东方学者进行东方社会文化的讨论,其所在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场合对他们的思维、辩证、引据各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东方学者不可能作为纯粹的个人,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对“东方”进行评论,他只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理人来“认识东方”,其思维及艺术创作成果,是东西方关系中西方的形象与东方的形象的对照。
因此,除了学术上的意义(包括对东方的研究、东方学的教学与写作)之外,“东方学”还具如下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东方学除了是一种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东方学对“东方”与“西方”的主观划分,渗透于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及殖民地行政人员的创作之中,远远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意识形态;其二,由于西方人所“拥有的”东方学具有此特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西方人的东方学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制度。
用萨氏自己的话说,“东方学是启蒙时代之后欧洲文化据以在政治学、社会学、军事、意识形态、科学和想像各方面塑造甚至制造东方的一个极为系统化的学科。”[4]
《东方学》一书之写作目的,不在于学科范畴的创设,而在于采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揭示隐藏在学科背后的意识形态。萨伊德采用了近二、三十年来在欧美具有最深刻影响的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及其主要概念“discourse”(即具社会力量的言论),[5]分析限制着东方学研究的领域、内容、理论和目的之言论制度(discursiveinstitution)。
《东方学》这本书的结构,与福科的谱系学(ge-nealogy)架构很类似,它以十四世纪为出发点叙述了东方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萨氏所采用的叙述架构是绵延的历史,并没有明确的历史分期,换言之,不过他强调东方学的发展有一个分界限,即十八世纪。
在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东方学内容比较松散,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势力的扩张,这门学科得到系统化的发展。通过东方学的历史考察,萨伊德阐述了十四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东方学如何描述、解释以致从理论上控制“东方”的作用作为一种思考、想像的工具,以及西方人如何通过创造和占有东方学来进行文化地理的意识形态想像。
《东方学》分为三大章十二小节。第一章称为“东方学的范畴”,从历史和文化哲学的角度探讨东方学的视野以及知识圈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章称为“东方的构造与再构造”,分期描述近世东方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及主要的西方文学家和学者描述和研究东方的手段。第三章从1870年出发,探讨殖民扩张以来东方学的发展,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法东方学的状况,及战后美国在东方学领域中的角色。
萨氏所分析的东方学史,是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worldsystem)形成的内在部分。在《现代世界体系》(1973)一书中,瓦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已经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如何在十四世纪之后形成以及在十六世纪以后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地理空间的内核(core),如何使非西方社会变成“边际”(periphery)。
瓦氏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散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于与世界市场形成同步发生并难以分割的西方霸权产生的东渐,瓦氏并没有加以分析。
实际上,十四世纪以后的世界史不只是一部经济政治的变迁史,还是一部文化变迁史。用沃尔夫(Eric Wolf)的话说,它是西方文化史排挤东方历史的过程,是欧洲变非西方社会为“无历史”的民族的过程。
[6]《东方学》的描述与分析,反映的正是瓦氏忽视的一种历史取代另一种历史并使后者成为“无历史”的历史。不过,它的意义远远超过补充《现代世界体系》的解说,而更重要的是为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指出社会、历史、与文本(textuality)的密切关系以及学术、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为一般的读者指出文化自我和他人的观念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为第三世界指出西方文化的潜在力量以及东方世界如何透视这一力量。
东方学的范畴和历史
对大片地理和文化空间(“东方”)的系统化研究和论述,起源于西方文化向东方的挺进。萨伊德说,“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学科和方法,是研究、发现、和实践的论题,也是西方人对其边界之外的一切事物的梦幻、想象、和议论。
”[7]作为一种“想象的地理学”(imaginative geogra-phy),东方学的发展与近代世界文化格局的变迁有关。在西方文化逐步“东渐”之前,东西方的接触早已存在。虽然古代东方文明(埃及、中东、印度、中国)的影响已在不同时期在世界上分别占有支配地位,并以不同的方式波及欧洲,但是并没有出现“西方学”(occidentalism)。
东方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形成的理论支柱之一。
东方学这个学科正式产生于公元1312 年。当年,维也纳教会通过一个提案,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地建立有关中东和近东语言和文化研究的科系。从此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被西方社会承认的“东方学专家”。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之间,东方学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西方宗教的源头(近东和埃及)及其对立体系(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资料。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东方学与教会的关系仍然附属于教会的知识结构。在几百年里,“东方学者”一直是指圣经学者(Biblical scholars)、闪米特语系专家、伊斯兰学者、以及稍后成长起来的研究汉语的汉学家(sinologists),研究东方的目的是为了扩张西方教会的势力。
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叶,东方学的范畴逐步扩大到整个亚洲,它走出了教会,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界。
十九世纪的东方学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学家、印欧学家),另一类是有天才的业余热心人士(如文学家雨果和哥德都曾写过有关东方的书),更多的东方学者是学者和热心于东方文化的名人。
随着东方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东方的百科全书,其中以斯瓦伯(Raymond Schwab)和莫赫(Jules Mohl)主编的大部头百科全书和目录为最有名。
据萨伊德的分析,十九世纪东方学的系统化发展,其基础在于十八世纪若干观念因素的产生。第一,十八世纪,随着欧洲对世界的“开发”范围的扩大,“东方”这个地域概念从原来的伊斯兰世界和近东,转化成相当开放的地理概念体系(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等等),使“东方”超脱了古代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范畴;第二,大量的东方学研究提供了有关东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资料和印象,使西方的历史学者有可能把东方历史当成西方历史的参照系。
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历史比较研究,对东、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加以探讨;第三,许多东方学者开始转变他们的态度:原来东方学者认为东方是一片松散的土地或一盘散沙,到十八世纪出现了把东方社会看成与西方社会类似的社会—文化有机体,强调它们的内在一致性和合理性;第四,十八世纪产生了极为流行的分类学,如物种分类学、人种学等。
分类学以物种和物体分类为基础,但是扩大到人和文化地理的分类,为东、西方的“辨别”(identification)提供了方法论武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