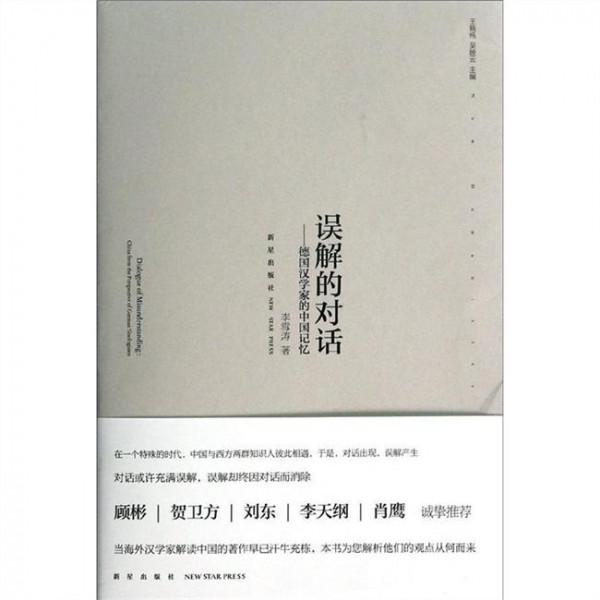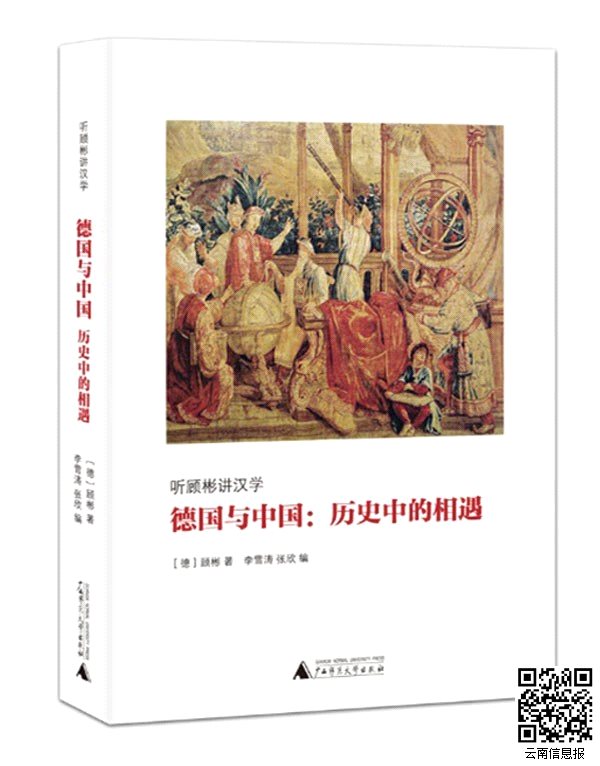李雪涛北外 李雪涛等:当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肖鹰: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客串主持。我们下午的时间宝贵,所以就先请我们这本书,《误解的对话》的作者李雪涛教授发言。
李雪涛:感谢大家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这本《误解的对话》是我近两三年的一些论文,集结在一起,是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对汉学做一个定位。今年我还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叫做《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的文献与研究》。
我一直想,从纵向上,从历史上,对于汉学的贡献做出一个梳理,这意味着我们要揭去我们的文化传统,从现在开始,另起炉灶,做一些海外汉学的研究。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看看民国时期,我们已经翻译了哪些东西,已经做了哪些贡献,哪些研究。我觉得如果不揭去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开始自己的研究的话,我们会有好多漏洞,这是第一点。
从横向来看,我觉得要把汉学放在哲学,或者是方法论的框架下进行探讨,这就引发出关于阐释学的一些想法。这也给当今的汉学做了一些定位,也就是汉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是什么。一直有人想要告诉海外的汉学家们,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真实的中国是什么。
顾彬教授自己也经常说,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话,我们汉学家就做不了研究了,汉学研究没有趣味,正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存在,我们的汉学研究才是有必要,有实际意义的。
收录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一直关注的,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的时候,是如何应对,如何反应的。这一点是受荷兰的汉学家,徐一河的启发,他说,如果我想去了解中国,那么我不会读四书五经,不是去看中国人如何生活,如何交往,而是看中国人在面对外来的冲击式,是如何反应的。
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想要了解一个邻居,就要去看他跟人打架的时候,是怎么表现的。在吵架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特点,有意识无意识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所以中国文明在面对佛教、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进入时是如何反应的,这就是《弘明集》,当然如果我们去读《弘明集》的话,就会知道中国传统的卫道士们,如何接纳佛教,如何拒斥佛教,比如范缜的神灭论,也是《弘明集》里面的一篇文章,这是第一次,所以徐一河写了佛教出征中国这一本书,描述了佛教为主的印度文明,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这么一个大题目。
接下来,是158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我们看到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基督教文明进行的批判,我认为这个进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但徐一河认为已经结束了,所以他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是怎么研究马克思注意的。我一直觉得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的过程中,更能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色。汉学家们研究汉学,是想弄清楚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儿,特别是通过这样的碰撞才能看清中国的特质。
我的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基本就是这些阶段,佛教的内容在其他文章里可以提及。书里面涉及的,主要是明末,还有晚晴到民初这两段。我认为这两段时间对于中国文化来讲,是面临着非常重要的转折。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把我的论文介绍给大家,我是为了把一些并不深刻的思考介绍给大家,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争论探讨,这是一种期望。这里没有完善的东西,给大家做范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方面,给大家多一些思考。
自近代以来,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学术问题,如果不放在汉学史的框架下来研究,我认为是看不清楚的,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汉学史的重要性。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能看到1898年的《马氏文通》的话,我们会说这是我们第一本的中文文法书,但如果把他放在西方文发脉络下,就会发现,在1583年后,有几十本的不同外语的语法书。
整个文法系统是有一个谱系,放在整个西方语言中,才能解释通。为什么要做西方汉学史?因为是为了做中国的汉学史。
因为近代中国的汉学研究,有很多断裂,必须要借助之外的力量,才能将其完善。总而言之,我觉得韩雪研究到今天,确实是方兴未艾,在很多领域还未完全展开。进入了之后,确实是一片广阔天地。同时因为涉及到中国、西方的学术,复杂性要比单纯的中文、历史复杂的多,因为你要同时关注几条线,除了中国的文学、历史,你还要关注西方的文学历史,所以这两条线,如何比较好的搞清楚,对于我们来说,不容易。
这本书是我在求学中的思考,出本后,还望大家继续思考。谢谢大家!
肖鹰:谢谢雪涛教授。雪涛教授刚才谈了一个观点,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要在碰撞中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这是我认为的很重要的一点。下面我们请顾彬教授发言,和我们碰撞一下。
顾彬:朋友们,你们好,97年我在中国听过一个我很重视的文学评论家,在一个会议上对一个荷兰人做的报告。他开头这样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谈的不错。他的意思,是还不够。从那时到现在,我总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认为97年的那个会议上,那位荷兰人做的报告是最好的,没有必要特别提出这样的说法。
我想那位评论家,是不是无意识的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政治。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是一个专家的时代。
不再是由我是一个德国人,就决定了我会了解德国的历史的时代。如果一个中国人,比我更了解德国的历史,我会毫不奇怪,毕竟他是专家,而我不是。所以,“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个说法,好像有误会的背景。
误解有坏处,也有好处,因为它允许我思考一些问题,毕竟人生里不只需要理解,也需要误解。很多八十多岁的德国哲学家倡导的是以相信为核心的哲学。毕竟有很多德国的学者也对中国抱着不同的成见,他们的常识,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合作。德国很倡导对话哲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如果不能与别人对话的话,那就不能被称之为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可以说,如果一个中国人不能从德国人那里了解中国人,那么你很难说他是一个中国人,反之,也同样。
李雪涛的书好在哪里?我认为最好的就是把国学和汉学联系起来。国学和汉学之间如果不拥有彼此,那么绝对是有问题的。国学为我们汉学家提供了研究基础。比如说孟子,孟子在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重要到中国学者感到惊讶。我认为中国哲学家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孟子。
到伽达玛尔以前,我们一直认为理解比较重要。但现在,我要说,理解很复杂,所以必须要允许误解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中德的学者之间要互相合作。我的几本著作,都得到了在座的几位的帮助与支持。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来问我们德国人问题。德国人认为,只有去请教,才有面子,就说这么多吧。
肖鹰:谢谢顾彬教授,刚才顾彬教授谈了一个问题,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人吗?我认为顾彬教授对于我们的文化,有很大意义。在这本书里,李雪涛教授也提到,海外汉学家的存在,是我们汉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要素。没有海外汉学家的存在,我们的汉学研究,就是有问题的。就好比生物多样性的机制一样。下面,我们就请贺卫方教授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贺卫方:我其实没有多少资格坐在这里。但因为之前做过一点法学界的小工作,对于近一百年,美国人对中国法制建设的研究做了一点小研究,跟这些汉学家们也是相关的。因为近一百年的中国法学史的研究,也是建立在西方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包括整个体系、概念,我们以前是不会把中国古典法律分为刑罚民法民事诉讼法,这些分类,还有对于法律的社会性的思考,这些对于法律这方面来说,都十分重要。
我想,李雪涛教授这本书的出版,把之前的文章汇集成册,一册在手,雪涛教授这几年的思考、研究,还有中国汉学的脉络和体系,都能够简单的理解。书明也很有趣,叫做误解的对话,这是一个引起误解的对话,还是很多误解之间的对话?在这本书后面,我写了一段“勾魂语”,我引用了凡尔赛宫的镜子做比,说我们看到好多不同的镜子,映出很多不同的自己,可是到底哪面镜子镜子里出现的才是真实的自己?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面镜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书名是后面的那个含义,即各种误解之间的对话。
这既是每一代学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不同国家汉学家之间的对话。这本书让我们知道,各种误解之间的对话也很丰富。正如顾彬老师所言,不接触外国人的话,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这让我想起歌德的一句话,不懂别人的语言,也不懂得自己。可是我常常困惑,这个别人是谁?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遇到一个研究突厥学的学者,我们不会说他是汉学者,但他的研究的确涉及汉学,也涉及到中亚的历史学。
我有的时候喜欢拿我们山东人跟河南人,跟江苏人比较比较,为什么我们山东人就没有出过一个皇帝?有人说我们有孔孟,但是那是皇帝的老师,也不是皇帝。山东几千年来没有皇帝,我倒觉得很有趣。从这里出发,未必是为了研究汉学,但至少可以去思考,我是谁这个命题。比较的范围有时宽广,有事狭小。我们经常在别人的观察中,看到那些令我们震惊的,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的特点。
刚才顾彬老师提到,孟子在德国似乎十分重视。我记得传教士,同时也是汉学家的威廉马丁曾经写过《中国先秦国际法研究》这本书。而《孟子》里面也提到了先秦时期类似国际法的相关内容,譬如说孟子倡导国际干预,也倡导人民推翻不好的君主,如果自己推翻不了,就邀请其他国家来征服自己的国家,也是可以的。
孟子有倡导人权高于主权这个倾向。但是我们的法学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些。这是很遗憾的。比如说《孟子》提到的皋陶放古叟这个故事。
最后提出了舜为了向父亲尽孝,而放弃自己的天下这个理论,如果按照西方法治的观念,这是很奇怪的,这是儒家思想中的缺陷吧。我最近也经常受到汉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带给我自己的启发。我觉得我们对中国古典历史的理解,包括现实问题的解读,都受益于汉学研究。这是我们经常受到冲击,也获得思考力量的来源,是我们为新星出版社和雪涛教授感到高兴的原因。谢谢大家听我这段充满误解的发言。
肖鹰:谢谢贺卫方教授,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他可是非常推崇法治,而非“逍遥法外”的,下面我们请杨慧林教授,为大家讲几句。
杨慧林:我先要做一下回应,刚才贺卫方教授提到了古叟杀人这个故事,我相信这确实与汉学有关。因为当年有一位汉学家,李亚阁,在翻译四书五经的时候,在这里遇到了麻烦,因为作为一个西方人,实在无法在道德上理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但一个汉学家有趣的地方是,到了他的后期,他更多的为这种行为做了解释。虽然很多中国学者对此不屑一顾,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也是很有趣的话题。今天有法学家在场,我也想起了一个跟伏尔泰有关的故事。
伏尔泰曾经就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这个话题为中国人进行过辩护。他引用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候,里立的一块碑,上面用中文和俄文分别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两国从此再不交兵,哪方破约,便要受那位一切的主宰者的惩罚。
”他认为这段话里面的主宰者,就是上帝。但是,这段话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尼布楚条约里,因为尼布楚条约并没有使用汉语。伏尔泰的这段引用,大概是来自于两位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的日记里。这些材料,对我们去了解历史很有帮助。
回到今天两位主人的话题上,我们的的确确总是去纠结过去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诠释学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是原本的问题。我自己的宗教学研究,最有感触的是圣经,因为圣经最大的特点,就是可翻译性。我觉得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诠释学从这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觉得雪涛教授更清楚,国学这个概念会更有防御的感觉,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更有意思。
为什么汉学可以像这个会议的主题词所说的,可以火起来?因为更多的西方人在做汉学,但是我们中国人做西方学术的研究,能不能像是汉学在中国的这种程度?我想这是值得在座的各位深究的,我先说这么多。
肖鹰:谢谢杨慧林老师,其实我读雪涛教授这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进入一个没生命的文本,去关注它后面的故事。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发现理论背后的故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生命之树总是长青。下面我们邀请王锦民教授为大家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