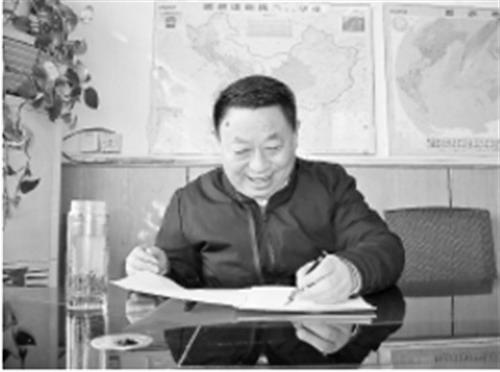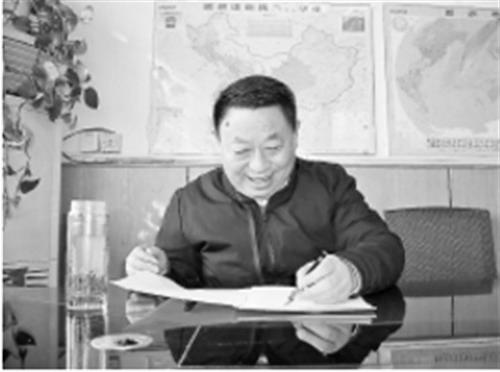毛森回上海 毛森将军回忆录之一
戴所帶來一班人都是指導員,把我們分成若干小組,經常舉行政治討論會。戴甚忙碌,很少來校;也講過幾堂課,沒有書本講義,口述社會各階層情形,百藝行業活動形態。對於當前派系組織、人事離合及時勢演變趨勢,都如數家珍;各地城市環境、風俗習慣,都瞭如指掌。
他不止行萬里路,全國各城市社會,似乎都曾親歷。趙龍文講解秘密結社、幫會組織;我們學警察時,雖已注意幫會對治安的影響,但只知一點皮毛,趙先生竟能溯追淵源、演變、組織、分佈、人事、情勢及當前在社會上的力量。
並要我們實習,解釋口語、暗號、擺設杯壼陣形、手勢、動作等。趙某是學者,並非幫會中人,他的雜學博聞,大家對他頗有好感。又請了北京教授朱渭清夫婦,來教我們方言及相命學;我們同學都是東南人,在校時雖也學過國語,但平時交談,都說東南方言,對國語很生疏,粵、閩方言,聽、談都困難。
朱夫婦一口北京話,清脆悅耳。朱妻本係廣東人,能說標準粵語。
那時北京社交,看相拆字很流行,朱教授亦善此道;他推算我的相命,將成「烈士」,恐難過六十歲。如能過六十三,則要照第二甲子算起。勸我廣積陰德,助人行善。又請來魔術師阮振南,他是越南革命分子,因程度很差,黃埔軍校勉強收錄他。
他的魔術變得很好,談吐滑稽突梯,一言一動,令人捧腹。在軍中風頭甚健。他要我們勤練玩紙牌等基本手法,我很慚愧,沒有學成一技。以後聽說他回越南革命,在胡志明部下卓著功績。較可笑的是軍訓教官馬策,沒有考察我們的程度,把我們當做初期入伍新生,從立正、稍息基本教起,那知我們早已熟透典範令,讀過統帥學;他教得力竭聲嘶,我們被整得啼笑皆非;因為軍訓,只有服從,不能抗辯。
後被戴知道了,才停止軍訓。
尚有化裝術、催眠術……等各種功課。古代青天刑吏,也有採用,現在各國警探間諜,更廣泛應用科學儀器「測謊機」、「錄音機」、各種電子、電腦等;但在正統警官立場眼裡,對有些伎倆,仍視視為旁門左道。
如催眠術,校中舉行慶祝會時(似為二十年國慶),徵得三期同學章微寒之同意,作為催眠對象;他年最小,也最活發,尚未完全成長,在禮堂檯上被催眠過去,扮演大總統就職,其架式動作,活潒一位尊貴的總統,並發表演說。當時我見催眠師十分緊張,事後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催眠後還醒動作,如有遺漏一點,沒有做到或做錯,將長期影響其心神智慧及身體健康。」章以後即不再長大,心智似亦不及當年靈俐,一眼即覺其發育久健全;恐其催眠時對身體某部沒有完全還原,至今我的腦海裡,仍留疑團。又請了大畫家梁鼎銘,教我們速繪法,對人物抓住其特徵,用簡單幾筆,描繪出其圖形,有的真能畫得維妙維肖。另請專家教速記。能把對方說詞。用符號記下,此技非短期所能學成,現在發明錄音機,速記更無用了。後有一部分同學被挑出,學習無線電收發技術,從此即為無線電專業人才。
二期畢業之後,二十一年秋續招正科第三期,但名額減半。校長施承志被戴擠走,由趙龍文接任校長。除法律、警察等部專業教官留用外,其他教職人員,大部被調換。三期畢業後,尚續辦第四期,同時舉辦「乙種特警訓練班」、「丙種特警訓練班」,招收各色男女青年,培訓中、下級幹部。
二十一年冬,我們甲訓班結束,送去南京明瓦廊大豐富路洪公祠續訓。訓練班門外掛著「外國語研究所」招牌,裡面也有和我們相同的訓練班,約有三十餘人,多係黃埔軍校四、五、六期的軍官,也剛在別處訓練結束,來此續訓;如陳恭澍即其中佼佼者之一。這是戴的工作有組織、有訓練、最初奠定規模的基幹。這近百幹部,以後都成各單位最早領導人,後來官階幾都升至將官。我們兩班合併,一面短期續訓,一面考核各人能力、社會關係、適宜分派何地、何種工作,並在兩班中各挑選六人,共十二人,成立最高幹部班,杭校特警班中六人,即石人寵、張人佑、鄭海良、王滌平、羅道隆及我;軍校特警班六人即黎鐵漢、李鐵軍、郭文彥、胡宿嘉、趙理君、卓飛。現在僅我與石、張三人仍在世上,其餘九人都已去世。大都死於抗戰時期,為國犧牲。不久,兩校同學陸續派出工作,彼此不知派往何地?擔任何職?以後偶然相遇時,傳告一點。
我們十二人繼續受訓,主要教官多係德國軍事顧問團的人兼充。其中駱美蒼係將級,態度嚴肅,要求較苛。有一年輕校級教官,常駕車帶我們去山野上課,非常活躍;他能在一天時間,把全南京站崗警察偷拍下來。他的秘密相機如帶狀,略彎,掛在胸前衣內,鏡頭如紐扣,露出衣外,快門用一線通至褲袋,用時只要鏡頭對準目標,用手一捺,即拍下目標,同時自動移上次張,不需拿出對光、距離等;拍完一條軟片,再拿出沖洗。
尚有偷測軍事目標、航空速繪等等新奇技術;愈學愈覺可怕,自覺「弱國無國防」。
中國教官如余樂醒、葉道信等,都是留俄共黨特工能手。余樂醒教爆破,有一天自製手榴彈,我用杯子裝炸藥,倒入酒精,調勻如糊狀,再塗於拉線之一端,裝進手榴彈內,再將拉線裝藏木柄內,將柄端蓋緊,即成自製手榴彈;用時去了蓋,用力拉引線,等於火柴擦著粗面,即發火爆炸。
因酒精揮發很快,我塗了幾條拉線,即乾了;一時大意,隨手拿了銼柄刮一下,立即爆炸(即如撞針撞擊子彈屁股的雷汞),杯子落地粉碎,火藥上衝,我的頭髮、眉毛都被燒焦,左手掌現尚留一點疤痕,全教至彌漫硝煙。
余教官焦急惶恐,各同學也關懷圍慰。我的臉部、手部被火藥燒得面全非,樣子很可怕;但自知沒有傷及要害,碎片沒有射入體內,去了醫務所包紮之後,即算無事。四、 傷寒重病幾乎喪生
這一爆炸,我並不把它當做大事,可是幾天之後突發高燒,燒得我昏昏沉沉,有時昏迷不省人事。病情怎樣?什麼時候被送入中央醫院?我不知道,只略記得送入醫院。
有一天,清醒過來,見我父親在我房裡,戴的秘書毛應熊,陪在他身邊。我很奇怪,問父親怎麼來的?他說:「這裡打電報邀我來的,已來到幾天了……」因我病重,醫護人員不許我們多講話,並有特別看護專在我身邊日夜照顧。
我記得內科主任戚大夫,常親來診病,外科主任沈大夫,不時也來。病漸好轉,父親每天來看我,停留相當時間,略有交談。等我稍有康復,毛應熊才對我說:「你患的是嚴重傷寒病,一來即很兇,因高燒不退,昏迷一個多星期,最嚴重的時候,氣如游絲,只靠冰袋把你保住,人也認不得了,以為已無希望,故一面打電報給你父親,一面準備後事。
」他說了後,我才想起:似在朦朧夢中,曾見老師同學來看我,並有人問我「我是誰,你認識嗎?」其中似有父親。
後問父親,父說,他確曾來過,見我昏睡,醫護人員不許他說話。可能父子連心,昏夢中相見。過了兩個星期,才脫離危險。但此病實在太厲害,高燒過度,腸炎傷害,恢復較慢;住院六十五天,才准回校。
在此期間,各同學已陸續分發工作,離校之前,多來看我,教官也有來。醫藥費似花二千多元,由戴給付。這是一筆巨款,當時不論機關學校,很少代人付醫藥費,多由自己負擔。我未參加工作,他即代我付了二筆醫藥費,我對戴深深銘感。
那時校中同學、老師都已離開,只剩下幾個電台人員及雜兵伙伕,對我病後調養,毫無照顧。我除每天和大家同樣三餐外,連牛奶也未喝過一口,補品藥物更談不上了。病後需要補充營養,總覺肚餓,常在附近買些油條、小餅充飢。不久,頭髮、眉毛脫落;又,可能飲食不調和,火氣上升,兩眼通紅,幾乎看不見東西。在附近找得一家印度人開的眼科小診所,醫療幾次好了,費用自己支付。健康恢復很快,已能慢跑操練。
我父在京期間,即住離校很近的小旅館。我為送他回家,陪他搭乘京杭直達公共汽車,到了杭州,送他上火車回家。父親堅邀同回,他說:「媽媽每天倚門而望,全家及各親屬都切望見你。」我為了逃避婚姻,已幾年沒有回家,對大家確甚想念;但為避婚及候派工作,仍未與父同行,依依分手。我回京後仍續調養。旋屆二十二年國慶,舉行全國運動會,三期同學派來南京實習,內有葉霞翟(後為胡宗南夫人),上級要我帶他們實習,每天我帶他們實習參觀。忽因福建醞釀獨立,我奉派入閩工作。
第 筆
"毛森".art_autc 第 6 筆
回憶錄 第448號:(1999年09月)
列印
往事追憶──毛森回憶錄(二) 作者:毛森 附圖
五、時代犧牲的婚姻
我的大姨母周梅英,長期吃素信佛,家住英岸。同村鄭芝寬夫人,亦吃長素信佛。我母稟承外祖母信仰,也吃齋禮佛,自然成為佛門之友。鄭之幼女鄭彩耀,常依我母膝前,逗人喜愛。姨母開玩笑說:「不如給你做媳婦吧!
」初只說說笑笑,以後我母與鄭母漸漸有意,大姨自願促成。當時大哥已結婚,二哥也已訂婚,幼弟則與外祖母襁褓族孫女定婚,自然只能選中我了。我年尚小,不知世事,彩耀更小,只一天真幼女,我們自不知道。
以後她們逐漸認真,談起結親。慢慢我亦略有所聞,但因年小,羞於開口詢問。偶爾聽母說起她的纏足苦情:腳掌、腳趾已捲緊,……能忍痛……扶牆倚壁行動,痛苦不過,她常私自解放……其母把它包緊,用線密縫……。
我才明白她正被纏成三寸金蓮,又不給她上學。我已稍懂事,乃表示不要小腳、不識字的妻子。當初大家並不重視我的態度,後見我意態甚堅決,才漸猶豫起來。我則自接觸新文化之後,如脫離黑暗迷途,豁然開朗;對胡適革新思想,特別崇拜,自然也信仰杜威學說,如我從事教育事業,將效法杜威自由教學主義。
原由孔門出來的我,也贊同打倒孔家店,堅拒不要纏足、文盲的女人。她們見我如此反抗,才莫可奈何送彩耀去清湖小學上學。
她沒有正式上過學,只在家中其兄念私墊時學得幾字。可能因入學太晚,所有同學都比她小,她已長大,羞與為伍,只讀一年左右即輟學;所以只能寫幾句粗淺的東西,寫不成通順的信。她的腳也得到解放,但為時已晚,筋骨彎折,已成定形,無法伸展,由此對其母發生反感。
其母尚以棄置若干精美新鞋而可惜。我則一直反對與這樣的女人結為終身伴侶。女父鄭芝寬先生為煤商,經常由江山運煤去杭、滬出售,在鄉間可算殷戶;因我拒婚,常怪責其妻選錯東床,女母則向大姨訴苦。我父素性和善,不表明確主張,我母堅決要我娶她,否則她沒有臉做人了。我則堅決解除婚約,爭吵甚烈,以致聲淚俱下。我負氣離家,為了避婚,好幾年沒有回家。
我奉派去杭州見胡國振,胡對我說,福建陳銘樞等要造反獨立,他臨時奉令成立浙、閩、贛邊區情報站,站部設在上饒。要我星夜由江山入浦城,監視閩北各部隊動態及十九路軍部署。發給我密碼、發電紙等,沒有配帶電台,用軍事委員會軍事雜誌社(社長潘佑強,黃埔一期生)通訊員身分,對外活動,支領少校薪。
路經江山時,因多年沒有回家,很想念家人。母親個性堅毅,對每一子女,都深切愛護,對我期望尤深,只是新舊觀念不同,如過門不入,心實不安。我乃走進家門,全家自大歡喜。她們促我立即成婚,我說:「任務重要,在家只能停留一天,不能辦婚事。」大家不肯放我。母親甚至聲言,如不答應,要向我下跪。她是生我的母親,不答應也得屈從;我無法逆天忤倫。我十一月十八日抵家,二十日即把彩轎抬來,次晨(二十一日),我即離家入閩。
第二章 初派福建六、閩北初露鋒芒
二哥常去閩北經商,他陪我同行。我以商人身分,翻山越嶺,到了浦城邊境九牧地方,寄宿一家小飯鋪。天尚未亮,聽到幾聲槍聲,旋有十多名便衣隊來店盤查;見我是小商人,問了幾句,並無留難。據說:他們是紅軍游擊隊,經常來查行商旅客。大家對政府軍都叫「白軍」。這是我初次接觸到共產黨游擊隊。那時閩、浙邊境,只有地方團隊及紅軍游擊隊。紅軍移動,多在夜間,政府監視哨,常隱伏必經路徑;如係十字路口,則將手榴彈保險打開,接長拉線,綁在樹枝或草幹上,每面都是如此。崗哨則隱匿草叢中,不論那面來人,都將碰動拉線爆炸。大動物經過也將碰炸,早晨則一一收線、收彈離去。只需少數人力,即能在廣大山區佈崗警戒,故夜間行人絕跡。紅軍對這類暗探活動,十分注意,如被發覺,都慘刑處死。在那裡,我也初次看到蘇維埃政府的寄信郵票,中共在邊區設有郵政傳遞網。
到了仙陽鎮,才見獨立四十五旅駐軍。二十四日到浦城,我以新聞記者李谷生身分,拜訪旅長張鑾基。詎我在飛渡關山的幾天裡,斷了消息,十九路軍已於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獨立。張說,他剛接到通電。
即將原電給我看,大意謂: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郊場搭台,召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改年號「中華共和國」元年,以半藍半紅顏色。中嵌五角黃星的旗為國旗;以陳銘樞任人代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為人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光鼐為經濟委員會主席,蔡廷鍇為人民革命軍總司令。
張旅長表示十分憤慨,並聲稱絕對擁護中央;又介紹他的副官張□佑和我詳談。張副官乃四十五旅代表,與駐閩北建甌約五十六師劉和鼎、駐尤溪新編第□師(後改為五十二師)盧興邦、駐邵武的獨立第四旅周志群等部,被邀去福州參加獨立代表之一,剛剛回浦城。
張副官說,他們表面上只好表示贊同獨立。陳、李等亦看出其委蛇態度,只在情勢上不得不盡力拉攏。
參加會議之後,他們乘輪船繞道上海經浙回閩。在上海曾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效忠中央。如果十九路軍強力壓迫,則向浙、贛邊境稍退,採取一致行動,靜觀中央處置。我立將當前情勢,用電報拍告上級,並積極採訪各方情況。
那時全國震動,南京亦甚驚惶。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只有一點保安部隊,蔣委員長正在南昌部署五次圍剿,江、浙都無國軍勁旅;如果曠日持久,十九路軍發動攻勢,其他地方有力響應,閩北駐軍可能改變態度。他們都非中央嫡系部隊,被迫調駐福建。盧興邦更是割據民軍,誰能保住其地盤即投誰。蔣委員長為積極平亂,一面調兵遣將,準備討伐,一面空投巨款,對各駐軍極力撫慰,並催促修築機場、公路。張鑾基動員所有鄉民,親自督工。
有一天,我在飛機場遇到張旅長,他似開玩笑又似懷疑的對我說:「十萬大軍即將來浦,委員長要我準備糧秣、駐營:日夜加工,有恐辱命。」並提及一些番號,他向我探詢這些部隊現駐地。我說:「這就是三軍未動,糧草先動。委員長的指令,絕不會有錯。你是勁旅主官,各軍駐地,你比我更清楚。」當時戰事頻繁,各部隊駐地,非嫡系軍官,確不清楚。我初離南京,素極關心軍情動態,故能瞭如指掌;心想部隊調動素保秘密,何以預告張旅長?大概這就是中國式統帥術,安定軍心的手段吧!但知有幾個部隊,遠在華北邊區,如何能救近火?不免有些懷疑。
過了一個多月,尚未見中央軍入閩。福州人民政府氣勢很囂張,以為國軍被紅軍纏住,不敢對其用兵。南京袞袞諸公爭議莫措,據內部傳說,蔣對他們保證,在一個月之內,敉平閩變,回京開□中全會。福州方面則忙於開會分官,過分輕視中央,沒有積極備戰。據我探查,閩北重鎮的延平,僅駐司徒一旅;最前線的南雅口,只有一個連對北警戒;延平以南古田、水口,兵力亦甚薄弱,該軍四個主力師,分駐福州及閩南各要點,沒有大會戰的本錢,不能與一二八戰役同日而語。蓋淞滬乃一隅之地,當時有中央精銳八十七師、八十八師等為其撐頂,輿論為其宣揚助威,抗日戰役之能獲得輝煌戰果,並不全是十九路軍一己之力;而其不察,反以是居功驕矜,妄圖獨立,自取滅亡!我常感覺誇大宣傳,固有助長聲威,但過大誇張,常易僨事。盛譽之下,反易迫人陷於絕境,使團體毀滅;十九路軍即可作為殷鑑。
據我記憶所及:討伐閩變,乃蔣委員長一生最得意的用兵之一,真可說師出如神!他把十九路軍估計得很高,抽調十五個師以上的兵力,大部係準備五次圍剿的勁旅,列陣於武夷之陽。因浦城的機場尚未完成,他驅車入浦城,又因街道狹窄,不能通行,與夫人輕裘緩帶,乘輿進城;談笑用兵,以雷霆萬鈞之勢,揮兵南下。三十六師迅即攻佔延平。司徒旅投降;張治中統八十七、八十八等師經建甌,攻略古田、水口,直薄福州;其他部隊或沿閩江而下,或直指閩南各據點,如狂風捲落葉;不過幾星期,叛軍即被全部解決。人民政府要角,幸而逃得快,浮海去香港,否則盡為俘囚矣!
戴先生亦隨蔣委員長來浦,曾至我的住處巡視,詳詢一般情形。對我生活簡樸,工作切實深入,表現優異,大為嘉許。可能對我建立良好印象。蔣平閩變之後,將大軍調回閩、贛邊境,派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衛立煌為前敵總指揮,即駐延平,與南路陳濟棠合圍,部署五次圍勦。
大軍南下時,我亦隨軍去福州。至水口過新搭浮橋,黑夜踏上活動的木頭上,掉下閩江,茫茫不辨方向。幸小時學得一點土法游泳,掙扎游至岸邊,沒有滅頂。所以我對游泳,從前認為係救生技能,現在才視為健身運動;每人都應學會泳術。
上級以我報導軍情,安撫軍心,探訪民隱,頗有貢獻;令我組織閩北站,站部即設延平。並派報務員楊震裔等二人,來延平設台,與上級直接通報。我跑遍閩北十七縣,羅致幹練青年張新民、李鳴華、喻炎、徐謙、吳輝映、鄧□等十餘人,佈置情報網。
那時共軍主力已退縮贛南,在閩已無多大活動。當局全力開闢公路網,建築沿閩江碉堡線,防共軍向東突圍。我站主要工作是監視民軍活動、部隊軍風紀。因連年征戰,軍紀廢弛,加以福建係極落後地區,貪官污吏,魚肉人民。
除我們盡力檢舉外,南昌行營並令康澤組織別動總隊,在贛、閩戰區巡察,賦予先斬後奏之權。這樣深入各階層,搜檢各種貪腐劣跡,工作十分繁重。談不上大成績,只算盡力苦勞。
二十三年春,奉召出席南京工作會議,得到一點口頭嘉獎。回延之後,為了工作方便,戴先生介紹我認識福建水警總隊長李國興,給我閩江水警第二大隊附名義,並無薪水。同時另介衛立煌,請其給我連絡參謀名義;我見過衛,但他並未發表我的職位。
彩耀來到我家,掛了空名的媳婦,自然寂寞,要求我父送其來延平,父親沒有來信通知,即陪她同來。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自認命運安排,為時代犧牲者,不得不把她留下。彩耀為想控制我,不久邀其二兄鄭佩賢、三兄鄭佩傑來到我的身邊,我說,沒有職位容納他們。他們表示不計職位待遇。我無法令他們回去,只好任佩傑在家裡燒飯打雜,佩賢跟班跑腿。七、奉調福州工作及初為人父
由於五次圍剿的成功,共軍向西突圍,閩、粵、贛次第肅清。陳儀勵精圖治,省政漸上軌道;閩北走上新建設,已無變亂之慮,上令撤銷閩北站。二十五年初春,我奉調福州站副站長。站長卓飛,本地人,黃埔四期生;。閩變時他潛伏福州,建功甚大。
我攜眷到了福州,即住東大街旗汎口站部。陰曆二月二十六日,彩耀誕生一男,因為生於福建,即取名毛建。她知我不愛她,見我很喜愛孩子,即不自己哺乳,三年之內,連生二男一女,都交奶媽哺養。
毛建自小即肥頭大耳,強壯活潑,與群兒遊玩,常被其推倒,不知哪個給了他綽號「火車龍頭」。次子是彩耀回江山生產,產後攜奶娘同返福州,我去洪山橋碼頭迎接,我子已能爬動,十分可愛。據告:家鄉什麼老先生把他取名「毛吉(吉旁)」,我說:那是不常用的字。
隨即取名毛革。他與長男個性不同型,自小本分忍讓,不與別人爭強好勝。三女是在協議離婚時出生,把她取名毛綏,以示我們最後愛女,安和吉祥,各得幸福歸宿。
其母對她憎厭,生下即交我母撫養。中共統治之後,可能隨聲錯寫,變成了「毛瑞」。我家因受我累,家破人亡;瑞兒被視為不祥之人,無人肯收容,四處乞討,流浪至玉山,與貧農祝發金結合,生了二子四女,常被其夫毒打,一九七九年離婚。
她於六十年代初,與我們取得聯絡,才得接濟其生活;大陸開放之後,本擬接其來美團聚,一九八三年十月,不幸腦溢血,病纏至今,真苦命兒也,建、革二兒,則於抗戰勝利後,接來上海團聚,得到良好教育。當時妻也要我把綏兒一起帶出來,但老母迷信,說是算命先生說,綏兒的生辰八字與我有沖,不如留在她身邊作伴,等小學畢業後再帶出來念書。不想這一延誤,造成她的終生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