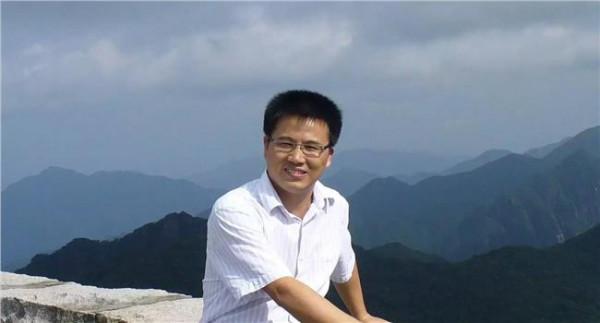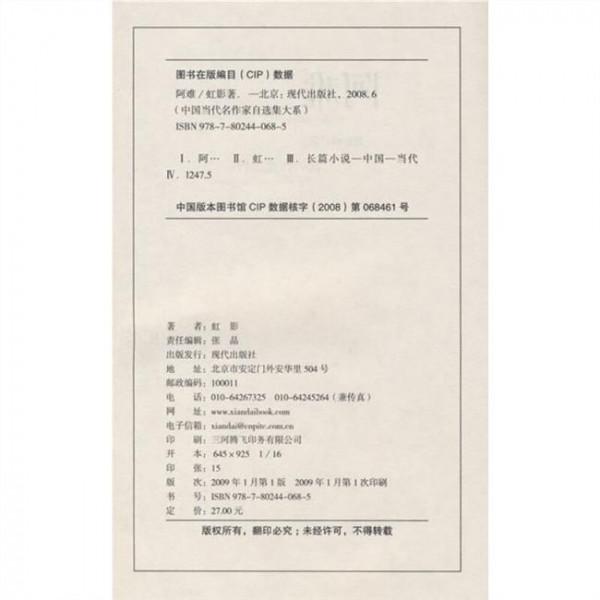虹影阿难 为何去印度——评虹影《阿难》
约一千五百年前,玄奘法师翻山渡水、历尽艰辛去印度,而在虹影新作《阿难》中,女主人公的目的地也是印度。当然,后者的旅程不再含有《大唐西域记》的传奇和历险色彩,大型喷气客机使得现代的印度之行似乎并无悲壮可言,但是,与人们一般愿意注意和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我从不赞同将八世纪玄奘的故事理解为马可波罗式的努力──如果我们过份地宣扬它的神奇性质,则不啻于遮蔽了这个事件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上一种真正的特殊性;简而言之:玄奘的举动乃是激于宗教虔信之渴念。
此一渴念,虽不可由一般中国人的内心来否定,但确为中国本土文化典籍的精神所否定。亦即,我们固不便声称中国人内心天然地缺乏宗教情绪,然而作为世界古代几个伟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化,唯一不曾自发形成而由外域输入宗教虔信体系却是事实。
疏理这个话题颇复杂,不过儒家伦理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石,充当其结构者,无疑是抑制和阻止宗教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儒家伦理建立了一个有别于宗教的解决社会和精神焦虑的独特方式,而且由于它的行之有效,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不能像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取得精神的权威,即便佛教也是如此。
佛教在中国能较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为广,恰是因其神学意味不如后二者浓厚,许多士大夫对它的兴趣与其说出于神学,不如说出于哲学。
观佛教传入及立足中国二千年史,番僧不断东来,而汉僧逆向往佛教发源地求经朝圣者,仅唐代有玄奘、义净等六十余位,以后竟就绝迹。此一现象充分说明,中国人之于佛教,不重本原的溯求与归应,而专执于与本土文化的互证互融,且修身成分多于虔信成分,致其伦理意义大于信仰意义,这也大大迥乎一般的宗教态度。
中国的社会在非宗教的氛围和结构中生存了二千多年,一直安然。它的被触动,还是因了最近这一百来年的历史。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不惟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也在精神领域引入了信仰思考。西方文明的侵入首先便以十字架为前导,尽管由于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罕见的非宗教化特质,十字架登陆中国的努力,除开它的医疗、教育部分,几付东流,全无在非洲、美洲大陆那样的成效,可是信仰体系的问题却就此在中国提出了。
清室甫终,袁世凯政权便企图假立宪尊儒学为「国教」(陈独秀批判为「以国家之力强迫信教」),于是,中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宗教基础、「孔教」够不够格乃至它究竟算不算宗教等话题,一时成为舆论焦点;此议虽随袁政权迅速倒台而作罢,问题却留下了。
到二十世纪晚期,现代化进程再获延伸之日,这样的问题也以新的背景再次发生。一是在文化反思层面上,韦伯(Max Weber)有关基督教与近世资本主义之关系的理论,在中国知识界深获人心,并促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总批判从历史、政治、社会的眼光移到信仰和精神体系方面;二是在生活实践的层面上,信教特别是信基督教突然成为一种时髦,80年代大城市教堂恢复宗教活动以后,人山人海,几成奇观,虽然蜂拥而至的人群里有多少人出于明澈的虔信很值得怀疑,但对信仰的好奇和朦胧的需求却反映出现代性概念下的社会心理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某种固有危机。
《阿难》的主要故事,正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从诸多方面来看,阿难是一个精神危机象征;这种危机,部分是他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个体的存在危机,部分则作为一种缩影,以反映置于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厄难。
在这本对侦案小说具有戏仿意味的长篇小说中,虹影尝试提出罪及救赎的主题:阿难之罪及社会历史之罪。「罪」在这里,并不简单地与「恶」划等号,它更多表示一种偏斜、罅裂、不自足以及失去支点的状态。作者所以戏仿侦案小说,可能的解释是本书情节也隐含着罪与正义之间的冲突。
不过,此处的正义远非一般的社会概念,而是精神归宿的追询。阿难其人,一而二,二而一──是阿难,是黄亚连。作为摇滚艺术家,叫阿难,而除此以外──作为商人、在逃的经济案件嫌疑人以及孤儿──叫黄亚连;在项目组负责人孟浩眼里是黄亚连,在女作家「我」眼里则始终是阿难,或者,始终与黄亚连明确区分开来(页214:「『那是黄亚连,不是阿难。
』我也不知道为甚么要强调这点。
」);最后走入滔滔恒河水中的那个人,是阿难。作者以圣徒之名相穿凿,有多种寄意,而主要的两点,一是关乎救赎,二是以字隐义。难者,灾也,厄也,困误不明也。阿难从孤儿到歌星到商人到沉寂恒河,一生漂泊,苦无所依,尽在一个「难」字当中。这或许并不只是一种个人遭际抑或小说者言,而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处境。我曾在自己一本集子的序中写过以下的感想:
漂泊者,是居无定所的人吧?我想,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经历,使我内心有一种无所执的状态,实际上也不知究竟该执甚么。……有时,读着自己留下来的文字,不禁悲自心来,因为从中我找不到一个完整的自我。……无根、漂泊、选择和改革,古老的中国及其文学,自从被迫走出它的老屋以来,就一直「在路上」。
所以,读《阿难》尤其让我尝到一种「于心戚戚然」之感,虽然我没有他那样的遭历,性格也毫不相干,但魂灵却在同一处痛着。
阿难的出生、成长,无不伴随二十世纪全球化和民族冲突两大文化背景的激烈碰撞,而在这种碰撞之中,他突出的命运是「无力」。突然间丧父亡母成为孤儿;少年时代受累于父亲历史和中印冲突;文革中随人流冲进英国代办处纵火;80年代的摇滚巨星;后摇身一变,从叛逆的艺术家变成唯利是图的商人……其人生轨迹,常自相矛盾,乍看令人不解,例如他由于身世而历来为极左政治所贬抑打击,但其所做出的纵火的极端之举却连许多极左份子亦望尘莫及,他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一个骇世惊俗的先锋派艺术家变成商品拜物教的信徒。
这样的大矛盾大逆转,绝不仅仅发生在阿难身上,事实上,这种情况自二十世纪以来,在几代中国人尤其是它所谓「精英」群体亦即知识阶层的身上,在无数青年学生、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身上,屡见不鲜;毋如说,我们若想找到人格和思想完整如一的例子已难乎其难。
这种普遍并且似乎没有尽头的自我背叛和扭曲,多被从个人质量上检讨着、拷问着,直到不久前,还有一位文革中曾名列「写作班子」的文坛闻人被这样质难,但质难者恐怕无法解释,这种个人质量的追询如何面对显然并非个人的整体「堕落」的事实,而且,除了文革那样一个特殊的可以用「堕落」来描述的时代,在上世纪其它一些重要时代──例如90年代、50年代、40年代(延安)、30年代和20年代──知识阶层何时不在抉心自食?又何尝延存了完整统一的灵魂?「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郭沫若这几句诗,岂止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更是走向现代性以来中国人在精神、心灵上那种必然命运的谶语!
这命运,就是漂泊、无根、撕裂和难以自掌的命运。卷入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最深刻的困境并不是经济或知识体系上的,那可以通过「转型」来克服,而有一种困境既必然发生又无法克服,亦即对自身文化的不认同(或曰难以认同)。
二十世纪中国诸多大事件(包括文革在内)、大论争以及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分裂现象,甚至一些杰出人物如毛泽东、鲁迅身上复杂的矛盾性,皆以此为最终解释。这种与自己为敌的处境,不单单蚀损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它真正可怕的前景在于精神「归途」的惘失。
从国家到个人,对精神「归途」的寻求始终未断,有如孤雁飘零;人们寻求过德先生、赛先生,寻求过进化论,寻求过马克思主义,寻求过人道主义,寻求过存在主义……结果都因无从解决与固有文化历史的关系而搁浅。现代化进程每前进一步,上述困境也就加深一层,事到如今,精神基础的脆弱与暧昧,已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完整性、凝聚力,乃至民族的长远生存。
我以为虹影所看到和表达的,正即此也。有着游记般美丽和罪案小说般悬念的《阿难》,实际上是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精神危机的一次长镜头式铺览,是对精神上「家」的概念的追问。《阿难》结尾处隐晦地写道:「你是那种『黑寡妇』的贪婪的雌蜘蛛,我将让你吞食我,一口口撕咬吞进你的身体,在一场忘情的交合之后。
」这个令人震惊的句子与场景,也许将是对全球化下文明冲突的最深刻的象征。作者有多年国际化生存的经验和体会,在这当中,中国人在「现代性」时代的精神无归或悬空状态,想必更具体,更有质感。
然据我看,虹影虽敏感、痛切地揭现了中国的精神困境,但她也仍不能摆脱对于「归途」的困惑──这正是读《阿难》后我不能不提的问题:为甚么去印度?
表面看,一千多年前玄奘去印度,阿难、「我」则在二十一世纪伊始也去印度,似乎构成某种「历史的回声」,然而这里面包含了错觉──也即前文指出了的:玄奘之去印度,个人精神的意义远大于民族文化的整体意义,虽然也对文明传播垂功至伟。
关键在于,先秦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形成其自适、自足、有效、运转良好的结构,它足够支撑中国人的精神,供给情感与理智之所需,解决疑问或危机,以是之故董仲舒才敢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此外的文明输入皆不过是微调和补充。
有所补则纳之(如佛教),无所补则任之(如耶回二教)。无论佛教东输还是玄奘西游,都不表示中国人的精神基础有所欠缺而欲获一新的支撑,而仅因其义理有可采之处以益人心,所谓「儒主入世,释主出世」而已。
到近世,中国固有文明的有效性却遭到彻底否定了,鲁迅说:「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又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追逐现代性的过程根本废止了自我文化的参照系,对价值的主张已无法从固有典籍中获得,转眼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便成一堆废纸,中国人则实实在在成了灵魂上的没有家园的流浪者!
这才是清末以降中国持久的精神危机的真正根源。问题不在于中国文化有没有一个宗教核心,不在于中国人心灵是不是缺少宗教的支撑。假若固有精神文明未遭废黜,假若固有的哲学、价值体系仍可以运转,则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充分性和完整性并不亚于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或任何其它的人们。
所谓宗教的必要性、不可或缺性,并非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规律,事实上,在过去二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虽不基于政教二元结构,仍然运转良好、协调,甚至比多数文明更为健康(这不意味着否认它存在种种弊病)。
毫无疑义地,在探究现代性之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时,没有可能从宗教的角度切入,也无从使结论归结到信仰匮乏上──本质而言,此类思考对古代中国纯系伪命题。
但二十世纪后,同样的提问却变得极真切,且日益难以回避;文革后中国据说面临了「信仰的真空」,实际上,「信仰的真空」何尝是文革后始有,自无奈踏上现代化之路、远离甚至不得不亲手破坏自己的精神家园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被悬于「信仰的真空」。
恰恰是在这里,我们被西方价值观──例如韦伯式理论──进一步误导着,认真地以为自己的不幸的症结,乃是缺少一个类似于基督教的信仰体系的支撑。虹影笔下的「我」追寻玄奘足迹前往印度,以及目睹阿难一步步走入恒河洗涤灵魂的场景,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幻觉:对得救的途径或曰精神出路的幻觉。
但是,此因非彼因,此果非彼果。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并非其文化上先天匮乏宗教所致,更非走向恒河、耶路撒冷、麦加所能替代地解决。中国人的希望在于,能够回到自己固有的精神家园,简单地说,就是重新认同、肯定自己的历史、伦理和价值观;舍此别无他途。
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不论眼下看起来还何等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