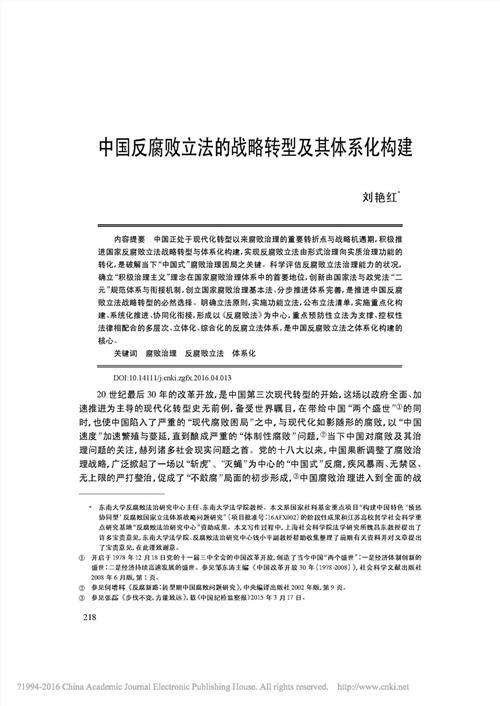重庆刘艳红 刘艳红、钱小平:中国反腐立法体系建设重大现实问题与对策建议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反腐败立法建设,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初步构建起相对完备的反腐败立法体系,这一立法体系在总体上由“党内法规范”与“国家法规范”构成,其中,国家反腐败立法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核心是构建腐败惩治的刑事法律体系。然而,面对现代化进程中腐败衍生与恶化的状况,立法体系出现了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影响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甚至严重危及了国家安全与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立法科学”是法治中国建设之关键的重要论断,使反腐败立法的科学化被提上了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中国反腐败立法体系建设,尚存在难以与艰巨的腐败治理任务相匹配的问题,更无法为中国清廉社会的构建奠定法治的基础。为全面提升中国反腐败立法的科学性与腐败治理能力,有必要全面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的起草与制定工作。
中国反腐败立法体系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反腐败立法建设,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初步构建起相对完备的反腐败立法体系,这一立法体系在总体上由“党内法规范”与“国家法规范”构成,其中,国家反腐败立法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核心是构建腐败惩治的刑事法律体系。然而,面对现代化进程中腐败衍生与恶化的状况,立法体系出现了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影响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甚至严重危及了国家安全与党的执政地位。这些重大现实问题集中表现于:
一是反腐立法理念仍受制于“应对性”治理的观念影响。在国家严厉打击腐败的政策导向下,党内、党外反腐立法不断增多,惩治力度不断加大,但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7年至2012年腐败案件的立案数量来统计,贿赂犯罪的数量不降反升,大(要)案高发、犯罪纪录屡被刷新。导致这一问题最为关键的原因是立法理念仍停留于“不敢腐”的层次上,立法重点偏离了作为腐败治理核心的“不能腐”层面,以刑法为中心的腐败治理,重视事后的应对性治理,而忽视了事前的预防性治理,由此引发腐败治理的严重瓶颈。当前中国腐败的类型已从个体性、“独狼式”腐败向群体性、“环境化”腐败演变,而反腐理念却未能适时进行调整,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财产登记与公示制度等具有事前预防功能的制度难以法制化而得到全面实施,成为反腐败立法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原因。
二是预防性立法过于分散。目前全国仅有汕头、珠海等少数地区制定了地方性腐败预防条例,缺乏统一的国家预防法。尽管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预算法、审计法等国家立法设置了部分条款,承担了部分腐败预防功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预防原则、标准与制度指导,且在治理理念上根本性地将腐败治理的希望寄托于刑事惩治法,这些立法普遍存在监管范围窄、监督不透明、问责机制缺乏、责任威慑不足等问题,难以产生积极的预防效果。
三是“二元化”反腐立法体系所设定的容忍度标准区分度偏低。中国的反腐败立法体系由“党内法规范”与“国家法规范”构成,这种“二元化”体系的优势在于,通过设定不同的腐败容忍度标准,不断降低社会对腐败的容忍限度,在运行规律上,应当以党内法规范建构腐败的最低容忍标准,进而,通过国家法惩治较为严重的腐败犯罪。然而,两套反腐规范的设计基准高度重合,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对腐败的评价标准一致,缺乏阶梯化的功能区分。
四是社会管理立法的反腐功能评估机制缺失。不断开放公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的范围,而实施法律的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趋势,社会管理立法成为立法发展的重点,据此,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公共管理立法,各项立法分散在各种规范性文件、规章、行政法规、法律,包括党内的法规之中,但诸多立法对公共权力的腐败预防功能重视不够,有的部门立法甚至本身就是腐败的产物,或是滋生腐败的根源;在具有反腐功能的立法中,有的反腐败功能强大、效果明显,有的则效果并不显著,可有可无。低质量的反腐败立法浪费了立法资源,降低了立法运行效果,不符合法治反腐之要求,应当及时从立法体系予以调整,但目前缺乏有效的立法后评估机制,难以识别低质量立法,是导致反腐败立法规制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促进国际反腐合作的国内法基础有待加强。中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积极开展了国际反腐败合作,但在国内法上仍然缺乏与国际反腐败公约相互协调的平台性、对接性法律,不利更为深入地展开国际反腐败合作。
中国反腐败立法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