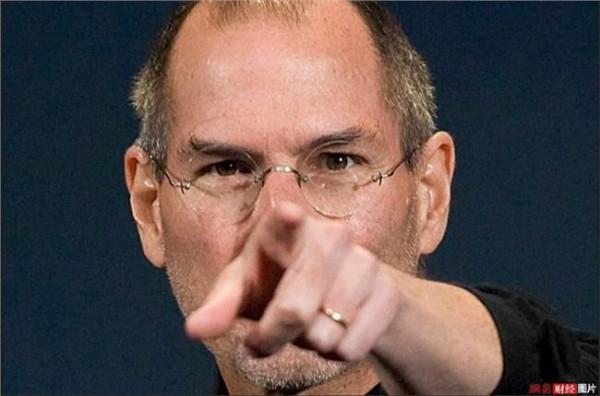陈思和莫言 陈思和:我对莫言三个故事的解读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作为莫言的客人,与莫言一起前往斯德哥尔摩,参与了诺贝尔奖颁奖盛典的全过程。他回来写了解读莫言演讲的长文 《讲故事的背后》,这里发表的是部分内容。
莫言在众多媒体(主要是西方媒体)的争议声中走上诺贝尔讲坛,他本来可以对媒体上的误解与攻击置之不理,因为能够代表桀骜的中国形象登上这个西方神圣讲坛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他的胜利。但是他还是愿意回答这些误解与攻击,方式仍然是讲故事。
他说:“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又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面的两句话,让我一度把这一部分的三个故事解读为莫言在西方媒体面前的自我辩护,后来细读之下,我觉得我的理解不全面,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莫言在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把这三个故事看作是作家站在世界讲坛上对更多的听众讲述的寓言,通过三个故事表达了人们所关心的莫言有关个人与社会、体制和宗教的三重关系。
当然,莫言既然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就注定不会有明确的结论。故事不是猜谜,可以有多种理解和诠释。我仅谈谈自己的理解。
第一个故事,还是从莫言的自我忏悔说起。他说了他在念小学时的一次告密事件:在集体参观忆苦思甜教育展览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了表示悲伤而努力装出痛哭的样子,只有一个同学没有这样做:“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
他睁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这是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在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教育下已经开始出现了扭曲心灵的伪善性格,把原来发自内心感情真实的“哭”演变成为政治上表示进步的举动,不仅如此,由于伪善行为本身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所以他们特别害怕看到有人在这个集体中不参与表演的行为,伪善者特别讨厌的就是真诚,因为在真诚的面前,伪善者就感到了作假的困难。
那位没有参与痛哭表演的同学并不是什么觉悟的先驱者而只是心灵中单纯善良暂时还没有受到戕害。但是很快灾难就来了,有十几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这个同学,其中也包括莫言。于是这个同学受了警告处分。单纯的孩子无法在虚伪成风的环境下苟且地生活下去,他只活到四十多岁就死了。莫言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如果在一个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对这个故事都会产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当一部分人们对于某种外在理想原则作了绝对的确认以后,这部分人们就成为一个“集体”,他们在共同的理想原则下生活,为同一的理想而奋斗; 这对于自愿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理想的信仰,无论宗教、政治、党派都需要克服个性的欲望和权利,以最大能量奉献于理想事业; 但是当这个原则扩大到集体以外的范围,要求集体以外的人也必须遵从这个集体选择的理想原则,这就变得荒诞和非理性。
当某种理想被强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并且利用集体的统治力量使它成为人人必须遵从的教条的时候,那么荒诞也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它会摧毁所有影响所及的人的个性选择。
中国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王道,但事实上人类世界历史上无数的战争、杀戮、镇压、刑法等等,都是在“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堂而皇之的正当理由下进行的。这是人类通往奴役之路还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分歧点。
一旦选择了奴役之路,那就意味着个性的毁灭,所有的人必须被迫伪装成服从,尽量使自己取得与集体的同一性。因为只有在这种集体的同一性下才能获得安全感。莫言把“当众人都哭”和“当哭成为一种表演”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集体与个人的异己关系,而后一阶段,则是在个性已经被毁灭的前提下个人是否还有消极存在(不伪装)的可能。
我突然觉得,莫言的这个故事呼应了巴金先生生前呼吁“讲真话”。巴金的呼吁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讥笑、讽刺和鄙视,那些讥笑者故意混淆和模糊“讲真话”的背景,把“讲真话”曲解成“小学二年级”学生就可以做到的低级要求。
但是在巴金看来,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要做到“讲真话”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在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持不说假话。
“讲真话”和“不说假话”也是两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后者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为之的保持操守的措施。而莫言的这个“小学生装哭”的故事,又一次明确分清了两类“不哭”的允许范围和限度。
第二个故事,看上去过于简单,寓意也不明确。故事发生在军队期间,莫言一个人在看书,老长官推门进来,显然是找平时坐在莫言的办公桌对面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不在现场,于是老长官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人?虽然用的是问号,但明显不是在问莫言。
少年气盛的莫言被这种漠视他存在的态度所激怒,于是冲动地抢白老长官:“难道我不是人吗?”这样的调侃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经常会遇到的,并没有什么尖锐性的含义。这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1980年代初人道主义思潮刚刚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作用的时候,在这个背景下大声疾呼“难道我不是人?”留下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
但是,莫言在这里偷换了对话中“人”的概念:老长官说的“没有人”是指他所要找的那个“人”,敏感的莫言则把“人”泛化成为所有的人,概念的人,成为大前提,于是就有了小前提:“我也是人”。这是典型的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思维方式。
那么,莫言感到内疚的是什么呢?是对老长官不够尊重?是故意曲解了老长官说的“人”的所指?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老长官作为领导漠视了下级军人莫言的存在。所以他描写了当时的心情:“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
”这是一个向体制要人权的寓言。契约是双方的,作为一个下级军人珍视老长官的权威,那么他必然在乎老长官对自己是否在意。“难道我不是人吗?”其实是抗议老长官对他的漠视。但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反问莫言:难道你是不是“人”还需要“问”老长官吗?你需要由老长官来证明你是一个人吗?这又回到了演讲的第一部分的故事,当莫言告诉母亲,别人都嫌他“丑”而欺侮他时,母亲对他说,你并不丑啊!
你五官不缺、四肢健全,为什么说你丑呢?关键还是你自己能否心存善良,能否多作好事。
所以,一个人是“丑”还是“美”,要通过自己的遗传基因、内心本能及其实践来证明,而不是依靠别人的眼睛来确认。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推论莫言后来真正感到内疚的,应该是他“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的幼稚行为。
“难道我不是人吗?”的提问需要看对象,看你是对谁提出这样的问题。联系到前一个故事,如果是要这个假哭的集体认可你是一个“人”,甚至是个“模范的人”,那你的前提就是,必须裂开大嘴嚎哭,或者用唾沫抹在眼睛里冒充眼泪。
我们从莫言的小说中看,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开始,莫言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几乎都没有人把他们当作人看的,而是他们自身的生活实践中,那种大胆无畏、放荡无度的元气淋漓的生活方式(像余占鳌,九儿),或者不屈不饶、九死不悔的倔强的生活选择(像西门闹、篮脸),为自己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这才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具有独立价值的人。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从老一辈那里听来的。这个故事似乎涉及个人与宗教的关系。莫言在演讲词里公开说:“那时(指童年———引者)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
”这种万物有灵的民间宗教,不能简单归为佛教还是道教,或者是其他什么宗教。我以为莫言从小接受的是民间最普遍的有神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头上三尺有神灵。
我们在人间做什么事,也许自己并不明白是善还是恶,只有当你做了以后才能知道,因为有“神”的眼睛高高在上。在雷电交加面前,这八个泥瓦匠可能都是无辜的人,因为处境危急,才使人生出疑惑:需要选择一个“坏人”,通过惩处他来拯救其他人。
这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而是古代的活人祭祀的野蛮方式。但是在离我们现在并不遥远的历史上,这种野蛮祭祀的现象曾经频繁地出现过,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抛出百分之五的人进行活体祭祀,用他们的牺牲来保护大多数怯懦者的短暂安全。
于是集体就犯罪了。所以当八个无辜的泥瓦匠决定选其中一个无辜的人作为牺牲的时候,另外七个人就犯罪了,受到了神的惩罚。这个故事显然不是来自西方的宗教故事,而是一个被世俗化了的中国民间神话。
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离开忏悔的主题,但是忏悔的主体扩大了,不再是莫言个人的忏悔,而是他把自己融入了这个有罪的群体,提出了集体忏悔的精神要求。人不是天生有罪的,而是在他人即地狱的人世间,你随时可能被当作有罪的人给抛出集体,也可能因为抛了别人而犯罪,被压死在雷电击毁的庙宇里。于是,你到底做那个被选出来的泥瓦匠还是另外七个被压在废墟里的泥瓦匠,只能由你自己来选择。
第一个故事讨论人如何使自己保持真实,第二个故事讨论人如何才能证明价值,而第三个故事,则是讨论人何以为善。莫言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