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陈涌 陈涌海:水的外表火的心
陈涌海怀抱吉他,坐在大厅的红木桌上,弹唱自谱的《将进酒》,曲风苍茫慷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一旁倚坐木椅、须发皆白的老人,击节颔首,陶醉其中,是艺术大家钱绍武。陈涌海的朋友杨一拍摄了这段视频,放在网上大受热捧——乐者何人?有人搜索出胡续冬的旧文:“陈兄涌海,湘人,北大物理系86级老青年一枚,科学家乐手,主业为中科院半导体所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量子、纳米之余,弹琴复长啸,纵情民谣中,十年一觉民谣梦,当年乐手多不再,唯陈兄涌海,虽步入怪叔叔之年,琴上行走如故。
”网友拜服,有附诗:“太白高风卷地起,扑面方知来沧海。遥见猛士击大鼓,天籁纷纷入我怀。”一位高三老师也留言,平时班上对文学艺术不屑一顾的理科生们,听完震动:“原来,科学家可以那么感性,古诗词可以那么迷人。
”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陈涌海和记者喝茶。细格衬衫,细框眼镜,清秀斯文,很知识分子——“你给我一把吉他,周围都是朋友,我就能放开,嚎一曲。
”看似平湖秋月,心中则有猛虎,细嗅蔷薇。陈博导研究物理也当有激情,只是实验数据显得冰冷;而艺术能够挖掘、翻滚、爆发这份激情。他在办公室和家里各放一把吉他,弹唱吟咏,拓展精神。
你为看到的五分钟惊叹,于他只是最普通生活。他造了两个迥异而交融的人生,并在每个维度行走自如,自得其乐。艾青曾举起酒杯吟道:“酒,是什么?酒是水的外表,火的心。”唱摇滚的科学家,好一杯美酒。
李白和刀子有个媒体朋友对陈涌海说:“你唱《将进酒》的一刻,是李白附体了,要是李白坐在我身边,肯定就是这个样!”陈涌海边笑边答:可能是吧,不清楚。他自认为并不是那种霸气豪迈的人。
“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很豪气。钱老(钱绍武老人)捐了自己的字画,近两亿的财产都捐给清华了。还有许秋汉,有兄弟要去西藏采风,他几乎倾囊而出,真是千金散尽还复来而我,借大钱出去得跟老婆商量。”前不久凤凰卫视做了一档校园民谣访谈节目,也访了陈涌海,“都是八九十年代北大草坪音乐会那拨儿朋友,现在这批人有的当董事长,有的出国。
继续弹的,少。”他还在弹琴。性格也无大变,理性做事,淡然待人,多属君子之交。
中学当宣传委员,总是自己写完整版黑板报,不指派人。上了大学,卧谈会不谈姑娘(当时整个86级物理系也就12个姑娘),都是谈国家大事,一宿舍的男生,“嗒嗒嗒”谈到深更半夜。除了诗歌和摇滚,他没有什么爱好。
“我们那一代娱乐不多,很有理想主义情怀。现在的大学生,不分房子,不管就业,物质诱惑和外部压力都大多了。不过大学生本心单纯,还是理想化的,我认识一个外号‘万能文艺青年’的,诗词歌赋都行,休学一个学期,去小山村教书了。
这种人哪个时代都有。”如今老朋友不太弹琴了,陈涌海不免孤独,慢慢结识了新的音乐人,“互相闻到味,就会靠近。”基本半个月聚一次,搞艺术的多,画家、诗人、音乐人,喝高了就敲着盘子唱歌,吟咏,一众人等撞碗碰杯,不亦乐乎。
陈涌海喜好给古词谱曲,比如李煜的《渔父》,张玉娘的《山之高》,李白的《月下独酌》,又觉得古代诗词题材狭窄,不外乎抒发离愁、怀才不遇等等情绪,跟现代诗歌的含义相比,太过简单。
谱完七八个曲子,就觉得到头了。《将进酒》是三年前谱曲,最近突然火了。朋友们在饭局里起哄,我们团里出了明星啊。他讪讪笑,顶多是个网络红人。他跟记者客观分析:“主要是摇滚科学家有个噱头,可以炒作。把时间腾出来去追逐名利,可以,但我不愿意。
这首曲子也不完美,我自己看龚琳娜唱的《将进酒》艺术价值更高。”他收到了很多选秀节目的电话,口号是“你有这个梦想,我帮你实现”。他一概婉言谢绝:“这不是扯淡嘛。我的梦想用不着这个来实现。
”又话锋一转:“李白失意后索性诗酒人生,等我哪天也失业了,也有可能去卖唱,哈。”他弹唱吉他几十年,从没想着和名利勾连。西夏和陈涌海是青春时期“通过大音量放摇滚结识来的朋友”。多年前,年轻的陈涌海上了台,麦克风有点失音,他仿佛自言自语般唱歌,人们在台下哄闹。
西夏急得大吼:“陈涌海!不要怕!给我挺住!”西夏回忆说:“那时候,挺住意味着一切。现在,过气的校园歌手也大都没什么好歌唱了,只有纳米科学家陈涌海还在温文尔雅地叫嚣:做不了刀子,也要做刀把子。
哪怕做生锈的、钝刀的刀把子,也要跟刀子在一起。”陈涌海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开始兴致不错,火锅欢腾,涮肉飘香,后来大家聊到股票基金上市什么的,陈涌海就如坐针毡。
第二天他去猜火车吧喝扎啤,又去“江湖”看周朝演出,感觉到“一种放任自在与激越不定纠缠在一起的奇妙的感受”。那晚,他在豆瓣记录:“周四到周五,都是很好的月夜。孤月高悬。人世的繁花或者冷清,都是一样的清辉。
想起刚读的李白一句: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每次都不过是仓皇而归。”李白那句诗的前后是:“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讲述秋日静美,但觉无聊,于是李白携友同行,探访一位姓范的隐士。
而陈涌海能携谁、去探谁呢?时过境迁,落了仓皇。废墟上的张木生1986年刚刚来到北大的陈涌海,花了两个月饭钱,买了第一把吉他“翠鸟”。大学时期功课很紧,在北京科技大学读研时才有闲心玩吉他。
有一搭没一搭地弹,没有找人学。大概是1991年冬春,陈涌海参加了一次大学校园创作歌曲交流会,不唱温和民谣,而是嘶吼的摇滚。下台后认识了北大新生许秋汉,摇滚乐队“常规武器”的队长,就一起在北大草坪上唱歌,释放荷尔蒙。
下了晚自习,深蓝夜空,青青草坪,有人唱歌,有人咏诗,三五成群,听闻年轻的高晓松也在其中。那时,陈涌海也常去圆明园的废墟喝酒,情绪上来了,就想一吐而快,1993年写了《废墟》。
“我是杂草从生的废墟,我的残缺是我的美丽,我要你收藏我伤口中的诗句”之后来段独白:“我是典型的无话可说者,我只盛开米粒大的花儿,只有片刻的芬芳,风雨来时我会落下我所有的花瓣,免得说它们是塑料的。
”这种略带颓废的幽默,只在他弹唱时涌现。1999年他写了《单人床布鲁斯》,其时在中科院半导体所攻读博士学位,一副淡定理科男的风格。“老杆写了15页的信。给100米以外的人。
自己去当邮递员啊,还拉我去当电灯。老隋开了啥技术公司,在华尔街用模型炒股。老哈摇身变成了海龟,爬进了《名人》《财富》而我学会了气沉丹田,弹我的单人床Blues。”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校园合辑《未名湖是个海洋》,收录了陈涌海的作品《张木生》。
张木生是他虚拟的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山里来,苹果脸。城市很快让张木生的脸生了锈,空空如也的口袋掏不出钱,只掏出来尊严,又迷失了回去的路——“不知道谁摁下了他的play键,他又喊又叫走在最前面。
这个城市一定有病,但他只嫌自己病得太轻,白天夹着尾巴西装革履,黑夜里拿着刀子自己修理自己”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无数朋友从天南地北而来,身怀绝技,集聚一堂,饮酒弹唱,各尽其彩。
他谈到了若干朋友中的一两个。比如诗人俞心焦。“纯粹的民间诗人,没有上过大学,瘦弱不驯,身世坎坷。他有本诗集《灵魂大面积降临》,读起来很棒。尤其是《墓志铭》和《最后的抒情》。
我曾经很肉麻地当面表示我很喜欢他,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陈涌海从提包里掏出一本素净的书,是他自己印刷的俞心焦诗集。他曾写到二人惺惺相惜的交情:“心焦数度与他人语‘YH是我二十年的老朋友’,令我动心不已——气在寻找着气,场在等待着场,酒在浇灌着酒,人生若无知己,滚也罢。
”他喜欢俞心焦直抒胸臆的畅快,也欣赏另外一类不懂声色的诗人,比如韩东。陈涌海也提到了马骅。复旦大学毕业,曾在北大清华一带盘桓,策划文化活动,推进小剧场实践,还曾将周星驰请上北大讲台,风云无二之时,突然辞职,前往云南梅里雪山下的藏区支教,次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
“马骅临走时,把他的篮球搁在了我家,当时他就住在我家附近。”陈涌海口气淡然,仿佛马骅仍在人间,随时会敲门而入,取走那个遗失太久的篮球。
毕业二十年了,多少繁华过眼,多少悲伤入心,成熟的面孔下,依然有着激情随时澎湃的胸怀。伴随摇滚走过的旧时光,幻化成了吉他弦上的图腾。
自由陈涌海现在是中科院的科学家,还是该院“杰出人才”。他曾跟媒体这么解释职业:“天主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有一切,含有物质的很多信息。我首要就是研究量子结构和纳米结构的光谱。”有学生在《将进酒》的视频后留言,说在楼道里每天碰到陈老师,而这个唱摇滚的男人让他陌生到惊艳。
陈涌海说:“我的工作和业余生活是泾渭分明的,工作时非常理性,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学生还有点怕我。”遇到不用功的学生,他不发火,而是惋惜学生浪费大好年华。
如果学生出现一些概念性错误还很坚持,他真着急。“我最希望学生能够做出比我好的工作来,这也是所有当老师的对学生的希望。”作为科学家,他严肃,严谨,不苟言笑。就住在研究所内家属区,上班只要步行几分钟。
8点到办公室,晚上6点回家吃晚饭,9点又到办公室,忙到12点才走。他放手让研究生自己去做实验,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每天处理邮件,包括学生发来的工作汇报和文章草稿;阅读大量的科研文献,准备项目的年度进展等材料;因为是实验室主任,还需接待国内外来访学者,处理跟实验室管理相关的杂事。
“其实做科研也是有乐趣的,跟玩游戏一样,达到目的时,都会在大脑产生某种让自己感到愉悦兴奋的化学物质,如果是常人难以完成的困难级别,你完成了就能分泌更多这种物质。
不然也不会坚持做这行。”科研界也有钻营的人,为了名利不惜手段,摧眉折腰事权贵,使出各种攻势。如果“攻”下一个千万元的课题,几年不愁。
陈涌海觉得“钻营”此等事情,毫无意义。“我对这个世界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理性客观。有人觉得你可以混得更好,但你不愿意那么做,那就这样呗。我不愤世嫉俗。”从湖南来京已经二十余年,陈涌海自认人生顺遂。
即便发生过可抱怨的事情,也已忘记。不幻想未来,对现况随性,他自嘲“对于有远大理想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好事。”有一次,中科院团拜会需要几个节目,被单位推荐,陈涌海答应参加。随后活动组织者打来电话,一一交代,最后问:“你快退休了吧?”他无语——在中科院,多半是退休的老头老太才鼓捣这些文艺活动。
偶尔单位组织一起唱卡拉OK,他们都唱俄罗斯歌曲和流行歌曲,就他唱崔健和罗大佑——喜欢文艺还偏摇滚,他是中科院的独一个。
独乐又何妨?去日本出差,他在JR新宿站,听两个街头音乐人鼓捣插电的声学吉他,入了迷,就站着听下去。回到科研所,一日阳光灿烂,他抱起吉他,弹唱鲍照的《代春日行》,浑身发热,“献岁发,吾将行。
春山茂,春日明。园中鸟,多嘉声。梅始发,柳始青。”他享受着艺术带来的自由和轻盈,就像他中意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由那些熟悉的城市场景抽象出来某种出人意料却又合情合理的结论,这些都让我着迷。
我喜欢符合逻辑的玄幻和飞跃。”“艺术的美可以安抚人心,让人远离功利,心灵自由,不受羁绊。有此自由,生活不但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变得美好起来。”冬雪白过窗棂,夏花落了一地,生活继续,弹唱不败。(摘自《中国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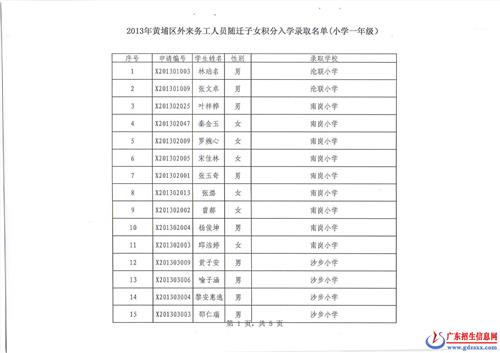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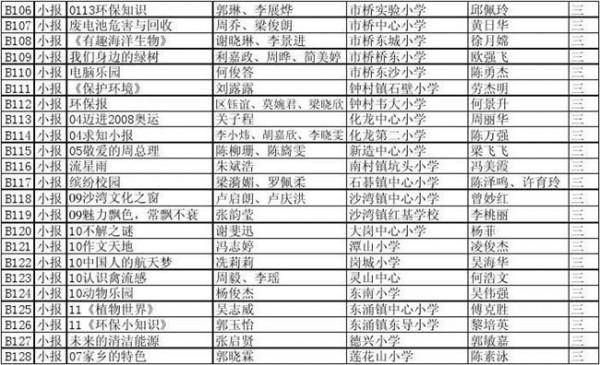


![>上海陈国庆 陈国庆[上海曲艺家协会会员]](https://pic.bilezu.com/upload/3/48/34845e795627d123c985baa9d35d4aa6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