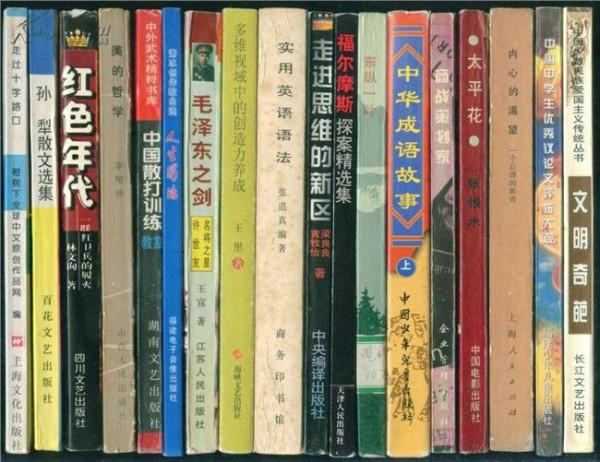此地是他乡孙甘露 【旅游】《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孙甘露:此地是他乡
就我而言,上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四十年是隐含着肉体错觉的,其余的六十年,则是一个镜像式的幻想体。因为我所无法摆脱的个体的历史,使上海在我的个人索引中,首先是一个建筑的殖民地,是一个由家属统治的兵营,一个有着宽阔江面的港口,一个处在郊区的工人区,若干条阴雨天中的街道,一个无数方言的汇聚地,一个对日常生活充满了细微触觉的人体。
十分奇怪,对于我的出生地的幻想,仿佛有一个时间上的锈斑似的顶点,虽然我在迷宫般的旧城中见过几百年前的城墙遗迹,但我的充满幻想的视线始终在二十世纪的短暂百年内转悠,再往前,那是一个古代化的现代,一个在英语中尚未将to Shanghai这个动词视作以强迫和欺诈手段雇佣水手的同义词的时代,肮脏、糜烂和混乱就要同殖民者一同到来。
此前,那个遥远的乡村中国的上海就象绢上的墨迹,意味深长而又无以名状。呃!这个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还要不断修改的想象,却出乎意料地象是一个所指。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因为感官的作用时常令我们迷惑,而一个遥远的过去却稳定地散发着仿佛是传统的光芒。
我时常自问,我是否怀有普鲁斯特式的雄心,想要在记忆深处召唤出逝去了的时光的原貌,而我也不断告戒自己放弃这种努力,那个由诸种物质构成的上海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如同一
代人的生活,如果未曾被恰当的描述过,它就是不存在的,而描述所经历的衰减、损耗和变易更加深了这一点。
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这位死于车祸的作家写道:“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
在上海的市中心,一座如今已被拆除的建筑的二楼,隔着南京路,从它的窗口可以清晰地看见上海图书馆的钟楼,如今它已被改做了上海美术馆,而在历史照片中,我们被告知,这幢建筑曾经是跑马场的一部分。如果出现在虚构作品中,这种历史变迁虽然充满寓意,但依然可以被视作是笨拙的一笔。
外滩,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那个被不厌其烦地四处展示的建筑群,曾经有两年时间,我在侧身其间的一所学校里念书,这使我有机会从它的背面观察它,从它缝隙般的街道眺望荒凉的浦东,黄浦江上漂浮着的铁腥味,着火的巨轮以及来访的各国海军的舰只。当我叙述这一切时,年代的顺序已经被打乱,因为我想着意呈现的是一幅由记忆连缀的图景,一些由语言的音节带来的触觉,由此与长久以来弥漫在我心间的莫名的沉默相呼应。
这是一个令我有一丝诧异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在某处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即使我每日行走于其间,在某些时刻,与某些人、某些事在此相遇,依然只是没有奇遇的旅行,依然只是观光客的浮光掠影般的遐想,即便是本地人,它也给你一种过客的感觉,它只是明信片上的风景,或是你的私人的照片上因暴光过度而令你目眩的背景。
曾经因各种原因在此聚集的人群,如今三三两两、若无其事地在此经过,一丝笑意不经意地在他们的嘴角掠过,令我不犹的想起杜拉斯的片言只语,“我生命中的故事是不存在的。
”“有过的也不曾有。”或者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而你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
沿着堤岸,向左右两侧望去,在目力不可及之处,分别是上海的老城和港区,这是上海最为拥挤和最为空旷之处,对我而言,这都只是偶然的与童年的嬉戏游玩相维系着,它们所代表的繁杂和辛劳,在当时都仅仅是为碎片般的记忆而存在的。
南市更象是庙宇的后院,在人间含辛茹苦的烟火之上,带有一丝天国的微光,而港区在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略显冷清的货栈,有些货物经年累月也不见有人挪动,这只是一个孩子们放学后闲逛的地方,它的郊区式的孤寂,码头工人也许是看不见的,一如孩子们所难以触摸的那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成人世界。
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一度喜欢上了黄浦江上的渡轮,花几分钱,随着人流来回摆渡令我沉思我一无所知的事物并且由此获得慰藉,江面在四季中的形态以及风雨中水面那令人窒息的味道,是最初令我产生迷惘之感的东西。流水天然地变成了一个象征,它的波澜和雾气绵绵不断向两岸涌去,似乎要使潮湿的南方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
后来,我离开江面越来越远,更多地在街道上徘徊、流连和观望,我所幻想的那个黄浦江畔的上海,消失了,因为时间的拨弄,我杜撰的热情也消失了。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多少会有一点惘然若失的感觉,你在那里度过的岁月,就是你失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它们像沙子一样在你的指缝间流走,悄无声息。在你叹息它的流逝的同时,你已经忘却了曾经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消磨时间,艰难地打发它们的。拥有和丧失,时光硬币的两面,享有它也就是磨损它,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流通。
再过五十年,杂志上也许会有这样的标题: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如人们今天在问,上海人为什么迷恋三十年代?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隐秘的对应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怀旧之风也许正是对未来的召唤。
追忆是永远不会碰壁的。它化解了人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诸多忧虑,这种优雅的伤感是作为一种弥补而存在的。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或者按我引用过的话:“它只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上海的街头茫然四顾,你不能想象人们在死后把自己安置在一个信箱里。这里面当然有近一个世纪来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但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命运,如果我们无法聚拢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们只能四处飘零。
其实这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影像,物质的外观,城市的风貌、生活场景,当然是它的精神特质的一部分,如果它具有相当的连续性话。在影像的背后,是无数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回到我们前面的观点,故事一定具有某种形式的封闭,历时性的变化总可以从共时角度加以考察。
从文化的形态看,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营垒,最多是一个偶尔被激进主义利用进行激进活动的保守主义场所。它从来不是对抗性的,它总是绕过某些东西,或者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妥协。它的矜持、含蓄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也使它避免了激进主义式的思想僵化。 这也许是人们今日喜爱“在家里、在咖啡馆、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一个潜在的背景。
我曾经幻想,有一天在上海之外的某一个地方,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中,全然以回忆的方式书写那个人声鼎沸的上海。如今,这种幻想已经荡然无存,因为我逐渐地明白,我一直就在上海之外的某个地方,比任何地理上的位置更远,由时间以我所不自知的方式令我无穷地思念它,而缓慢地失去对上海的触觉。
在文学中,那个身体的、本世纪的上海从未显著地存在过,而这个无以名状的世纪上海就要带走它所有的气味、肤色、彼此交错的眼神和神经质的但是低调的生活。也许就是这种在文学中从未建立起肉体感觉的生活,(拉什迪曾经痛切地陈述过远离故土而使肉体感觉中断所带来的伤痛。
)使我们天然地精神分裂式的生活在若干个不同的时空中,使一切生活都变成了预设。而一切体验都变成了对预设的体验。由此,上海变成了一个人们在潜意识里想要在经济上攻占,而在文化上舍弃的城市。
一种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幻觉从未如此耀眼地成为我们生活的光环。人们依然没有找到他们自己的调性,你去看一下充斥于世的比老建筑更加陈旧的新建筑,就可以知道,依附于此的生活将会更多地依赖于破坏。
事物会在转瞬之间变为记忆,从而期待人们重现它的努力。伟大的马塞尔·普鲁斯特更使我们为自己的一知半解找到了逃避的理由。对记忆的崇尚使我们失去了接触事物的能力,而记忆修改事物的能力,使我们更加沉溺于此。生活是第二位的,而关于生活的支离破碎的新教条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是上海?是什么使上海的生活缺失了愤怒和激情而变得如此莫名其妙地倾向于优雅?那些吃大蒜的、甩着膀子走路的山东人呢?那些说话带着浓重拖腔的东北人呢?那些贪吃的宁波人呢?那些大嗓门的、爱冲动的苏北人呢?那些嗜汤如命的广东人呢?我所热爱的这些声色俱全的大叔,在九十年代的新民居运动中,经过一次居室装修就变成了一种人。装修人。
你要是没有经过今日建材行的洗礼,你怎么还感奢侈地自称是个上海人呢?当然,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一个官方现实罢了。温和地说,它处在幻想的另一侧,是一个滋生细微触觉的地方。但是在一个像新装修的卫生间那么干净的地方,你要是不先用滴露洗干净你的手,你是什么都不敢做的。
这是一个向内翻转的时代,从未有一个时代人们的内心像今天这么丰富、深邃,一直深到不可测知。
如果不是一种修辞,那么,有什么比缓慢更缓慢呢?一本比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缓慢》更迟出版的小说?一种对更深的记忆的涉及?
我还记得在我的小说《呼吸》的封面上的引语:小说仿佛是一首渐慢曲……,难道我是在说,我要越来越慢的退回到记忆的深处?那里存在着什么令我难以释怀的使灵魂震颤不已的记忆吗?或者是因为缓慢的天性使我陷于想象,有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仅存于近乎静止的地方呢?
缓慢当然不是一种托辞,我记得诗人柏桦那优雅迷茫的诗句: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一切!这里连可资比较的事物也不存在,这种自弃式的态度从来都是令人迷恋而又困惑的。
缓慢还关乎气息和声音,从容地、适度地、低声地、诚恳地,试图除去一切杂质和噪音的,因为“写作是需要百般矫揉造作而后才能掌握的一种才能。”
缓慢还涉及诸多事物的比较,地点,从一处移向另一处,捷克和法国,专家和昆虫,个人和公众。遗忘的喜剧,契柯西蒲斯基,因为记忆,人们总是遗忘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写作,一种离心运动,使我们日益远离我们的初衷。由南方向北方,由东方向西方,由小说向电影,由中文向译文,由边缘向中心,总之,写作使个人变成了它的形象。
哦,缓慢还是温和的,疲倦的,歉意的,沉思的。顺便说一句,我第一次接触到“缓慢”这个概念,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遥远而迟缓的土星,处在椭圆形轨道的最远端,它莅临的周期是如此漫长而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