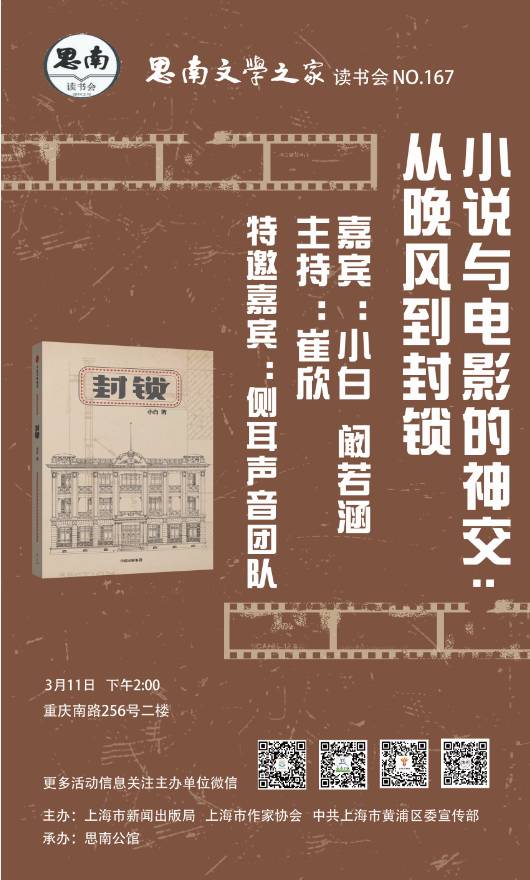王朔孙甘露 王朔vs孙甘露侃电影
孙甘露:好像电影和剧本不一样。 徐静蕾:不一样。因为它太多字了(四万多字)。后面整个从戏里面的导演说亲戚开始,全都没用。我觉得就是拍了,最后也会因为总长度的原因给剪掉。即使是这样,第一次完成片的时候总长还是有两个半小时,很艰难地剪到现在的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孙甘露:你是把剧本全都拍了,然后从里面把内容抽出来吗? 徐静蕾:前面基本都拍了,但中间有一个整段剪掉了,特别可惜。因为那一段和梦想那一段节奏有点相近。
说的话和表达的意思并不重复,但节奏上很重复。电影的节奏很重要,尤其是这个电影,稍微把握不好,就会让观众觉得疲劳。但也挺难拿下去的,因为里面有一些调度,走来走去的,后来找了半天找到一个可以合到一起的点,又在声音后期上做了好多连接才合上的。
孙甘露:我看了剧本,说的事还挺严密的。你把它拿掉一块,当然出于电影的考虑,节奏、调度、包括审查,但可能影响到对内容的理解。 徐静蕾:肯定是啊,我也很担心,所以往下拿任何东西都要想很长时间。
好在王朔一开始就跟我说,随便删减,你按你想的随便弄,所以压力稍稍小一点。我觉得光从电影上来说,拿掉也问题不大,因为一旦它影响了整个电影的节奏,我势必要删除,每次拍电影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每次都会很痛苦,但是,还是不能因大失小。
不过我想这些东西我将来会把它放在某个网站上,不会浪费。 孙甘露:完整拍,我估计得三四个小时。 徐静蕾:四个小时,完整拍。这部戏不像我以前两部电影,以前我可以整场拍戏,可以整场剪掉,而这部戏,每句话都有内在的关系,如果拿掉一句,下面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就变得很奇怪了。
所以除了上面说的那一大段之外,我基本都是一句一句剪的,稍微水点的全都拿掉。
这跟其他戏在剪接上不太一样。 孙甘露:这戏拍起来是不是特困难? 徐静蕾:拍起来是困难。比如寻找机位的问题。因为就这么一个房间,机位很少,而且方式也很少,通常就只有正反打、摇移什么的,而且,我又不太愿意在这部戏里用一些很特别的角度,我觉得没必要。
很特别的角度在电影里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比较强烈的感受——为什么要这么弄,是不是有其他的意思,而当我又没有其他的意思时,我就不要用令人产生歧义的角度。 但是还是需要寻找一些变化。
比如光影,电影中的红光,剧本里其实是没有的。拍摄当中我一直在想,虽然是一个晚上一个环境,镜头的角度又不能太特别,就要让光影有一些变化。所以后来的设计是,一开始是台灯的侧光,中间是红色的光,后来是房间的顶光,到最后是大逆光。
这要从剧本里找一些契机,找完之后还得自己把自己圆回来。比如,为了光影变化的原因用了红光,显然比较小资,正好后面有一段戏中女演员和导演言语上起了点冲突,有一个适合的机会,就让女演员乘机讽刺了导演一下:“还有这个灯,就充分的暴露了你的趣味。
”这样给圆回来了。反正挺费劲,主要是不能损失原著,尤其他的东西不是很水的东西,每句话都有内在的意思的,所以比较难。 还有当然是台词量非常大。
我通常演戏是不需要太多时间背台词的,只要翻看看就能背下来,但这部戏的台词我必须得背。晚上回到家里,在现场,都得背台词,还要想机位。很多时候觉得比较紧张。 孙甘露:剧本看着有的是水词,好像没什么意思。
但过会儿它又绕回来。当然电影不能百分百按剧本拍的。看完电影之后,其实还是值得把剧本再看一遍。 徐静蕾:我第一次读他这个剧本,看着都晕。尤其像我这种平时不太看书的人(笑),而且他的好多话确实太口语了,必须要说出来,反复地读,才能读出它的意思来。
第一眼看我有点懵,就对他说,你自己拍这戏得了,我给你当副导演。当然,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想干导演这种具体工作(笑)。 这部电影虽然没有炫目的情节,但是其实信息量很大,最后出来也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没有给观众喘气的时候。
我听说观众笑得最多的地方是“光和光怎么打招呼你知道吗?”这句话。我就想为什么这个地方反应最大?这肯定不是全剧最搞笑的,得出的结论是:我在那中间停顿了比较长的时间。
“光和光怎么打招呼,你知道吗?”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停了一会儿才说:“最黑的地方”,给了大家一个想的空间。也许是这样吧。做声音后期的人,说他们每次做的时候,都在不同的地方笑和有反应。
这就说明,第一次看的时候,信息量太大,他们根本没反应过来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过了。 他的东西,能删的我已经逐字逐句地去删了。我将来可能会做一个电影完整版本的剧本,对照起来就很清楚,哪句拿掉了。
剩下的我真的不好再拿,再拿可能会简短一点,但是不完整了。 孙甘露:我是先看剧本,后看电影。在我看来,王朔说的不单是梦想和现实,这是个隐喻,当然也可以从比较白的方面来理解。我觉得他这种说话的方式,花了那么多年,找到了对当下现实很准确的一种描述。
徐静蕾:是的。你可以简化成为名字《梦想照进现实》,理解为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多数人都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也是我为什么舍不得拿掉很多东西的原因。他也说找到一个新的语境。
对我来说,它把很多我明白但我可能说不出来,也很难用几句话表达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孙甘露:他反映了当下中国人说话的一个真实的处境,人与人的关系。现在,人与人说话,如果都特别真诚,说着说着,与现实的关系就有点远了。
剧中看似延续了王朔以前那种调侃的文章,但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发展了。 徐静蕾:我觉得这就是真诚的对话。什么叫真诚?难道说深奥、文绉绉的说法就叫真诚?我不这么觉得。
孙甘露:它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说话,但其实反映的是真诚的东西。我觉得,它妙就妙在以相反的方式说社会的这种变化,与当下中国的现实特别吻合,反映了人的一种新状况。 徐静蕾:他是抛开了被教育出来的那种语境的对话。
孙甘露: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对南方人来说,可能理解起来会有困难。我父母是北方人,理解起来还可以。有些言词必须用北方话来念,才有那种味道。 徐静蕾:别说是南方人,前面说了其实对我,第一遍看的时候也都晕,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还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之前我们排练了四天,就是对词,我都拍下来。因为这种全部对白在一个场景的形式没有人会不担心,我很担心观众会不会看不进去。所以我剪了一遍对词的过程,看一下节奏。
觉得还好。一开始,觉得开始的说喝酒那段太长,到后期的时候剪下去的比较多。后面还好,当然会有不同的人的理解问题,但那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电影都不可能拥有所有观众。 孙甘露:韩童生对剧本的反映怎么样? 徐静蕾:他很喜欢,他说他看的时候,很多地方看哭了。他觉得很多地方挺狠的。他的主业
是一个话剧演员,这种电影,有点类似话剧,戏眼也主要都在男演员身上,肯定给演员很好的发挥空间。因为,说实话,我都是配角,如果按相声的说法,他是逗哏,我是捧哏。最重要的话都是他说的。我是一个陪衬,给他的话更有力量。
其实从表演方式上说,我们俩很不一样。他是典型的话剧演员,而基本上,我是一个比较“水”的演员,也有一种说法叫“生活化”。(笑) 话剧演员在舞台上,要照顾最后一排的观众,所以容易比较夸张,但是电影就完全不同了,给你个特写,眉毛一扬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表演很不一样。
在现场我比较多提醒韩老师注意的是,表演要收,不能太外在,有十分的时候也只要演出八分就足够了。 孙甘露:我在看剧本时,在想象王朔平时说话的腔调,可以帮助理解节奏声音。
徐静蕾:韩童生是个很好很专业的演员,他很容易根据导演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表演,也会找形体上的一些东西帮助自己完成人物,比如他会突然拿个大顶,那是剧本上没有的东西,是他自己想的。
孙甘露:我在想,搞个话剧也不错。 徐静蕾:其实想过这事。因为这次上映时间特别赶。我是没那精力了。这种话剧,如果我演的话,最起码排练一个星期。因为不像拍电影,台词我可以今天背两页,明天背两页,话剧得从头到尾背下来。
现在也有人找来,想做话剧。 孙甘露:如果做话剧的话,台词部分有意思的东西更完整,观众更能理解。 徐静蕾:对,一方面话剧更活,和观众距离更近,另一方面,话剧观众和电影观众是两回事,话剧观众是做好了看这样一个东西的准备,而电影观众看惯了常规的那种类型电影,尽管我已经说了这不是一个那样的电影,不喜欢你就不要来看。
但还是有部分观众来看了,没有得到在通常电影里要得到的东西,就觉得枯燥,这是没办法的。
孙甘露:你以前那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叙事上比较传统。 徐静蕾:那个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虽然是茨威格写的,但我很容易把它转换成我的角度讲一个故事,把我的东西加进去。首先它是个名著,比较讨巧,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很感人,而且光影可以做得很漂亮。
但《梦想照进现实》不同,编剧的主导性很大,是我无法逾越的,尽管我加了一些东西,却不可能把它变成我的东西。而且,这个电影基本没什么大的情节起伏,我的能力和理解也有限,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在不影响编剧表达的情况下寻找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只有很专业的观众才看得出来。
做画面和声音剪辑时,我一秒钟一秒钟在改,但大多数人是不会注意到的,所以也可以说这都是为自己做的,一秒钟不做好我会很难过。
可能电影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就是娱乐消遣,有时我自己也是如此,累的时候也喜欢看美国大片。不用动脑子,热闹一下,睡觉去了。从这点上,我可以理解,也认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但是自己做片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喜欢做一件动脑子的事情,这是我选择做导演的原因。也许这件事情这个题材正好适合更多的观众,也许不是。 应该说前两部电影与这个相比,简单很多。
算一次尝试和自我挑战吧。 孙甘露:王朔写了一个比较没有情节的故事。 徐静蕾:基本没情节,就是她不演了。 孙甘露:他以前写的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玩的就是心跳》,结构比较复杂,有些意思可以通过情节推动提示给观众。
而这次,话都是摞着的。 徐静蕾:是,前面一直在说,我压力很大,因为它拍出来更像个编剧的东西,不是导演的东西。我觉得它很好,很怕放在我手上该说的话没说出来,所以我比较紧张,而且这次又是做低成本的尝试,周期不能长,时间很紧,只拍了十六天。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拍了四个半月。 后期也特别赶,到现在完整的胶片我都不敢看,看了我会疯的。因为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混录的时候,老觉得有一个高频打我的脑子,可大家都说没有,说是因为我累了,但我至今对此表示怀疑。
再比如,我特别讨厌混响,尤其在它只是起到美化声音的作用的时候,但是混录师特别热情推荐说这个特好。我很难一下子否决他的意见,只能婉转地、不停地游说。
这也是人家的工作,经过前两次导演工作的“培训”,最大的教训是:不要过度打击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可是到了晚上,离结尾工作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这个特傻,给我去了吧。 拍一个电影当中,最累的就是沟通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参与创作的人,要让大家都保持一个很好的创作状态,尽管我是导演,但导演毕竟不是每一个步骤的具体执行者,很多环节要依赖摄影、美术、录音、演员等等各个部门来完成。
这次因为时间短,尤其在后期,一天要干三天的工作,有很多环节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到自己满意。所以,不忍心看完整版,只看过一次对白双片,我就已经疯了,出去自己待了会儿。不过其实每次拍完一个电影,我都不敢马上看,要隔段时间才能看,否则我会特别沮丧,看到的都是种种不满意,只是这次更多一些。
孙甘露:这个电影太特殊了。 徐静蕾:这样的电影,中国没有过。国外其实也基本没有,起码我没看到过。我看过一两个,有的是爱情故事,场景也在不断的变化中,还有伍迪·艾伦拍过那种不停在那里说的电影,但还是有场景变化、有情节。
孙甘露:这个确实是挑战,事情没有变化,到最后还是没结果。这个戏没有发展变化。 徐静蕾:是的,而且我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表现形式,这是我的能力问题,我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很不自信,可能让王朔自己来导会拍得好些。
孙甘露:让他导不如让他演。 徐静蕾:也有人说让王朔演。他演和韩童生演,肯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演也不是特对。
因为他这个人,一说话,说高兴了,显得很油腔滑调(笑),尽管他说的事情本身并不油腔滑调。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他演的话,会出另外的效果。 不过他演我做导演的话,我就更晕了。他肯定在现场要有很多的改变,他说的话改变了,我得做相应的改变,灯光呀,镜头呀怎么改,而且他那么主观的一个人,离远点他还会说:你随便拍。
到了现场可就不一样了,肯定打起来(笑),那还不如他自导自演,我可以帮他做事务性的工作。
孙甘露:王朔有点打算做小众电影。他原来那个《我是你爸爸》,你看过吗? 徐静蕾:我不太喜欢,我觉得有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在里面。疯人院啊,火车啊,脸谱化的。那不是我的趣味。 孙甘露:你倾向于比较简单比较沉着的叙事。
徐静蕾:这是我很典型的趣味。这次在上海电影节做评委,看了十七部电影,最好的电影,是内容和技巧结合得比较好的。《4分钟》一开始很静止,特别像艺术片,挺闷的,在你没感觉的时候镜头开始摇了,让你那口气呼吸得特别舒服。不是为了简单的描述和技巧的炫
耀,导演的节奏控制很好。 好的电影,节奏是最重要的。事没新鲜事,技巧也没什么新鲜的。就是你怎么把这些东西搭配在一起,让演员用不同的表现方法表现同样的东西。 比如有些电影里,两人分别了数年,处理方式是一见面抱头痛哭。
感觉这是小时候看小人书那种,现在还有人这样处理,过于简单了吧。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你别说七年,一年不见都会有些尴尬、生疏等等很复杂的心情,怎么可能一下就抱头痛哭呢? 孙甘露:去年有部电影《漫长的婚约》,未婚夫上了战场,受伤失忆,女主角是个瘸子,找未婚夫找了很多年,最后找到时,未婚夫坐在树下做木工,她走到他面前看着他,他回头看她一眼,完全不认识,女的非常激动,坐下来看他做事。
徐静蕾:嗯。
可能那样处理比较好,至少没那么简单。我没看过那个电影。我觉得,不好的电影都存在过于概念化和脸谱化的问题;当然,还有简单的炫耀技巧,形式大于内容。 孙甘露:听说这个电影想过不上映? 徐静蕾:嗯。王朔原来跟我说,可以不用在电影院线上映,但不做成胶片只做成DVD的话,挺浪费的,因为我已经用胶片拍了,还做了相应的很多关于胶片的制作的工作,不上映有点不甘心。
孙甘露:大银幕看,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徐静蕾:是的。
我自己第一次感觉不一样,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第一遍看大银幕,是在日本做胶片后期,我突然觉得怎么用了那么多旁白,最起码三分之二是废话。这是个经验问题,大银幕和小银幕是很不一样的,在剪接台上看不出来,因为没觉得画面会有很大的冲击力。
当然,也是因为不自信,在小银幕上看老怕表达得不够,所以后来看大银幕了就有废话很多的感觉。 话说回来,下一次到小银幕的时候,可能还是觉得不够,想用辅助手段。 音乐跟旁白是一样的。
一开始没有做音乐,用美国大片或者喜欢的欧洲音乐来做替代,都特煽情感人,把自己忽悠了。在做《来信》时,经历过一个这样过程,用了很多煽情的音乐,有一天突然觉得不对劲,太滥情了,这其实是我看别人电影的时候最讨厌的。
第二天,我就把所有音乐拿掉重新剪辑。旁白,我剪片子的时候觉得很好,还挺美的,一看大银幕立刻傻了,特别糟心,但声底已经做进去了,不能再改了。 当我看不喜欢的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导演很傻,也会觉得导演把观众当傻子了。
但当我自己做出把别人当傻子的事情后,自然也就会特别郁闷。但到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拍电影有时候是挺糟心的一件事情,永远都觉得啊,怎么是这样,老是看自己拍的东西不顺眼。
孙甘露:你的电影都是自导自演,肯定会牵涉精力。如果再有机会,光导还是自导自演? 徐静蕾:我一上来一直自己导自己演,不觉得有什么。我可能下面会拍一个大学生的戏,可能就不演。说白了,我对演戏没有太大的兴趣,除非是自己觉得很值得演的角色,而且演员这个职业太被动,运气的东西多些。
但它毕竟是我的职业,是最靠得住的,能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经济条件的,有了好的经济条件才能让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以我现在的心态拍电影做导演,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的事儿。
前几天我拍了一个广告,我演得比较少,只做导演,我觉得太轻松了,想的事特别简单,如果我要演的话,我就要调整自己的情绪,要保持好的状态。 有一类导演只管讲戏,连镜头都不管的,因为旁边有很多技术人员,否则还要摄影师干吗?这个分人吧!
我觉得这是工作习惯。当导演可以当得非常轻松,因为有美术有摄影师,他们都是专业的,有经验的,演员也是你觉得合适才找他的。要想省事是很容易的。
我这么说,人家说你怎么这么牛呀。事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做得好是不容易的。无论什么事情做好都不容易。 孙甘露:十二年前,你排那个话剧,我和王朔去看,觉得你当时的状态,不是全心投入在演,好像在看在观察。
徐静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有一个自我在表演,有一个自我在实行适当的舞台监督。他是一个体验派的,他都在说有一个自我在舞台监督。当年毕业写论文时,大家有个感觉,控制是表演中的最高境界,要能收放自如。
我不是一个非常投入的演员,确实是这样。我本身是比较理性的人,所以我很容易从理性到非理性的状态,随时转换。做导演和演员,一天要在理性和非理性中转换很多次。演员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完全理性。
很多导演,在监视器里看自己拍的东西,现场就会哭出来。我觉得这样其实很不好,沸点特别低,拍出来的东西肯定特傻。导演感动成那样,观众很可能无动于衷。导演我觉得应该相对保持理性。很多东西是后期处理时放上去的。
孙甘露:有可能的话,你还是更倾向于做导演? 徐静蕾:如果完全可以抛弃饭碗,我肯定去做导演。当然,如果我做演员更合适,或者省去和别人沟通的麻烦,还有好的角色,我也愿意。我并不是排斥当演员。
只是,那没多大意思。 孙甘露:你进入专业受教育时,是不是有个抵触的过程? 徐静蕾:我觉得小时候,每个女孩子都有打扮得漂亮的时候,会对跳舞唱歌有点憧憬,但我属于刚有一丁点,直接被我爸爸喝止那种,不太去想那些。
后来我去考画画,没考上。后来就很像假的那样,在门口碰上一个导演,然后问我是不是表演系的,后来我就去考了。 上学时,念课文我都特紧张,哪有每天站在讲台当着全班同学念课文的?确实挺恐怖的。
可是因为虚荣心啊,我能考上表演系,放弃肯定不甘心。连我爸那种从小对搞文艺特别痛恨的人,都觉得你怎么能考上表演系,真棒。现在不读书了,我还是挺热爱表演艺术的(笑)。 孙甘露:拍电影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排开这些,你想要的电影,将来想拍的,是什么样的电影? 徐静蕾:我没有,我觉得那是所有的电影,所有类型的电影。
我还没有什么电影使命,我觉得什么都有意思,就看你怎么表现。因为你找了不同的演员和摄影师,电影就完全不一样,就像变魔术一样,二度三度创作的机会特别多,变数很多,很好玩的一件事。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一般一个导演拍的第一部电影都是自己的故事。我倒是觉得,拍自己的故事是最没法拍的,我觉得我不能面对,至少此时此刻。
孙甘露:年轻时觉得不好掌握,老了也许好一点。可是又想,老了都忘了,还说什么呢? 徐静蕾:我只是觉得很残忍,自己拍自己。我觉得写日记更好。忘了很可惜,毕竟一生可能就那么多事。拍电影的话,每天好几十个人面对我赤裸裸的心情,作为我来说,我很难用这种形式表现我自己。
我想,可能是把自己的事看得很重。跳出来可能又不一样了。 孙甘露:后来再演过舞台剧吗? 徐静蕾:没有。后来也有人找我演,但我觉得角色没什么意思。
我不能为了演而演。 孙甘露:你还是一个喜欢控制的人。 徐静蕾:我绝对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你现在很难衡量我演戏好还是导演好。当演员的时候,好不好都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能是编剧好故事好角色讨巧,让人“死”得不明不白,“火”得不明不白。
我演《将爱情进行到底》,我演了七集的,就看我在那火了,我都糊涂。当导演呢,很容易看清楚自己是三十分五十分九十分,责任特别清楚。 这是演员和导演的特别大的区别。
孙甘露:你还是想导戏? 徐静蕾:如果让我一定选个职业,以目前我能做的,还是做导演比较好。导演,从第一分钟开始就有事情想,完了就回家睡觉了。 当演员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在片场看会儿书打会儿游戏,马上就得进入那个状态。
演员真是特别辛苦的职业。我觉得一个人都能当演员了,肯定什么苦都能吃了。刚开始拍戏的时候,住最破的宾馆,地板长毛了,在大马路上吃饭。当然,也有人喜欢演戏,那也挺不错。但问题是,我不是这样的。
孙甘露:你在香港拍的是什么戏? 徐静蕾:《伤城》,一个复仇的故事,基本上是男人戏,我在里面算比较主要的,双生双旦。男演员是梁朝伟、金城武,女演员舒淇、徐静蕾,跟花瓶差不多了。就是典型的香港商业片。
不过,作为演戏来说,演这种戏最舒服了,住最好的酒店,搭戏的都是全亚洲最有名的演员,导演也不是太累的导演,因为刘伟强自己扛摄像机,所以每天的拍摄时间也不会太长,否则他就抽筋了,所以也不是太累。
孙甘露:香港拍戏的方式和内地有什么不同? 徐静蕾:其实差不多,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他们片场每个人都有耳麦。不像我们没钱,在片场拿一大喇叭喊。现场有三台机器,也省一半的力气。我这次是两台机器。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学学。 虽然拍了三部电影,我将来一定要试试完全不一样的电影,耍点技巧,很容易挺傻的,但就是好玩嘛。这次我拍广告,用了很多最好的机器,甚至有跟拍的设备,一般拍电影没钱用这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