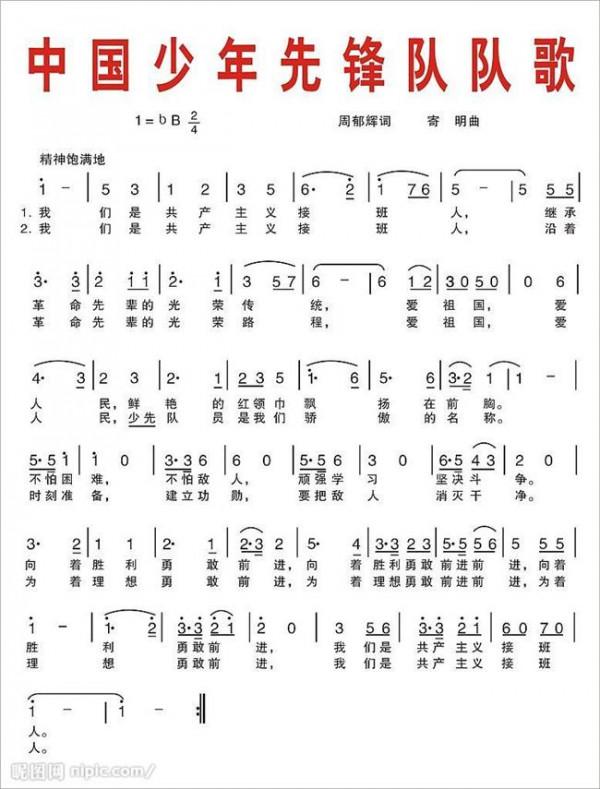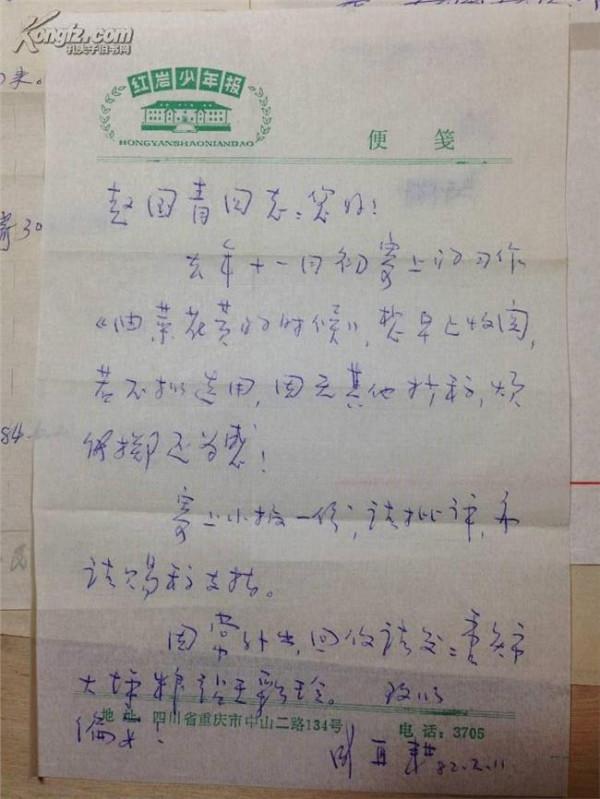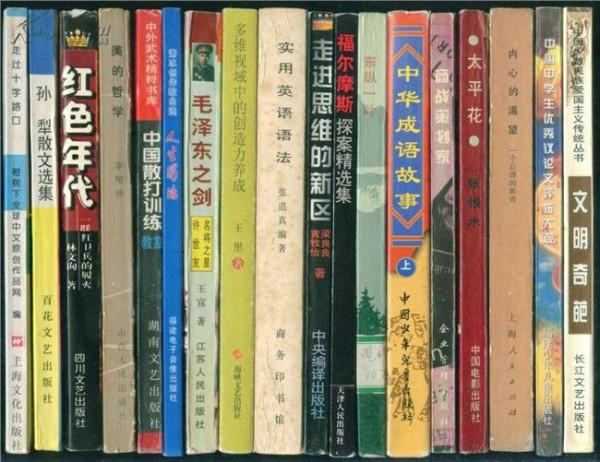孙甘露妻子 话语颠覆下的先锋精神建构――重新解读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
【摘 要】孙甘露的小说是在语言上进行了彻底的实验和突破,但其作品的文本意义却为当代学者所忽略,更有甚者否定了其文本意义,并将其定义为一个为了创造语言而写作的“先锋革命者”。本文就其《我是少年酒坛子》进行了一次彻底地文本解读,在分析其语言的先锋性实验中,从字字句句的形式幻象中解读出了文本之中的深刻“意义”,并尝试对传统评论所设置的“核心是虚无”的定义进行解构,赋予其“意义”。
【关键词】“陌生化”;先锋革命;文本意
先锋派小说以艰涩、晦暗、非逻辑、反理性被受众所质疑,却成为评论家的聚焦点,孙甘露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在语言实验上最具先锋性质的作家”,这几乎成为所有学者的共识。不可否认,孙甘露的小说的确是在语言上进行了彻底的实验和突破,他打破了一种现代汉语的规范,将词语进行重新组合,使其达到“陌生化”的惊艳之感。
这从其先锋实验代表作《访问梦境》、《信使之函》中可以略见锋芒。而另一方面,上述作品的文本意义却为当代学者所忽略,更有甚者否定了其的文本意义,并将其定义为一个为了创造语言而写作的“先锋革命者”。
本文就其《我是少年酒坛子》进行了一次彻底地文本解读,在分析其语言的先锋性实验中,从字字句句的形式幻象中解读出了文本之中的深刻“意义”,并尝试对传统评论所设置的“核心是虚无”的定义进行解构,赋予其“意义”。
陈思和认为《我是少年酒坛子》在其超现实主义式的语言中,语词不再指向现实,也不具有主体赋予的象征或隐喻意向,它们从表意功能中滑脱,成为一些自由的语象,在文本中自在地游走,似乎讲了一个有深意的故事,其实什么也没有。
孙甘露在形式上的确开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语言的形式就是语言的内容,二者不可能分离,所以我认为,正是这种“革命”使它的内容更富于意义。在上文中我们已从形式上认识了孙甘露的这种“语言革命”是在意义的基础之上的,是通过象征、隐喻等方式表达意象的。下面我们将从内容上对它进行真正的解剖:
一、“格式塔质”
格式塔心理学家爱伦费斯举例说:“我演奏一支曲子,由六个乐音组成的熟悉曲子,但使六个乐音作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尽管有了变化,你还是认识这只曲子。在这里一定是有比六个乐音的总和更多的东西,即第七种东西。”他称之为“格式塔质”。
这“格式塔质”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说的“弦外之音”、“象外之象”即意象。意象不仅仅是一种描写,而且是一种隐喻,它暗示了某种不可见的“内在”的东西。所以,对于具备强烈“诗意”性质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我们仍可以发觉作者铺设的许许多多的别具一格的意象,它为我们带来了惊艳的同时,也含混了其解读的明晰性。仅此我略举其中几个颇具特色的范例:
在文中“场景”部分,五个段落分别以“1959年”作为核心,分别阐述不同的内核。细心的读者会发现1959年是作者作者的出生年代,可见作者选择这个时间也绝非无意。作者用“1959年”来影射自己的一种企图打破常规进行自己颠覆话语的先锋革命的愿望的萌发,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表述方式,了然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为后文出现的理想陈述做好了铺垫。
2.铜币
铜币这里可以看作是“理想”的意象,诗人对“闪闪发光的铜币”的努力追逐的形象“仿佛在晚霞的余光中划着一艘孤独而华丽的龙舟”,也正是这种理想面前的强大障碍――孤独,使其最后放弃了铜币,最终,铜币陷入了最尴尬、最落魄的境地,这也体现了作者对理想的永恒坚持的一种怀疑和无奈。
二、形而上的意味
所谓“形而下的幸福,形而上的自由”的过渡,体现在文学上就是象征,象征将文字所指向的内容深刻化,精神化,同时也自由化,让读者体味到一种“形而上的意味”。象征是比喻或隐喻基于意象之间的比较或替换的更进一步发展,当一个意象不断被重复、持续,就在象征的层面上产生了意义:
1.诗人
朱大可在他的《都市的老鼠》一文中是这样理解孙甘露笔下的“诗人”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是他谴责的最初对象,为追逐一枚铜钱或一头发情的驴子而放弃了信念的诗人。”他认为在文中孙甘露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诗人”的,他认为孙甘露是将“诗人”定义为颓废和无恒定的信念的情感易变的知识分子。但从具体的语句中,我们却可以读出了另一种信息:
“不能因为你在街上,就说大家都在街上。”
诗人否定这种以偏概全的人生态度,反映其对一种普遍存在的缺乏真实的做作的创造风格的鄙弃和反感。
“藏无定法。”“不藏即藏,藏即不藏,聚即散,散即聚……”
这个句子中透露出诗人一种“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的道家哲学观,将其内质的精神内核无意中显露出来,即庄子所谓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达观的出世态度。
“不,我是来参加嘲讽仪式的。”
“嘲讽”是一个略带否定的态度,作者将之与“仪式”这个颇具庄重严肃色彩的词语搭配起来,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和反讽和一种在强大的现实压抑面前的无奈。
“一个从早至晚四处串门的人和在南方弄堂或者北方胡同里散布流言蜚言的人,这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使他们之间难以互相辨认。”
诗人将前者的无所事事及后者的粗俗可鄙并列起来,体现了他对世俗的大众化的一种精神的排挤,也体现了其本质中对打破日常规范企图颠覆传统的一种反叛精神。
“是的,我沉浸在一种疲惫不堪的仇恨之中……仿佛有一种遗世而立的美感。”
之所以让“仇恨”无限,诗人体会了一种对众生的庸常的的“仇恨”,对死气沉沉的诗歌感觉感到失望,对缺乏思考只会追风逐影的创作感到遗憾。这里,就要提到孙甘露深受影响的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创作,他也是体验到的巨大的幸福和绝望总是同时到来,他说:“我的寂寞,由于有了这样美好的希望,竟然变成了快乐。”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诗人”身上找到博尔赫斯的影子。